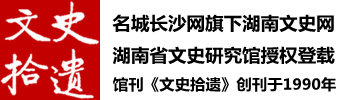黄兴是近代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杰出的民主革命家、军事家,辛亥革命时期与孙中山并称的主要领袖人物和民国“开国二杰”之一。但是自“二次革命”失败与中华革命党成立后,由于旧的封建正统思想(“天无二日,人无二主”)作祟,由于革命队伍中极‘左’思潮长期泛滥的影响,也由于某些政治因素(黄兴逝世日也是蒋介石的生日)的干扰,黄兴在很长一段时间受到排挤、贬斥,历史地位得不到应有的肯定,对黄兴的学术研究也长期处于低迷状态。据查考,民国时期28年间,仅出版有振汉子著《黄兴》(光复社1912年出版)、刘揆一著《黄兴传记》(1929年印行)、何伯言著《黄克强》(青年出版社1945年出版),以及黄蔡二公事略处编《黄克强先生荣哀录》(长沙,1917年印行)、天忏生等编《黄克强蔡松坡轶事》(上海文艺编译社1916年出版)等几种小册子和资料汇编,另报刊陆续发表10来篇纪念性的介绍黄兴生平业绩和革命精神的文章或小传。新中国建立后至改革开放前的30年间,亦只出版林增平编《黄兴》(湖南人民出版社1958年出版)和常谊编《黄兴》(中华书局1963年出版)2种小册子,另报刊先后发表学术论文3篇,其它文章及回忆录10余篇。故有研究者对近百年来的黄兴研究作了如下概括说:民国时期的黄兴研究,“真正的学术性研究论著很少。对黄兴的研究,尚停留在介绍与追述阶段,涉及范围限于黄兴事功、爱国精神、对革命的贡献等。对黄兴的地位和作用,还未能作出正确评价”;“新中国建立后的前30年间,对黄兴的研究还只是起步。研究的论文既少,而且评价偏低,与黄兴在辛亥革命时期的重要地位很不相称”;直到1979年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随着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实事求是学风重获发扬,“二百”方针逐步得到有效贯彻,黄兴研究才“称得上进入了研究的黄金时期”。本文拟对改革开放以来的黄兴研究作简要回顾、梳理,并就黄兴研究中尚存在的不足与问题谈些看法,以期推动黄兴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改革开放以来黄兴研究的主要成绩
改革开放35年来,黄兴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成绩显著:
一、发掘、积累了不少新资料,为黄兴研究的的深入开展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其中,黄兴本人著作的结集陆续出版,弥足珍贵。1981年由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中华书局出版的《黄兴集》(39.6万字),为大陆第一部带全集性的黄兴著作结集(台湾1968年初版、1973年增订再版了《黄克强先生全集》,但不够完善);2008年由刘泱泱增补重编、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版《黄兴集》(70万字),较旧版增加了近一倍的篇幅,是迄今为止最为完善的黄兴著作全集。关于黄兴生平事迹资料的收集整理,则先后有毛注青编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黄兴年谱》和中华书局1991年出版的《黄兴年谱长编》,辛亥武昌首义纪念馆编、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黄兴画册》,田伏隆主编、岳麓书社1996年出版的《忆黄兴》,俞辛焞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黄兴在日活动秘录》等。
二、研究成果大量出版发表,堪称硕果累累。35年间,共出版各类专著、传记、小册子、研究文集等达20余种,其中篇幅较多的专著和传记先后有薛君度著、杨慎之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黄兴与中国革命》,苏全有张历凭主编、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黄兴与阳夏战役》,李喜所等著、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黄兴的军事理论与实践》,刘英志主编、武汉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孙黄共时代》,萧致治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黄兴评传》,石彦陶著、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黄兴传》等。各报刊发表各类论文文章累计530余篇(其中研究性论文与考证380余篇),平均每年发表在15篇上下。其中纪念辛亥革命70、80、100周年的1981、1991、2011年,分别为33篇、71篇、18篇,纪念黄兴诞辰110、120周年的1984、1994年,分别为20篇、39篇。其它发表论文较多的年份为1982、1989、1990年,分别为25篇、23篇、49篇。
三、研究范围逐步拓展、质量显著提高,解决了一些过往模糊不清和存在争论的问题。首先是由于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和实事求是学风的发扬,黄兴的历史地位获得了应有的高度肯定,评价渐趋一致,一些原持贬谪评价的学者也明确改变了观点。这是近30余年来黄兴研究中最重要的也是最显著的一大收获。其次,由于研究者队伍的扩大、视野的开扩以及资料积累的增多,研究的内容和范围迅速拓展,由原先大多偏重于政治层面的研究,局限于革命事迹记述、是非功过褒贬,逐步由政治扩展到军事、思想、文化、教育、经济、社会、家庭、品德、人际关系,以及外交、华侨等诸多方面,实现了由片面到全面,由单线到立体的可喜突破。第三、也由于实事求是学风的培育发扬、“二百方针”的贯彻落实和资料发掘的增多,研究逐渐向深入发展,成果质量总体上显著提高,一些过往模糊不清或存在争议的问题获得了解决。萧致治著《黄兴研究著作述要》第二章《研究概述》第二节《黄兴研究成果透视》中,对此作了10个方面的概括和说明。这10个方面依次是:⑴“黄兴的家世和青少年时代研究”;⑵“黄兴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⑶“黄兴的军事理论和武装反清斗争”;⑷“黄兴与‘二次革命’”;⑸“黄兴与护国运动”;⑹“黄兴拒绝加入中华革命党评析”;⑺“民国初年黄兴的基本政治倾向”;⑻“黄兴的政治、经济、学术、文化教育思想与品德的研究”;⑼“黄兴的人际关系研究”;⑽“黄兴是革命实行家,也是理论家”。文字简明扼要,有观点,也有例证,足资参考,此处不赘述。
四、黄兴研究队伍明显扩大,并出现了有组织的研究。新中国建立后的前30年,黄兴研究者只有寥寥五六人。而改革开放以来的35年间,黄兴研究队伍迅速扩大,经查考,先后研究黄兴且出版发表著作的达250余人。这250余人,主要集中在湖南、湖北、北京、广东、上海、广西、天津、河南等省市,其他依次分布于四川、山西、云南、江苏、山东、辽宁、贵州、江西、浙江、黑龙江、吉林、新疆、福建、安徽、内蒙古、陕西等省市区,几乎遍及全国。先后涌现出了一批成果较丰、颇具影响的黄兴研究学者,如毛注青、石彦陶、萧致治、李喜所、苏全有、刘英志、邓江祁等。值得注意的是,在两湖地区,还陆续建立了以推动黄兴研究为目的的研究机构和学会。如1987年,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率先建立了黄兴研究室。随后,1993年,江汉大学建立了黄兴研究所;2001年,湖南学者也成立了黄兴研究会(挂靠于湖南省文史研究馆)。这些有关黄兴研究的专门机构和学会,组织编写和出版了多种黄兴研究专著和论文集,对推动黄兴研究深入发展,起到了有力的作用。此外,在此期间,还举办了多次有关黄兴的学术研讨会,如1988年由湖南省政协、社科院、社科联等联合发起在长沙举行的全国首届黄兴研究学术讨论会,1992年由海峡两岸学者携手合作在台北举行的“黄兴与近代中国”学术讨论会,1994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和美国黄兴基金会联合在北京举行的“黄兴学术研讨会”。这些学术会议的召开,也起到了组织与推动黄兴研究的良好作用。每次学术会议的当年和次年,通常都是研究成果出版发表最多的年份,就是生动的证明。
黄兴研究有待进一步开拓和深入
科研无止境。改革开放以来黄兴研究虽然取得了长足进步和显著成绩,但仍存在许多不足。研究资料还需要继续发掘、积累,力求全面、丰富;研究领域有待进一步开拓;一些问题尚存在争议,需要更深入探讨;等等。研究者必须继续奋发努力,将黄兴研究持续、深入地进行下去,以期取得更大的成绩。关于这一点,萧致治在所著《黄兴研究著作述要》第二章《研究概述》第三节《未来研究展望》中,提出了三点建议和希望:一、“有些研究成果是具有代表性的,但随着新资料的发现,认识水平的提高,仍有修改增补的必要。”他列举了薛君度著《黄兴与中国革命》,他本人著《黄兴评传》,石彦陶、石胜文著《黄兴传》。二、“黄兴研究的领域较前已有相当扩大,但仍有一些领域没有涉及或很少涉及。”他列举了黄兴与美国、与日本、与华侨,黄兴的外交思想、反帝思想、开发边疆增进民族团结的思想、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主张,黄兴的书法等。三、“发掘新的资料,提高研究水平,仍然是今后努力的方向。”他举例说:近阅衣保中《黄兴创办中国垦殖协会及其对吉林边疆开发的作用》一文,“发现有黄兴的两篇致吉林的电文,新出版的《黄兴集》就没有收录。因此仍有继续发掘的必要与可能”。这些建议和希望均十分中肯,我完全同意。但我认为须要补充的是,还应该在资料的甄别和史实的考订方面,更多地下地艰苦细緻的功夫,力求研究更深入和成果更准确。
下面,我便根据研究中所见,依黄兴事迹的时间先后,举几个问题为例,作些说明。
⑴ 黄兴十四五岁时在家自学,有资料记载说,黄兴在这期间曾订有《自勉规则》六条。这六条是:“一、行动必须严守时刻;二、说话必须说到做到;三、读书须分主次,纵使事忙,主要者不得一日荒旷;四、处理重要事务及文书,必须亲自动手,不得请托他人;五、对人必须真诚坦白,不得怨怒;六、游戏可以助长思虑,不应饮酒吸烟。”这六条显然超出了自学的范围,包含学习、工作、为人处世、品德修养各个方面。文中使用“必须”、“不得”、“不应”等字,似乎也不是自勉,而更像是黄兴对他人或者他人(如师长)对黄兴的要求。特别是第四条“处理重要事务及文书,必须亲自动手,不得请托他人”,更不像还在求学阶段的未成年少年所写的文字;这时的黄兴,学业远远未成(他四五年后才开始入长沙城南书院读书),也不可能有什么“重要事务及文书”需要他处理或请人代劳。因此,这六条《规则》,是否黄兴早年自学时所拟订,很值得怀疑。是否出自后来文人的拼凑,或是由于师长或父辈的要求,根本就非黄兴所写,有待进一步研究确定。
⑵ 黄兴早年也曾参加过科举考试,取得过秀才。他是于何时、又通过何种方式考取秀才的?过往的记载,时间上存在两种不同说法:1893年说和1896年说。方式上则大体一致:都认为是通过善化(今长沙)“县试”获取秀才的。后来研究者根据当事人的回忆,大多倾向于1896年说,这点应可成立。至于原先大体一致的“县试”说,我则觉得还有欠准确。因为按旧时科举考试制度,凡童生应考秀才,须经过三个阶段的考试,即县试、府试和院试,层层递进。县试由县官主持,府试由知府或直隶州知州、直隶厅同知主持,院试则由主管全省教育行政的学政(清末或称提学使)主持。只有先经过县试、府试,最后通过院试录取者,才能分别送入相应的府、县学继续学习,成为府、县学生员,通称秀才。因此,黄兴应是先经过县试、府试,然后通过院试录取,分发原籍善化县学为生员,即考取秀才的。
⑶ 黄兴的早年学历究竟如何?他幼受父教,又读过私塾,这些都没有疑问;问题是此后去了哪里上学?过去好些有影响的著作,包括台湾出版的左舜生著《黄兴评传》、陈维伦著《黄克强先生传记》、李云汉编《黄克强先生年谱》,大陆早先出版的章开沅等主编《辛亥革命史》、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等,都说黄兴从1988年起就入岳麓书院读书,直至1898年由岳麓书院保送去武昌两湖书院深造才离开;继后湖南大学编校史,岳麓书院举办院史陈列,都将黄兴列入岳麓书院学生名单,加以宣扬。其实这都是以讹传讹,不符合历史事实。黄兴其实从没有入过岳麓书院,他进武昌两湖书院也不是由岳麓书院选送,而是由湖南校经书院选送的。近些年萧致治著《黄兴评传》、石彦陶著《黄兴传》,才对此讹传作了考订和更正,认为黄兴所入不是岳麓书院,而是长沙城南书院(1893年入学)。萧著提出了三点更正的理由:①岳麓书院入学门坎较高,肄业者皆廪生、附生、监生,而不收童生;城南书院则入学门坎较低,兼招收附生、监生和童生。黄兴1896年才考取秀才,“在此之前,他只是一名未入学的童生,尚无资格进入岳麓书院就读”,而入城南书院则是具备条件的。②黄兴入长沙城南书院读书,有他的同学雷恺的多篇回忆录为证,而黄兴的长子黄一欧也说到:“雷恺先生曾多次同我谈过与先君在城南书院的旧事,是实在的。我从未听过先君青少年时曾进岳麓书院读书。”③“黄兴本人也从未提过在岳麓书院读书。如果他真在岳麓书院读书十年,差不多占去了他生命的四分之一,一定对他印象很深,在他生平行事中,不可能一字不提。”至于湖南大学和岳麓书院认定黄兴为岳麓书院的学生,很可能是因为黄兴曾被选送进校经书院深造,而校经书院的前身湘水校经堂曾附设于岳麓书院内的缘故。但查由湘水校经堂到校经书院,有一个演变过程,地址也几经变迁。它是由湖南省政当局创办并主管的,始创时期(1833—1836)和重建时期(1862-1879)均附设于岳麓书院内,其时主讲和阅卷均以岳麓书院和城南书院两山长为主,省政官员并定期到堂讲课;扩建整理时期(1879-1890)改迁于城南书院旧址;改制时期(1890-1903)则连名称也改为校经书院,院址也移建于长沙城北湘春门外熙宁街。因而湘水校经堂、校经书院与岳麓书院,无论在其附设时期和改迁、移建时期,都不是下属和主管的关系。校经书院正式成立于1890年,已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书院。而黄兴是于1898年才由城南书院选送入校经书院、不久又由校经书院选送武昌两湖书院深造的,他这时的学习与选送,与岳麓书院毫无关系可言。作为千年学府的岳麓书院与湖南大学,早已由她的悠久连绵的历史、深厚的文化底蕴、山长校长皆时贤名流,和历来学生人才辈出,而享誉古今中外,大可不必再借原本不是岳麓书院学生的近代伟人黄兴来增光添彩了。
④ 华兴会的成立是近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即辛亥革命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黄兴早期历史中的一件大事。由于华兴会原属秘密革命组织,且发动起义又仓促失败,遭到严重搜捕破坏,以致没有留下任何原始文献资料。事后黄兴也没有专文述及。其他当事人(主要是刘揆一、章士钊、周震鳞、曹亚伯、黄一欧等)多年后(辛亥革命后以至新中国建立后)的回忆录又真伪杂陈,言人人殊。如成立时间,有1903年(11月4日)说,1904年(2月15日)说。成立地点,有连陞街机关部说、保甲局巷彭渊恂宅说。与会人数,有12人说、20余人说、 30余人说,具体人员名单亦各有同异。领导成员,黄兴被举为会长,各回忆录一致,副会长则大多无明确记载(宋教仁、刘揆一是其它史籍载明的),惟秦毓鎏《自述》称曾任副会长。华兴会宗旨,各回忆录也无明确有据的记载。等等。这种原始资料严重缺失和记述不一的状况,给后来的研究者研究华兴会和黄兴早期革命活动带来了极大困难,亦导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已成的研究著作,或是从不同记载中,择取一说;或是折衷诸说,“兼容并包”;或是另行采访,再立新说。如成立时间,有从1903年说者,有从1904年说者,又有折衷调和二说,提出两次会议说者,称第一次为筹备会议,第二次为正式成立会议。成立地点,有经采访另立新说,提出在西园龙宅(明德校董龙璋寓所)者;参与成立会人数,也添加了100余人之说;华兴会旨,则出现了“驱逐鞑虏,复兴中华”的新提法。这些新说,究竟有何真实可靠的依据,仍不甚了了。总之,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尚有继续、全面、深入、细致研究的必要。
⑤ 1905年12月8日,辛亥革命时期著名的民族民主革命家、宣传家,“革命党之大文豪”陈天华(字星台),因抗议日本政府限制中国留学生革命活动而颁布的《关于准许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被留学生称为《取缔规则》),激愤难遏,留下绝命书,在东京大森海湾蹈海殉国。紧接着12月25日,有署名“强斋”者奋笔撰写《陈星台先生〈绝命书〉跋》一文,刊于稍后(1906年1月22日)出版的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第二号。此《跋》的作者“强斋”究竟是誰?后来出现两种说法:曹亚伯著《武昌革命真史》称其为黄兴所写,而另外有多种著作则认为系宋教仁所作。研究者也各有所从。这就成了需要研究弄清的问题。以曹亚伯与黄兴的亲密关系,其说或不无根据,但未予说明。考黄兴在从事革命或流亡期间,虽曾用过不少化名,而生平著文,则未见有用笔名者。又考黄兴在陈天华蹈海前后的行踪,他于该《跋》写作和发表的这段时间内,很可能并不在日本。因为时任香港《中国日报》社长兼总编辑冯自由有记载:“(乙巳)十一月,黄克强至香港,寓《中国报》社。”按:旧历该年十一月,公历为11月27日至12月25日。黄一欧也回忆说:“……一九0五年秋末冬初,才同湘潭黄积成一起去日本。其时先君已去南洋。”查1905年立冬在11月8日,则秋末冬初当在公历11月上中旬之内,距陈天华蹈海尚有一段时间。且黄兴这次离日时间较长,他辗转香港、广西、越南等地,至次年9月才经由上海返抵东京。根据这些,曹亚伯所说该《跋》为黄兴所写,迄今尚是孤证,似难成立。那么,该《跋》为宋教仁所作说又有多少证据呢?考宋教仁所著文,所用笔名甚多,其中有与“强斋”字音近似者。他在主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期间,就用“勥”的笔名发表过多篇时评(见于该刊第一期者3篇);稍后至《民报》时期,宋文更多,常用的笔名则是“勥斋”。“强”、“勥”虽字形有所不同,但查汉语字典,都有强迫义,又都有固执、倔强义,且用此义时,读音亦相同;而 “勥” 又同“犟”。三字在古近汉语文献中是可以通用的,则“强斋”即为“勥斋”亦可成立。另据与宋教仁同属报人且关系密切的汤增璧回忆:“自星台烈士蹈海,渔父为纪其事于《民报》。”亦可作为佐证。但总的看,证据仍欠充分,期待有更多的新资料发现和更深入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的黄兴研究】刘泱泱[黄兴诞辰140周年纪念专辑]
2015-01-03 11:28:00 来源: 评论:0 点击:
黄兴是近代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杰出的民主革命家、军事家,辛亥革命时期与孙中山并称的主要领袖人物和民国开国二杰之一。但是自二次革命失败与中华革命党成立后,由于旧的封建正统思想(天无二日,人无二主)作祟
分享到:
相关热词搜索:改革开放 黄兴 研究
上一篇:【法国官方档案中的黄兴】邵雍[黄兴诞辰140周年纪念专辑]
下一篇:【在“礼”与“法”之间——黄兴社会治理思想述评】胡波[黄兴诞辰140周年纪念专辑]
分享到:
频道总排行
频道本月排行
- 20【东汉邓禹其人及晚清重修邓禹墓考】邓继团2023年1期总131
- 11【于光远曾两次来安化马渡调研—一份与“马渡调查”有关...
- 10【浏阳算学社】耿静好 林洪2023年3期总133
- 10【长沙城建大事记(上)(公元前475年—公元1850年)】陈先枢...
- 7【新发现柳直荀1921年三篇文章解读(一)】李忠泽 罗慧...
- 7【纪念辛亥元勋黄兴 揭秘民国建立真相】吴欢[黄兴诞辰1...
- 7【烽火间隙的酬唱和风雅】王金华2022年4期总130
- 7【保存陈毅安烈士五十四封遗书的李志强】焦广2021年4期总126
- 6【民国成立前后黄兴的民族观念】田涛[黄兴诞辰140周年纪...
- 6【民国建立后黄兴与孙中山政治思想的同异】宋德华[黄兴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