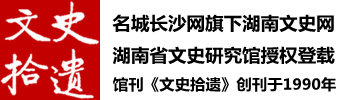内容摘要:黄兴的社会治理思想,主要体现在礼和法两个层面。先礼后法,礼法并重,法治取代人治,在宪政框架下实行政党政治,是黄兴社会治理思想的中心内容。
关键词:黄兴 社会治理 礼治 法治 政党政治
在辛亥革命史的研究领域,一直流行着“孙氏理论、黄氏实行”的说法,以为孙中山纯粹是个思想家,而黄兴则始终是一位实行家。辛亥年间出版的《血书》就认为:“黄非思想家,亦非言论家。实为革命党中唯一之实行家也。”(1)因此在孙中山思想研究如火如荼的时候,黄兴思想研究却倍受冷落。虽然近二十余年来黄兴思想研究有了一些新的成绩,但大都集中在黄兴的政治思想和教育思想等方面,(2)对黄兴的社会治理思想一直缺乏应有的重视和深入的探讨。
诚然,黄兴本人并没有对社会治理问题进行过专门的论述,他的社会治理思想也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更没有中国儒家《大学》里的社会治理思想那样富有逻辑性,但我们从他的演讲、函电、诗词、书信和实际行动中,仍然可以看到其社会治理思想的基本轮廓。概括地说,黄兴的社会治理思想,主要体现在礼和法两个层面。先礼后法,礼法并重,法治取代人治,在宪政框架下实行政党政治,是黄兴社会治理思想的中心内容。
一、 礼治与德治:社会治理之本
中国古代乡土社会,实际上是一个极端封闭的没有生人的熟人社会。在熟人社会里,不需要法律诉讼,不需要彼此设防,人们在熟悉和亲密的关系中生产劳动和社会交往。他们比此重然诺、讲信用,重礼教、守规矩,重修养、敦气节,在既定的礼制和规约中共同维系着熟人社会的稳定与和谐。黄兴就是一位在乡土中国的熟人社会里成长起来的革命家。
相对邻近的广东而言,“湖南民性似乎偏于倔强保守。”在黄兴诞生之前十年,为了捍卫儒学传统,矢志扑灭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抢救清王朝的湖南人就是曾国藩、左宗棠及其统帅的湘军。但是,十九世纪第一批醉心于“西学”的人群中却有许多人籍贯湖南。他们之中最有影响的是魏源、郭嵩焘、曾纪泽。清初许多民族主义思想家也出生于湖南,其中最著名者有王夫之。(4)黄兴的祖辈素有“居身淳谨”、“悬鉴励操”、“力学敦行”、“敦礼践善,在痒有声”、“勤于职守”、“洁己奉公”、“敦气节、重然诺”的美誉,更注意修身立品、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克勤克俭、邻里和睦。(5)黄兴的祖父虽有军功六品顶戴,从九品职衔,但只有虚衔而无实职。他的父亲当过都总,算是一乡之长,但原则上还算不上真正的官员。(6)黄兴从小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具有优良传统品德的家庭。
黄兴小时候就受到较为严格的传统文化教育。5岁开始读《论语》,诵唐诗、背宋词、练书法、对对子,打下了较为扎实的国学基础。十四五岁时因家中连遭不幸而失学。但他在做些力所能及的农活的同时,还利用空闲时间学文习武。为了将来有所作为,他曾自觉地立志修身,并订有《自勉规例》六条:“一、行动必须严守时刻;二、说话必须说到做到;三、读书须分主次,纵使事忙,主要者不得一日荒旷;四、处理重要文物及文书必须亲自动手,不得请拖他人;五、对人必须真诚坦白,不得怨怒;六,游戏可以助长思虑,不应饮酒吸烟。”(7)年轻时的黄兴,虽然还没有深刻理解孔孟儒家的社会思想,但在做人做事上已承传了祖德家风,敦礼践善,守约笃行。
进入城南书院和武昌两湖书院后,黄兴对儒、道、法、墨各家学说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对程朱义理之学也有了不少心得。在城南书院学习时,他“着意老庄,尤着意禹墨;注重儒术,但亦注重兵法刑名,而于孙吴兵法阐发尤多。如札记所载,先生认为孙吴诸家所论之理,多与道、儒、墨、法各家学说互相贯通。机智权谋,辅以仁义,训兵用将,威爱兼施等情,更非寻常军人文士所可践履者。其后治军事政事,大率本于诸家之学以及兵法要则而致之用。如于孙子所谓修道得法,上下同欲,亦即于政、军措施,与军民意志之配合,多所致意,俾克大展其兼资文武,造福国民之经纶。”(8)这时的黄兴对诸子百家的思想学说,采取的是兼收并蓄、择善而从的态度。尤其注重“兵法刑名”。在两湖书院求学阶段,笃志向学,成绩优异,深受院长梁鼎芬和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器重。在各科中,对地理和体操尤为重视,认为“不通地理,无以知天下大势;不习体操,无以强身而有为。当时风气初开,每临操,同学中有一、二顽懦者多掉以轻心,甚或以揶揄出之,不欲轻卸蓝衫。……而先生独异是。临操如临阵,短装布鞋,抖擞精神,听令唯谨,动作无不如度,不稍苟。久之风被全校,顽懦者亦为肃然起敬焉。”(9)从湖南长沙到湖北武昌,学习的内容丰富了,活动的空间扩大了,结交的朋友增多了,但是知礼守约已成为黄兴自我道德修养的基本标准,礼制和规约也内化为黄兴的社会治理思想的重要内容。
中国传统社会是个礼治的熟人社会。社会对人们行为的控制,主要依赖于礼制和教化。在孔子看来,“凡人知礼,能见已然,不能见将然。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礼云,贵绝恶于未荫,而起敬于微渺,使民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10)也就是说,法禁已然,譬则事后治病之医药;礼防未然,譬则事前防病之卫生术。儒家之以礼导民,专使人们在平日不知不觉间从细微地方起养成良好的习惯,自然而然地成为一个健康人格的人。孔子又说:“礼义以为纪,……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11)也就是说,法是恃政治制裁力发生作用,礼则专恃社会制裁力发生作用。“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12)儒家确信非养成全国人之合理的习惯,则无政治之可言。所谓“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13)就志在劝诫圣君贤相,治民莅事应重在化民成俗。所谓“劳之,束之,医之,直之,辅之,翼之,使自得之,”(14)即相信以“自得”之民组织社会,则何施而不可者。事实也是如此,礼治为中国社会曾带来高度的稳定和长期的繁荣。
尽管礼治有数不清的流弊,可是礼的基本精神是主动的,它不像法治依靠外在的权利来进行。儒家深信同类意识之感召力至伟且速,谓欲造成何种风俗,惟在上者以身先之而已。梁启超就明确指出:“要而论之,儒家之言政治,其唯一目的与唯一手段,不外将国民人格提高。以目的言,则政治即道德,道德即政治。以手段言,则政治即教育,教育即政治。道德之归宿,在以同情心组成社会,教育之次第,则就各人同情心之最切近最易发动者而浚启之。”(15)
黄兴虽然没有象孔孟或历代大儒那样公开谈论礼治社会的构想和礼教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也没有专门研究社会治理的著述,但从他处理矛盾纠纷和解决社会问题、以及待人接物的态度和方法上,仍然不难看出他对儒家礼教和德治怀有尊重崇敬之情,有时甚至相信只要有“无我”和“笃实”的精神,有“大丈夫”敢于冒险犯、勇于担当的品格,就能达到激励同侪、引领群伦、投身革命和建设的目的。1906年黄兴在《民报》创刊周年庆祝会上所说的“革命家不可无道德”,就反映了他对道德的高度重视。在他看来,道德的重要性不只在于改良社会风俗,还在于它关系到“种族存亡、国家兴灭”。他说:“民国初建,首重纪纲。我中华开化最古,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夙为立国根本,即为法治精神。”在正式发表的电文中明确地表达了他对忠孝等儒家思想观念的理解:“以忠言之,尽职之谓忠,非奴事一人之谓忠。古人所称上思利民,以死报国是也;以孝言之,立身之谓孝,非独亲其亲之谓孝。……盖忠孝二字,行之个人则为道德,范围天下则为秩序。……即如此次起义,全体一心,父诏兄勉,前赴后起,复九世之深仇,贻五族以幸福。于民国则为忠,于私家则为孝,是以政治革命、家庭革命诸学说,原为改良政教之起见,初非有悖于忠孝之大原。”(16)在这里,黄兴并未简单认同儒家的忠孝观念,而是结合革命运动和时代精神创造性地将中国与西方、革命与道德统一起来,为政治革命、家庭革命,乃至社会革命服务。在解除南京留守职务时,黄兴更明确表示:“此后之关系,不在形式,而在精神,不在私情,而在公义。如兴有不忠于国,遗害于民者,愿诸君子以正义责之,兴俯首受罪以谢天下。诸君子之行动,兴苟见以为不合者,亦当勉效忠告。掬此热忱,庶几宏济艰难,共跻福利。”(17)黄兴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1912年5月黄兴得知熊希龄与外国银行团订“货款协定”而损失国权极多时,立即致电熊希龄:“吾辈均以国家为前提,于个人关系,绝不宜稍存意气。而于国家生死关头,尤当审慎,岂得因一时一事办理骤难得于遽萌退志。……兴于公本系至好,责公劝公,固皆为国,亦即所以为公。”(18)
值得称道的是,黄兴在处理党内党外事务时,总是强调道德和操守,总是怀有礼让和敬畏之情。他与孙中山共事10余年,曾先后3次发生龃龉,但每次都以黄兴的退让而告终。(19)尤其是在同盟会内部三次“倒孙风波”中,黄兴从大局出发,尊重孙中山,拥护孙中山,利用个人的见识和威信,维护了革命队伍的团结统一。他曾致书胡汉民称:“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先生何定须执着第一次起义之旗?然余今为党与大局,已勉强从先生意耳。”(20)陶成章、章太炎发动第二次“倒孙风波”时,要刘揆一改组同盟会,推黄兴为总理。黄兴深明大义,坚决反对,并反复强调:“革命为党众生死问题,而非个人名位问题。孙总理德高望重,诸君如求革命得到成功,乞勿误会,而倾心拥护,且免陷兴于不义。”(21)黄兴的劝阻和开导,维护了孙中山的地位,也避免了同盟会内部的分裂。1911年10月,黄兴被举为大元帅,但他坚决推辞,并对李书城说:“顷接孙中山先生来电,他已启程回国,不久可到上海。孙先生是同盟会的总理,他未回国时我可代表同盟会,现在他已在回国途中,我若不等待他到沪,抢先一步到南京就职,将使他感到不快,并使党内同志发生猜疑。……肯自我牺牲的人才能革命。革命同志最要紧的是团结一致,才有力量打击敌人。要团结一致,就必须不计较个人的权利,互相推让。”(22)正是黄兴对革命的忠诚和对名利的淡薄,才换来了革命组织的团结和革命事业的成功。
孙中山因此称黄兴“禀赋素厚”,周震麟称黄兴“光明磊落、敝履权势”。“治学行事,脚踏实地;对待同志,披肝沥胆。因而能够得到一般同志的衷心爱戴。”胡汉民称黄兴“性素敦厚”,“处世接物,则虚衷慎密,转为流辈所弗逮。先生使人,事无大小,辄曰慢慢细细。余耳熟是语,以为即先生平生治已之格言。”(23)黄兴长女黄振华也说:“(黄兴)自幼至壮年,甚有礼貌,孝顺父母。不吸烟、不喝酒、不赌钱、不打牌。喜运动如打拳、打球、钓鱼、打猎,也喜欢下围棋和团体游戏。”(24)章士钊回忆说:“克强情异虬髯,帜鄙自树,太原真气,户牖冥濛。”“吾弱冠涉世,交友遍天下,认为最难交者有三人:一陈独秀,一章太炎,一李根源。但吾与三人都保持始终,从无诟誶。吾答或问:吾恃以论交之唯一武器,在‘无争’二字。然持此以御克强,则顿失凭依,手无寸铁。何以言之?我以无争往,而彼之无争尤先于我,大于我。且彼无争之外,尤一切任劳任怨而不辞,而我无有也。由是我之一生,凡与克强有涉及大小事故,都在对方涵盖孕育之中,浑然不觉。因而我敢论定:天下最易交之友,莫如黄克强。又克强盛德大量,固不革命对吾为然也。凡视天下之人,罔不如是。”(25)
同时代的人对黄兴的评说难免有主观色彩和情感投入,但黄兴赋性敦厚,崇礼重德,知行合一的个性品格,也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他不仅以严于律己、诚实守信、谦虚谨慎、光明磊落和淡泊名利的精神品格引领群伦,而且还以儒家倡导的礼和德来教化和规训人们的言行,调节和改善组织内外的人际关系,促进人与人、人与组织、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因此,道德教化和礼制规训,或所谓的礼治与徳治,在黄兴这里仍然被视为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
二、 人治与法治:社会治理之法
礼制规训和道德教化是中国历代统治者治理国家和社会的重要方式,礼治和德治也一直是历代思想家、政治家热衷讨论的话题。但是,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西方的民主与法制给西方社会带来的文明进步,使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反思中国的礼治、德治下的人治,甚至直接呼吁打破“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清规戒律,树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权观念,在社会治理上全面学习西方,实行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法治”。(26)
中国的旧律基本上以伦理法作为制法与执法的依据,这种现象自唐律的制定以来就没有太大的改变。宋、明和清律基本上都是因袭唐律的标准而编纂,改朝换代并没有对法典的编列有革命性的影响。这个源远流长的引德入法、援礼作律的做法,在汉律的制定中已经明显可见。(27)后来的法律,只是沿袭汉唐以来的“以礼立法”的作风而已。这种礼刑合一的制法是中国法系的特色,也是“儒学法学化”和“法律儒家化”等论辩所以能够兴起的原因。(28)晚清不再以礼制法,不啻是对沿袭两千余年的中国法系的一大否定,也是对儒家倡导的德治与礼治的一大打击。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以沈家本的修律而言,虽然它的范围远大于身体权的维护,而它的初始动机也不是为了身体的解放,但这个为了司法主权而采取的动作,却在实际修法的过程中,将旧有的伦理束身的法律规矩做了一次挑动,使以礼入法的原则不再成为中国法制的主导势力,取而代之的是更具体权利法形式和人道意涵的法律制度。”(29)虽然光绪朝所颁布的宪法大纲充满了皇权至上的论调,但在有关臣民权利义务的条款上,也首次言明人民在法律范围内有言论、著作、出版、集会和结社等自由;人民身体非依法律不得加以逮捕、监禁和处罚。这个企图以法律来规约人民身体与意志活动范围的努力,到了民国之后,有了更进一步的改观。最明显的是,皇权作为身体的最后统治者的身份不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民主共和的平等身体关系,皇族不再成为法外人的身份团体,从总统到平民均处于同一的法律地位。《临时约法》规定人民有身体、居住、迁徙、财产、营业、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通信和信教的自由,以及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都说明个人身体在此时已经走上法律化的路径,不再片面从属于皇权、父权、夫权和家长权的垄断与统治。(30)
黄兴虽然早期接受的是传统文化的教育,但其时西学思潮和反满情绪已经波及到他所在的书院,各种介绍新知识新思想的书籍、报刊也成了黄兴课余的读物。他后来回忆说,“两湖书院功课亦极平常,其宗旨纯系忠君。顾读书数月,见报纸所载,友朋所言,始知世界大势决非专制政体所能图强,亦非郁郁此间所能求学。”(31)因此“课程余暇,悉购西洋革命史及卢梭《民约论》诸书,朝夕盥诵。久之,革命思想遂萌芽脑蒂中矣。”(32)在日本弘文书院期间,正是留日学生思想最活跃的时期。据李书城回忆,“弘文书院同学每晚都在自习室讨论立宪和革命的问题,最初颇多争论,以后主张排满革命的占了多数。黄克强先生在同学中一向是笃实厚重、不多发言的,但他把问题看清楚了,竟将手中的小茶壶掷地摔碎,表示他已下定决心从事排满革命,不是任何力量所能动摇的。”(33)黄兴改名就与他决意革命、振兴中华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曾告诉友人:“我的名号,就是我革命终极的目的。这个终极的目的,是兴我中华,兴我民族,克服强暴。大家要知道,我们民族做鞑虏的奴隶牛马,已有了二百余年,我们决不能长令上国衣冠,沦于夷狄,任人随便屠宰。我们要矢志复兴我民族的中华国家。而复兴民族的对象,是要克服强暴的鞑虏,删除鞑虏走狗强暴的官吏,及一切强暴的障碍,还我黄帝子孙的河山。复我中华民族的自由、平等、幸福,涤除奴隶牛马的耻辱。我要誓死实现我革命终极的目的,达到我名副其实的革命事业。”(34)显然,辛亥革命时期的黄兴,不仅对民主革命的目标和任务有了清晰的认识,而且对封建专制下的“人治”和民主政治下的“法治”有了较为深刻的理解。
民国初年,黄兴在演讲和函件中,多次指出“人治”传统的弊病,公开提倡法治,主张依法治国,用法律保障民权。在屋仑华侨欢迎会上,黄兴指出:“法国大革命人权宣言,为扫专制回复民权之铁证。诚以人权者,即人类自由平等之权能也。世界人类,无论黑白,均欲恢复固有之自由权。美国离英独立宣言,以力争人民自由而流血;人民被治于法治国之下,得享受法律之自由;人民被治于专制政府之下,生杀由一人之喜怒,无所谓法律,人民之生命财产,无法律正当之保护,民权亦从此泯绝。故共和立宪政体,以保障民权为前提。南京政府颁布约法,中华民国人民有身体居住之自由,信教之自由,言论出版之自由,此法律保障人民自由之特权,”(35)并强调“全国人民皆得受治于法律之下”,(36)“虽职官亦与平民同科……人民乃得法律上之保障,于保护国民权之中,寓尊重国家法权之意,此尤兴一得之愚所愿贡献于新造国家也。”(37)
依法治国,用法律保障民权,必须实现立宪法、行宪政。黄兴在国民党上海交通支部欢迎会上发表演说时强调:“惟现今最重大者,乃民国宪法问题。盖此后吾民国于事实上,将演出何种政体,将来政治上之影响良恶如何,全视乎民国宪法如何始能断定。故民国宪法一问题,吾党不能不出全力以研究之,务期以良好宪法,树立民国之根本。若夫宪法起草,拟由各政团先拟草案,将来由国会提出,于法理事实,均无不合。至于吾党自身,则当养成政党的智识道德,依政党政治之常轨,求达利国福民之目的,不可轻易主张急进,以违反政党进步之原则。”(38)在致王宠惠书时更指出:“尊著《宪法刍议》虽专窥全豹,其绪论中‘宪法非因一人而定,乃因一国而定,非因一时而定,乃因永久而定,’最为不刊之论。”(39)在1913年为《国民》月刊创刊撰文称:“今者,正式国会成立在即,建设共和国之第一者,首在制定宪法。宪法者,人民之保障。国家强弱之所系焉也。宪法而良,国家日臻于强盛;宪法不良,国家日即于危弱。吾党负建设之责任至繁至巨,首先注意宪法,以固国家之基础。善建国者,立国于不拔之基,措国于不倾之地。宪法作用,实有不倾不拔之性质。”(40)这就表明,黄兴对制定宪法格外重视,对宪法之治也十分期待。宋教仁被暗杀、袁世凯复辟帝制、破坏共和民国体制的严酷现实,使黄兴更加注重宪法之制定和宪法之实施。他说:“今日制定宪法,必须贯彻共和之精神,而首先注意者,应加入‘凡反对国体者,有罪’之一条。在美国,宪法实有此先例。……假使宪法明定反对国体之刑章,则一二好乱之徒不敢擅冒不韪,而一般之人亦罔敢为之附和。此为断除祸根计,为巩固国基计,所万不获已者也。”(41)
民国建立后,虽然有了《临时约法》,有了制定宪法的初识和动议,但许多人对民主与自由、礼治与法治等问题,仍然缺乏正确的认识。对此,黄兴在不同的场合,不失时机地进行宣传教育,希望新生的民国迅速进入法治的轨道。他说:“吾华立国最古,开化亦最先。制礼乐,敷五教,舜时已然,三代尤盛。吾国数千年文野之分,人禽之界,实在乎此。秦汉以后,学术庞杂,道化凌夷,君主私其国家,个人私其亲族,流毒至数百世。夷狄乘之,国种岌岌!忧时者眷怀世变,疾首痛心,主张政治革命,家庭革命。而不学小夫,窃其词不识其义,或矫枉过正,或逾法灭纪。来书所谓假自由不遵法律,藉平等以凌文化,鄙人亦日有所闻。……诸君创办昌明礼教社,以研究礼法,改良风俗为己任,深明匹夫有责之义,是宣布共和来所日夕望而不图得之者也。甚盛!甚盛!”(42)
但他对中国人的陋习和缺乏礼教的现象也给予了有力的抨击:“中国习俗恶染甚多,如食洋烟,喜缠足,不明公德,不讲卫生之类,志士呼号,已数十年,至今尚未能痛改。而其习惯之善良者,如孝友、睦姻、任鄎之类,或弃之如遗,不惜犯天下之大不韪。比来少年在学校则不师其师,在家庭则不亲其亲。似此行之个人则无道德,行之天下则无秩序。发端甚微,贻祸甚大。孟子所谓猛兽洪水之害,实无逾此。此中国习俗当湔除,当保存之不可不辨别者二也。抑又有进焉者,中外治理各不相眸;大抵中国素以礼治,洋素以法治。吾国制礼,或有失繁重者,不妨改之从同;外国立法,或有因其宗教沿其习俗者,万不可随之立异。本此意以辨其途径,导以从违,酿成善良风俗,庶几在是。”(43)同样,黄兴还对那些以为民主自由就是不受任何约束,可以胡作非为的思想认识和极端行为,也毫不留情地予以驳斥和遣责。在张振武案发生后,黄兴立即致电袁世凯,义正词严地指出:“凡有法律之国,无论何级长官,均不能于法外擅为生杀。今不经裁判,竟将创造共和有功之人立予枪毙,人权国法,破坏惧尽。兴前在留守任内办理常州军政分府赵乐群一案,舆论均谓可杀,兴犹迭开军法会审,由王军长芝祥率同会审各师长暨法官,调齐人证,悉心研讯,业经取具确供,复汇案呈请大总统,饬交陆军部复核。原期详慎议定,使成信谳,以示尊重法律、拥护人权,为各省都督开一先例。庶几共和开幕,国民不至有死于非法之惧。”“而张、方案乃如此,两事相距,为期甚迩,张、方独因一面告讦者擅定极刑,未讯供证而死。国民生命财产权专恃法律为保护,即共和国精神所托……纵使张、方对于都督个人有不轨之嫌,亦岂能不据法律上手续、率请立予正法,以快私心?”(44)显然,黄兴认为法律就是国家治理的根本方法,任何人都不能做违法的事情。自由是有限度的自由,必须限于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不能漫无法纪。他说:“共和国者,共和作事,共守和平之谓也。世界各共和国皆得自由平等,然必自由于法律之内,方有国民精神。今我国人民往往误会自由二字,溢出法律范围之外。”(45)
由此可见,在黄兴的思想观念里,自由与法律是对立统一的,不能错误地理解二者各自的内涵,更不能无端地割裂自由与法律之间的内在联系。对于民初中国社会来说,黄兴关于人治与法治的辨析,以及对自由与法律的思考,显然具有引导和启发的作用。
三、 政党与政治:社会治理之要
中国的政党萌芽于清末立宪运动。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制定的《临时约法》,以根本法的形式肯定了人民结社组党、参与政治活动的合法性,为政党政治的形成提供了宪法上的依据和保障。各派政治力量为了发展实力,争夺权利,扩大影响,纷纷组建政党,“集体结社,犹如疯狂,而政党之名,如青草怒生,为数几至近百”,(46)形成了民国初年政党的高潮。
如果说礼和法在黄兴看来是社会治理的两个重要法宝,那么政党在黄兴这里则是实现民主共和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黄兴本人虽然不是政党政治的最早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但在言行上他的确是政党政治鼓吹者的同路人。宋教仁是政党政治和政党内阁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他认为,人民是国家的主体、是主人翁,是临时约法所表述的“主权在民”的对象。他说:“夫国家有政治之主体,有政治之作用,国民为国家政治之主体,运用政治之作用,此共和之真谛也。故国民既为国家之主体,则宜整理政治上之作用,天赋人权,无可避也。”(47)“国民为国家之主人翁,固不得不起而负此维持国家之责,间接以维持国民自身之安宁幸福也”。(48)但事实上,不可能每个人都参与政治,因此要由代议机关和政府代表国民,由政党领导国民,在共和立宪国,政党实在是政治的主体,“亦可谓为实际左右其统治权利之机关。”政党进可以组织政府,实施自己的政见;退而他党执政,已党则处于监督地位,“是故政党虽非政治之极则,而在国民主权之国,则未有不赖之为唯一之常规者。”对西方国家的政党政治,黄兴大加赞扬。“一国政党之兴,只宜二大对峙,不宜小群分立”,黄兴赞同宋教仁组织国民党,也是为了实行这个原则,“藉以引起一国只宜二大对峙之观念,俾其见诸实行。”(49)
与政党相联系的是责任内阁制。宋教仁一直主张法国式的内阁制,并且由议会中的多数党组成责任内阁,即政党内阁。黄兴对宋教仁的政党内阁主张同样持赞成态度;希望在即将来临的选举之后,由国民党组织真正的政党内阁。(50)在欢迎国务总理赵秉钧和多数阁员加入国民党时,黄兴表示:“此次各国务员加入本党,实为维持民国前途起见,深望诸同志此后同心协力,共济时艰,俾成强有力之政府,各国早日承认,民国之福,亦本党之幸。”(51)在有人认为政党内阁是对袁世凯的不信任和有意设防,要求取消政党内阁时,黄兴立即出面公开解释:“国民党主张此制,纯为救国起见。”而且“政党内阁制度创始于英、法,各共和国均采用之”,“盖欲使内阁得一大政党之扶助,与国会议员成一统系,其平日所持政见大略相同,一旦发表,国会乃容易通过,不至迭起纷争,动摇内阁,陷国家于危险。故对于内阁可分负完全责任,对于总统可永远维持尊荣,而大致之计划始能贯彻。”(52)可见,黄兴对政党内阁的主张取坚决支持的态度。
但黄兴并没有停留在政党内阁制这一层面,而是寄希望政党建设和国民党之发展壮大。在黄兴看来,真正的共和政治,有待于政党对于政治问题的专门研究,欲组织强有力的政府,就必须建设强有力的政党。美、法、日等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即本于政党之力。他说:“欲追踪法、美以收共和之美果,不可不造成伟大政党,俾对于国家政治力加研究,以及稳健之主张,发表于国民之前,使全国人心有所趋向,而后得多数国民同情,政治进行可免障碍,国家之发达亦于此基之矣。”一言以蔽之,“民国成立之要素,端赖政党”。(53)因此,黄兴将国家建设和社会治理寄托在国民党的大力扩展之上。早在国民党正式成立前,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党、国民公党等协商合并时,就共同议定了国民党党纲五条,即保持政治统一、发展地方自治,励行种族同化,采用民生政策,保持国际和平。对此,黄兴亦“深为赞成”。(54)
不过,黄兴在对政党政治保持高度热情的同时,还告诫全体国民党党员,要将国民党建设成为一大政党,必须在党德和党风的建设上下大力气,甚至认为党风党德是政党政治的基础和保障。他说,国民党作为中国的民权党,要巩固共和民国,不仅应有“特别之党纲”,而且“更要有宏大之党德”。(55)在他看来,这种“宏大之党德”包含两方面内容,即对内严格要求,对外宽宏大量。他认为只有“以改造为精神,以促进为目的,以爱国为前提”,才能使党的道德水准不断提高。因此他强调“本党对于国家,以国利民福为前提,只有义务心,绝无权利心。现在为本党尽义务之日,而一切义务又须实心做到。”(56)并告诫国民党人:“凡他党之所主张,不可为无意识之反对,只当以国利民福为前提,平心静气,为稳健之批评,以待民国之抉择。”(57)“对于国民无论如何反对,本党皆宜引为已咎,归罪于自己感化力之不强。凡与他党交接,皆宜同兄弟一样,彼此互相携手,以救国家。”(58)而对于他党捏造谣言,诬蔑谩骂的行为,也应“大度处之”,“断不可尤而效之,”相信只有宽宏大度,互相提携,交换意见,“俾克砥砺观摩,收他山之助。”(59)黄兴还主张“以一特别党风造成一种党德,”指出“欲宏党风,须有包含一切之宏量。他党之攻吾也,虽含种种疾忌,而不好之点,吾人亦当引以为戒,认彼反对者为好友,不必反报,含养大度,培植党德,成一个最大政党,于攻击风潮中特立不移。”(60)
总之,在黄兴看来,中国实行政党政治是国家兴旺发达和民主幸福和谐的可取之途。而政党政治之实施,有赖于政党自身的建设与强大。政党的强大,则必须着力于党纲、党德、党风之建设。因为党纲“表示将来政治进入之方针”,(61)是衡量一个政党政治水平的标志,“党之人立于政纲之下,即犹一国之人同立于一旗之下,不可各有政见,互相攻击,宜绝对守其党纲。”(62)党德反映的是一个政党的道德水平,是政党的灵魂。党风体现一个政党的精神风貌,党风好坏关系到这个政党的存亡兴衰。他坚信,只要行其党纲,培其党德,宏其党风,必能成为一个极其伟大的党,必能造成真正的共和政治,实现国家富强、社会文明进步。
注释:
(1)薛君度:《黄兴与中国革命》,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5年版,第176页。
(2)刘泱泱《黄兴思想及活动评述》,邵德门《论黄兴及其政治思想》,赵宗颇《试论黄兴的爱国主义思想》,以上均见薛君度、萧致治合编《黄兴新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韦杰廷《论民初黄兴的社会主义思想》,萧致治《论黄兴的实业建设思想》,郭汉民《黄兴的“平民政治”思想》,芩生平《论黄兴的民主思想》,彭平一、黄林《黄兴教育思想刍议》,王兴国《黄兴伦理思想述评》等,均见林增平、杨慎之主编《黄兴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3)中国传统儒家“四书”中的《大学》,将社会治理分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个层次,而且这八个层次是环环相扣的一个系统。如果说格物、致知两层次大致是哲学思想研究的重点,那么,修身、齐家两层次就是社会思想研究的所在。《大学》又说:“自天下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未治者否矣。”可见,“八条目”中,修身是根本。(陆学艺、王处辉主编:《中国社会思想史资料选辑》民国卷上,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总序,第9-10页。)
(4)薛君度等、杨慎之译:《黄兴与中国革命》,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5年第2版,第1页。
(5)萧致治:《黄兴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21页。
(6)萧致治:《黄兴评传》,第21页。
(7)李云汉:《黄克强先生年谱》,第18页,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3年版。
(8)陈维纶:《黄克强先生传记》,第23-24页。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3年版。
(9)杜元载主编:《黄克强先生纪念集》,第122页,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3年版。
(10)《大戴礼记·礼察篇》。
(11)《论语·礼运》。
(12)《乐记》。
(13)《论语》。
(14)《孟子》。
(15)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第101页。
(16)《黄兴集》,第192-193页。
(17)《黄兴集》,第233页。
(18)《黄兴集》,第204页。
(19)萧致治:《黄兴评传》,第121-126页。
(20)《黄兴年谱》第69页。
(21)《黄兴集》第17页。
(22)李书城:《辛亥革命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第196-197页。
(23)薛君度:《黄兴与中国革命》,第170页。
(24)薛君度:《黄兴与中国革命》,第169页。
(25)薛君度:《黄兴与中国革命》,第170页。
(26)【日】沟口雄三:《中国思想史:宋代至近代》,北京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145-170页。
(27)陶希圣:《中国政治思想史》,台北食货出版社1972年版,第二册,第151页。
(28)余英时:《历史与思想》,台北经联出版公司1981年版,第31-46页。
(29)黄金麟:《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1895-1937)》,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108页。
(30)黄金麟:《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1895-1937)》,第171页。
(31)黄兴:《在湖南学界欢迎会上的演说》,《近代史资料》总64号,第33页。
(32)黄蔡二公略编辑处:《黄克强先生荣衰录》,1918年长沙出版,第21页。
(33)李书城:《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辑,第181页,中华书局1961年。
(34)李贻燕:《纪念黄克强先生》,杜远载主编:《黄克强先生纪念集》,第44-45页。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3年版。
(35)《黄兴集》,第381页。
(36)《黄兴集》,第251页。
(37)《黄兴集》,第211页。
(38)《黄兴集》,第309页。
(39)《黄兴集》,第310页。
(40)《黄兴集》,第316页。
(41)薛君度等编:《黄兴未刊电稿》,第105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42)《黄兴集》,第196页。
(43)《黄兴集》,第196-197页。
(44)《黄兴集》,第249-250页。
(45)黄兴:《在湖南普通全体大会上的演说》,《近代史资料》,总64号,第30页。
(46)丁世峰:《民国一年来之政党》,《国是》第一期,1913年5月。
(47)《宋教仁集》,下册,第459页,陈旭麓主编,中华书局1981年版。
(48)《宋教仁集》,下册,附录。
(49)《宋教仁集》,下册,附录。
(50)薛君度:《黄兴与中国革命》,第143页。
(51)《黄兴集》,第278页。
(52)《黄兴集》,第300-301页。
(53)《黄兴集》,第261页。
(54) 《黄兴集》,第246页。
(55) 《黄兴集》,第238页。
(56)《在醴陵国民党支部欢迎会上的演说》,(1912年11月18日),《近代史资料》,总第64号。
(57)《黄兴集》,第289页。
(58)《在醴陵国民党支部欢迎会上的演说》,(1912年11月18日),《近代史资料》,总第64号。
(59)《黄兴集》,第289页。
(60)《黄兴集》,第240页。
(61)《黄兴集》,第289页。
(62)《在醴陵国民党支部欢迎会上的演说》,(1912年11月18日),《近代史资料》,总第64号。
(胡波系广东省中山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教授)
【在“礼”与“法”之间——黄兴社会治理思想述评】胡波[黄兴诞辰140周年纪念专辑]
2015-01-03 11:28:47 来源: 评论:0 点击:
内容摘要:黄兴的社会治理思想,主要体现在礼和法两个层面。先礼后法,礼法并重,法治取代人治,在宪政框架下实行政党政治,是黄兴社会治理思想的中心内容。关键词:黄兴 社会治理 礼治 法治 政党政治 在辛
分享到:
相关热词搜索:黄兴 社会 治理 思想
上一篇:【改革开放以来的黄兴研究】刘泱泱[黄兴诞辰140周年纪念专辑]
下一篇:【华兴会与甲辰长沙起义】梁小进[黄兴诞辰140周年纪念专辑]
分享到:
频道总排行
频道本月排行
- 33【烽火间隙的酬唱和风雅】王金华2022年4期总130
- 32【铁血铸丰碑——浏阳党史人物简述】邓继团2021年3期总125
- 29【元代名人邓谦亨及其浏阳后裔族群考】邓继团2022年4期总130
- 20【东汉邓禹其人及晚清重修邓禹墓考】邓继团2023年1期总131
- 12【文强非毛泽东表弟考】邓继团2018年2期总112
- 11【芋园、芋园主人与芋园文化】李崧峻2011年2期总84
- 11【于光远曾两次来安化马渡调研—一份与“马渡调查”有关...
- 11【近现代日记中的李合盛】尧育飞2023年2期总132
- 10【浏阳算学社】耿静好 林洪2023年3期总133
- 10【长沙城建大事记(上)(公元前475年—公元1850年)】陈先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