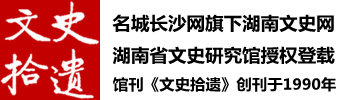黄兴,原名黃轸,字廑午,后改名克强,湖南长沙人。 与孙中山一样,都是杰出的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家,辛亥革命的主要领导者,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他们从1905年7月在日本相识,到1914年6月在日本分手,彼此共事有九年之久。他们一起共同组织中国革命同盟会,策划多次反清武装起义,领导了辛亥革命,组建了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但在“二次革命”后,两人却因意见分歧,终于分手。黃兴与孙中山的分手,从表面上看,虽缘于两人对中华革命党纲和入党手续存在不同看法,但实际上他们自相识后,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一直存在分歧。只是过去设有人去专门进行研究罢了。这里,就他们的关系略作论述。
一、反清革命、争取民族独立是黃兴与孙中山走到一起的根本原因
1904年秋,黄兴等在长沙发动反清起义失败后辗转到达日本。在日本,有幸结识了宫崎寅藏(即宫崎滔天),并很快成为好友。宫崎也是孙中山的好友。1905年7月,孙中山由欧洲到达日本,物色革命志士,发展革命力量,宫崎隨即向孙中山推荐了黃兴。宫崎对孙中山说:黄兴是个“非常人物”,孙中山此时需人甚急,迫不急待地要与黄兴见面。在宫崎的安排下,孙黃两人在黃兴的东京牛込区临时寓所相见,隨后一同到附近一家名叫“凤乐园”的中国歺館,两人就“革命的话题,推心置腹,暢所欲言,就象多年的老朋友一样”,大有相见恨晚的意思。两人足足谈了将近两个小时,因“专心谈话,两人酒菜未沾,直到最后才举杯庆贺”。 孙黃所谈的具体内容我们已不得而知,但推测所谈内容总不外是反清革命、争取民族独立这方面的内容。
黄兴回忆说他幼时因阅读太平天国史,而萌发“革命的动机”,又见“清廷政治腐败,纲纪不修,外人不以人类视我”,益坚“革命之决心”。 而孙中山自幼爱听老一輩讲“洪杨杀鞑子”的故事,以“洪秀全第二”自比,所以,“村童与乡人(干脆)称他洪秀全” 反清革命,争取民族独立,是黃兴与孙中山走到一起的根本原因。早在两人相识的十年前,1894年孙中山就在檀香山秘密成立了革命团体兴中会,黄兴与陈天华、刘揆一、宋教仁、章士钊、姚宏业等则在1903年11月,在湖南长沙秘密成立了革命团体华兴会。黄兴被举为会长。不过两人虽在用革命暴力手段推翻清朝统治这点上一致,但在革命组织上、革命宗旨上还是存在明显的差异。孙中山的兴中会的成立早于华兴会九年,其成员多为海外华人华侨。孙中山当时的视野较高,明确以“建立合众政府”为革命最终目标。而华兴会成立时的宗旨是“扑灭满清”,“直搗幽燕,驱除鞑虏”。 主张采取“地方革命,以湘省为根据地,即雄踞一省与各省纷起之法”,成功之道“在于广泛联络会党、军队和学生采取一致行动” 与华兴会成立的同时,还成立了两个小团体:一个是同仇会,“专为联络哥老会,策动会党参加起义”;一个是汉黄会,专为“运动军队参加起义”。 由此可见,兴中会、华兴会虽同为两个革命团体,但在人员构成、革命宗旨等方面明显存在差异,前者对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比较了解,容易接受;后者虽出于现实的考量,但种族革命的色彩较浓。这种差异在后来孙、黃革命合作中日益凸显,直接影响了革命的进程。
孙、黃相识的第二个月,1905年8月,孙中山代表兴中会,黃兴代表华兴会,联合部分在日的光复会员,计70余人,在东京赤坂区桧町三番黑龙会所在地宣布成立中国革命同盟会。对于与孙中山的兴中会联合问题,华兴会内部意见并不一致。据宋教仁在《宋漁父日记》中说:7月29日,他与陈天华应邀到黄兴寓所,“商议对于孙逸仙之问题(指与兴中会联合)。先是孙逸仙已晤廑午(即黄兴),欲联络湖南团体中人,廑午已应之,而同人中有不欲者,故今日集议。既至,廑午先提议,星台(陈天华)则主以吾团体与之联合之说,廑午则主形式上入孙逸仙会,而精神上仍存吾团体之说,刘林生(即刘揆一,字霖生,一写林生)则主张不入孙会说。余(宋教仁)则言,既有入会与不入会之别,则当研究将来入会者与不入会者之关系何如。其馀亦各有所说,终莫能定谁是,遂以“个人自由”一言了结而罢” 从这段记载来看,对于加入孙中山的兴中会,华兴会内部存在同意和不同意两种意见。黃兴是一个重然诺、讲信用的人,他既表示华兴会愿意加盟兴中会,当然不会反悔。但他又是一个讲究民主、平等待人的人,不会强制持反对意见的人去入会。在他的努力下,最终采取个人自由参加的办法,凡愿意者“各人签名”,“自书誓书”,“传授手号”。刘揆一“因持异议”,没有加入。 值得注意的是,黃兴本人是“形式上入孙逸仙会,而精神上仍存吾团体之说”,虽然加入了同盟会,但在思想上、精神上仍坚持原先华兴会的“誓扫胡虏,恢复中原” 宗旨。与同盟会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平均地权,建立民国”的纲领存在很大差异。在某种意义上,华兴会与光复会的宗旨“光复汉室,还我河山”接近,以种族革命为主要目的。这样做,从政治上说是讲不通的,已加入了同盟会,就得遵守同盟会的纲领。但当时的中国政党水平就是如此。当时中国的政党还处于萌芽状态,朋党盛行,结义行为较为普遍,同盟会还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政党。“二次革命”失败后,就今后如何开展革命,孙、黃意见对立,孙中山就曾指责黃兴有自己的的“亲信部下”,搞小团体,实际就是批评黃兴仍信任原华兴会会员、保留原先华兴会的“小圈子”,黃兴坚决予以否认,不承认有此事。在同盟会成立大会上,孙中山重申了他的革命主张,“革命之目的系建立共和政府,效法美国,除此之外,无论何项政体皆不宜于中国”。 这一主张无疑代表了当时中国革命的最高水平,要远远高于华兴会,这也是孙中山之所以成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精神领袖的原因。根据黃兴的提议,大会一致推举孙中山为总理,黃兴为执行部庶务,居协理地位,负责实际工作,总理不在时,可以全权处理会务。
二、革命宗旨不同,斗争策略严重分歧
同盟会成立后,经黄兴提议,将其与宋教仁主编的《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改为《民报》,作为同盟会机关报。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上第一次將同盟会纲领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即三民主义。对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同盟会內并非所有人表示赞同。蔡元培说:同盟会“会旨虽有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诸义,但会员大率以驱除鞑虏为唯一目的”。 以章太炎、陶成章为代表的原光复会员始终秉持“一民主义”(民族主义),章氏甚至认为革命成功后,是行宪政还是君主制,都无关紧要。当时不赞同三民主义的主要是原光复会员,华兴会会员抵制和不接受的不占主要。
孙中山因为清廷所不容,清政府要求各国驱逐孙中山,所以,不仅国内不能逗留,在日本、南洋同样不能自由居住。经过同盟会内部商讨,决定“国内一切革命计划委托黄兴与胡汉民两人主持”,孙中山则“专发展国外党务并筹款,以济革命之需”。此后,孙、黄先后于1908年策划了钦州起义和云南河口起义,两次起义虽告失败,但两人并未气馁,黃兴决定于1910年发动更大规模的广州起义。起义前,黃兴起草了一份《致总理论革命计划书》,分析了当时的敌我形势,广东新军的情况,革命力量与会党联络情况,在广州发动起义的诸多有利因素,并成立了统筹部,组织了“选锋队”(敢死队)。并派遣自己儿子黃一欧秘密打入广州防营内,与新军联络。三二九起义发动后,黄兴亲自率队攻打总督衙门,这次起义由于指挥问题和混入奸细,遭到惨败。70多名志士壮烈牺牲,他们的遗骸后来安葬于黃死冈,即今天的黃花冈七十二烈土墓。起义中,黃兴本人也受了重伤,后在党人徐宗汉的掩护下得以脱险和康复。他的英勇牺牲精神赢得广大革命志士的肯定:胡汉民说:黃君“广州三二九起义,乃毅然不顾一切,以牺牲之精神,为开国之先导,此先生不可没也”。 孙中山对黃兴身先士卒、冲锋在前的英勇行为也给予了高度评价:“黃君一身为同志所望,亦革命成功之关键”,但对他亲自督队认为非其所宜:“彼之职务,盖可为更大之事业,则此个人主义(指其亲自冲锋上阵),非彼所宜为”。
黃花冈起义前,孙中山的革命方略是先在南方一省或数省取得胜利,然后再向长江流域、黃河流域及其他地区发展,最后夺取全国胜利。因此,革命活动,武装起义始终放在两广和西南地区。“这种东一冲西一击的斗争方法,总是不能奏效”。 黃花冈起义失败后,黃兴、宋教仁等对革命屡遭失败的原因进行反思,认为“天下事断非珠江流域所能成,主张长江革命”。为此,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制订革命上、中、下三策:上策为中央革命,各省同时发动,最后一举攻下北京;中策为长江革命,先立政府,然后北伐,攻占北京;下策为边疆革命,即象先前做的那样。黄兴在致谭人凤函中说:“能争汉上为先着,此为神州第一功”。 长江革命的重点在两湖,计划在1913年发动起义,其注意点“尤在武汉”。长江革命实际上否定了孙中山的边疆革命方略,而中部同盟会虽仍遥奉孙中山和东京同盟会总部,实际上它是一个不受同盟会总会指挥的独立的革命团体。长江流域是中国的经济重心,交通发达,革命势力较强,会党活跃,长江革命成功的希望较大。当时黃兴的计划是:“以武昌为中枢,湘、粤为后劲,宁、皖、陕、蜀亦可同时响应以牵制之,大事不难一举而定”。 孙中山当时对长江革命有何想法,我们已不必再去讨论了,因为后来武昌起义的爆发和辛亥革命成功证明了长江革命方略的正确。
武昌起义爆发后,湖北地区革命党人抱着平民革命的思想,推举新军协统黎元洪为都督府都督。蒋翊武说:“武昌首义为真正之平民革命,只要顺应革命,举谁为都督都可以。湖北举义,以湖北人为领袖最为适宜” 虽说“平民革命”,但还浸淫于反满复汉的种族革命的理念。黃兴受武汉革命党人的电请,立即由港起程赴鄂,指挥起义军同北洋军作战。正如前面所说,黃兴虽身为同盟会负责人,但在精神上仍抱持原华兴会“直捣幽燕,驱除鞑虏”的宗旨,在此后的斗争中,竟也表只要袁世凯顺从共和,推倒清室,就推举袁世凯为未来民国的大总统。黄兴的这一主张除了他的种族革命的思想外,还与先前袁世凯与他的一次秘密接触有关。据黃兴说,早在1909年宣统改元这年,袁世凯就曾秘密派人同他接触,共商一起推翻清朝。“当袁世凯未解职(回籍)之先,是时兄弟(黄兴自谓)寄留南京,有直隶总督杨士驤代表人来会,据称宫保(指袁世凯)此时地位颇觉危险,甚愿与革命党联合,把清室推翻,复我故国。兄弟当时亦曾答以袁君有此思想,诚为吾辈革命党人所赞同。……然代表人去后,终不见袁氏有些许举动,未几,袁即辞职回籍。以意度之,或因有为难之处,故不能动也”。 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被迫起用袁世凯,袁氏的复出自然引起黃兴的高度关注。而袁氏此时也在大肆玩弄两面手法,一面令北洋军猛攻武昌,一面暗中派人与党人谈和。黃兴自上一次与袁氏来人接触后,遂也萌发利用袁世凱的念头。他向袁氏提出:只要他顺应共和,推倒清室,就推举他担任未来的大总统。他甚至希望袁世凯成为中国的拿破仑、华盛顿。1911年11月9日,在致袁世凯的信中写道:“明公之才能,高出兴之万万。以拿破仑、华盛顿(比之),即南北各省亦当无有不拱手听命者”。 但蔡元培对黃兴的看法不以为然,说:“弟之以为袁世凯者必不至复为曾国藩,然未必肯为华盛顿,故彼之出山,意在破坏革命军,而即借此以为帝”。 后来的历史证实了蔡元培的预见。12月9日,黄兴在致汪精卫的信中又说:“项城雄才英略,素负全国重望,能顾全大局,与民军为一致行动,迅速推倒滿清政府,令全国大势早定,外人早日承认,此全国人人所仰望。中华民国大统领一席,断推举项城无疑”。 为了说服持不同意见的人,他还搬出袁世凯同为汉人:“民军之起义无非欲推倒清室,今袁世凯求和,声令清帝退位,是政权已归我汉人之手,同心协力,建一真正共和之国家”。而“其时袁氏之部下亦皆汉人,我汉人不应互相残杀”,革命党“本人道之观念,故许其议和”。 “长江革命”中原定挥师北伐,占领北京,但此时黄兴并不积极。黃兴后来解释说:“只因袁氏当时戴假面具赞成共和,吾人以革命之目的已达,加以吾党以人道相待,不思再动干戈,至人民涂炭,故让总统于袁氏耳”。 当时各省都督府代表聚会南京,准备组织政府,拟举黃兴为大统领,黃兴力辞不就,表示“万一辞不获已,兴只得从各省代表之请,暂充临时大元帅,专任北伐,以待项城举事后即行辞职,便请项城充中华民国大统领,组织完全政府。” 而袁世凯在得到黃兴等革命党人的确切保证后,抓紧对清廷的“避宫”行动,以便早日将未来国家的政权夺到手。
武昌起义爆发时,孙中山正在海外,他是在美国一家报纸上得知武昌起义的消息的。于是连忙坐船回国。对于武昌起义后国内发生的一切,他当然不知,对于黄兴等革命党人计划推举袁世凯为未来大总统一事,无从知晓。12月22日,孙中山回到香港,其时他可能已知道国内的一些政情,所以,胡汉民劝他留在广东,主持广东政务,孙中山没有同意。25日到达上海后,立即召开同盟会领导人会议,力主北伐,反对南北议和,对于举袁氏为未来大统领从心里不赞成。对黃兴等人作法表示强烈不满。为了实现他“建立民国”的理想,仅用了五天时间,迅速组建了由革命党人和江、浙两都督及起义海军负责人联合组成的临时中央政府,并于六天后,即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宣告成立,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然而,南北议和、关于袁氏推倒清室、顺应共和,就举其为大总统,各省都都督府代表会议早有成案,中外皆知,孙中山无法去推翻更改,他最后只好无奈地接受“辞职”这一残酷的现实。孙中山和革命党人流血牺牲奋斗了十多年,最终却因“举袁为大总统”这一着而断送了革命。这大概是辛亥革命时期乃至以后一个很长时间,孙中山和一切反对这种举措的革命党人最为纠结的事,一切都做好了,等着孙中山与革命党人去接受。黃兴这一举指,可以说是“聚九州之铁铸此大错”。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种种倒行逆施,日益暴露,直接影响了黃兴在党人内部的威信,而孙中山威望日益增腾,与此不无关系。而“二次革命”中他与孙中山的分歧及革命失败后与孙中山的“两情分手”,再加上袁世凯悍然帝制自为,这一切更增加了人们对他“雄而不英”(吴稚晖语)”的看法。民国二十年代以后,黃兴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执政的国民党人对他少有纪念,簿书更少有宣传,这固然因他早逝,但在很大程度上与他在袁世凯问题上这一错误决策有关。
对于辛亥革命的失败,须有对当时社会整体性的反思。辛亥革命时期,“驱除鞑虏,恢复汉室”的种族革命思想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不仅革命党人中的大多数持这一思想,而且社会上也普遍存在“以汉替滿”的倾向。清军入关,大肆屠杀汉族人民,对各族人民实行残暴的种族统治,以会党为形式的秘密反清斗争几乎与清朝相始终。“驱满兴汉”、“以汉替满”成为全社会的诉求。作为汉族官僚的袁世凯,正是利用了革命党人头脑中这种种族革命思想,以及当时人们对他遭受清廷排斥打压的“同情”,施展其阴谋诡计,最后夺得了政权。在其帝制野心还没有完全暴露之前,多数人还不能能看清他的反动真面目。因此,从这一层面上说,辛亥革命的失败,又不独是黃兴一人的过错,而是一代中国人迷失所致。
1912年2月,宣统宣布退位,孙中山迫于内外压力,被迫辞去临时大总统。黄兴也因南京临时政府裁撤,由陆军总长而变为南京留守。6月14日,留守解职。内察国情,外观时局,深感当初自己决策之非和失去政权的伤痛。10月25日,是黃兴39岁生日。在乘坐“楚同”舰回湘途中作了一首感怀诗:“卅九年知四十非,大风歌好不如归;惊人事业付流水,爱我田園想落晖。入夜魚龙都寂寂,故山猿鹤正依依;苍茫独立无端感,时有清风振我衣”。 诗中对交出政权、革命失败充滿了无限凄凉之感。
三、“二次革命”中与孙中山意见对立,继因拒绝加入中华革命党,
最终“两情分手”
1913年袁世凯派人暗杀了宋教仁。“宋案”真相查明后,就如何解决,黃兴和孙中山又一次意见分歧。孙中山主张举兵讨伐袁世凯,并吁请日本提供武器和款项。官崎同意孙中山的意见,为之奔走,力促其成,只因日方所提条件苛刻,未能实现。 黄兴认为现在清朝已经退位,南北统一,“但能以政见相折冲,不愿以武力相角逐,”主张“求诸于法律”,通过法律途径加以解决。 他对于袁世凯铲除革命势力的阴谋还缺乏足夠的认识,把革命党人同袁世凯之间的矛盾看成是“兄弟阋墙之争”。由于孙、黃两人意见分歧,以致孙中山的讨袁计划不能说处处受阻,至少着着落后。直到袁世凯派重兵南下,“假鄂以逼赣,据沪以逼苏”,迫于自卫,苏、赣、皖、湘、粤等省方才被迫宣布“独立”,举岑春煊为讨袁军大元帅,进行“不得已之战争”。然而黃兴也清醒地看到:其时“南京已非民党势力”所控制,讨袁军“饷糈枪弹均缺,或当不免一败”,如“我奋斗到底,將使大好河山遭受破坏,即获胜利,全国亦将糜烂,且有被列强瓜分之虞”。 当时黄兴还考虑到:“且其时知大势已去,不宜再为负隅之计,以徒劳兵事,而致引起国民无穷之恶感,反不如留后来之地步,以作第三次革命之工夫”。 当时民国初建,民心思安,对于革命已感厌倦。革命党人讨袁比反清革命更难,当初清廷已是众矢之的,要求推翻它的人多,革命党人反清斗争深得人民同情与支持。而现在讨伐的袁世凯是民国的大总统,袁世凯是用“孙、黃捣乱”、“破坏民国统一”的“罪名”来讨伐革命党人的,党人斗争取胜的难度很大,与其引起国民无穷之恶感,不如暂且退却,以图将来。“二次革命”的失败,缺少民众的支持亦是一因。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黃兴等一批革命党人再次流亡日本。孙中山事后追维,认为这次失败主要是黃兴不与他合作,矛头直指黃兴。在致黄兴的函中说:“若兄(指黄兴)当日能听弟(孙中山自谓)言,宋案发表之日,立即动兵,则海军也,上海制造局也,上海也,九江也,犹未落袁氏之手,况此时动兵,大借款必无成功,则袁氏断不能收买议员,收买军队,收买报館以推翻舆论。此时之机,吾党有百胜之道,而兄见不及此。及借款已成,大势已去,四都督已革,弟始运动第八师营长,欲冒险一发,以求一死所,又为兄所阻不成。此等情节,则弟所不满于兄之处”。 黄兴对此不以为然,在复函中予以反驳:“宋案发生以来,弟即主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意指用暗杀手段),先生由日归来,极力反对。即以用兵论,忆最初弟与先生曾分电湘、粤两都督,要求其同意,当得其复电,皆反对,陈其不可。今当事者皆在,可复询及之也。后以激于感情,赣省先发……先生欲赴南京,……且轻身陷阵,故弟愿以身代先生赴南京,实重爱先生,愿留先生以任大事,此当时之实在情形”。 认为“二次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乃正义为金钱、权力一时所摧毁,非真正之失败”。并力劝孙中山“不为小暴动以求急功,不作不近情言以骇流俗,披心剖腹,将前之所是者是之,非者非之”。组织干部,计划久远,共同努力,分道进行,革命没有不成功的。 但孙中山没有接受黃兴的意见。
孙中山执定“二次革命”的失败,是革命党人不听从他的指挥所致。孙中山的看法有一定道理,自辛亥革命成功,同盟会改组国民党,许多党人以功臣自居,腐化坠落,早已丧失了革命意志,革命阵营已呈一盘散沙状态。“二次革命”失败后,许多人离开了革命队伍,甚至卖身投靠袁世凯,加害自己同志。而部分逃亡到日本的革命党人也“均极灰心,以为我们已得政权尚还归于失败,此后中国实不能再讲革命,对前途悲观绝望”。 有鉴于革命力量的软弱涣散,为了重新凝聚革命力量,实现“掃除专制,建设完全民国”的理想,孙中山计划改组国民党,但未成功。只好另组新党一一中华革命党。规定凡入党的人必须完全“服从文(孙中山)一人”。“此次重组革命党,首以服从命令为唯一之条件,凡入党各员,必自甘愿服从文(孙中山)一人,毫无疑虑而后可。”“你们许多人不懂得,见识亦有限,应该服从我”。“我就是革命”。“我敢说,除我之外,无革命之导师”。同时还规定:“在向领袖宣誓时,须按指模(中指)”。并将党员分为数等。 中华革命党的组建,尤其是实行党魁集权制,是孙中山在革命遭受严重挫折、革命力量处于严重软弱涣散的情况下,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延续革命的不得已之举,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但这种用封建落后的组党方法有违民国民主政治。因而遭到黃兴、李烈钧等一批革命党人的反对。黃兴直指孙中山这一作法违背了孙中山自己平日所倡导的民主平等之主张:“不愿先生反对自己所提倡之平等自由主义”。并拒绝参加该党。孙中山复函黃兴,望黄兴同意再给他进行“第三次革命”,“以两年为期,过期不成,即让兄(指黄兴)独办”。并要黄兴劝阻所谓“亲信部下”不要散布“中国军界皆听黃先生之令,无人听孙文之命”、“孙文所率者不过一班无知少年学生及无饭食之亡命者”之类的话。黃兴见后很不高兴,复函说:“革命原求政治之改良,此乃个人之天职,非为一公司之权利可相让度、可能包办者也,以后请先生勿以此相要”。“弟并未私有所标帜以与先生异,故绝对无“亲信部下”名词之可言。若以南京同事者为言,皆属旧日之同志,不得谓之“部下”。今之往来弟处者,半多先生会内之人。至词之有无,弟不得而知”。 当时不赞同孙中山做法,拒绝参加中华革命党人不少,李烈钧、李根源、陈炯明、柏文蔚、钮永键、程潜、熊克武、谭人凤等都是,他们也都是跟隨孙中山多年的老同盟会员。黃兴的驳斥是对的。但他们的意见对立直接造成国民党内部分成两派,党务一时不能统一。而对黄兴来说,精神压力更大。“戟指怒骂,昔年同志,贻书相讥,谤语转移,哓哓嗷嗷”等等,不一而足。他一再反复解释:他与孙中山之间只是“为此不妥之章程(指中华革命党章程),未免有些意见不合处”。“吾非反对孙先生,吾实要求孙先生耳”。 他原名黃轸,就是汲取太平天国后期领导人争权夺势自相残杀的教训,“前车既辙,来轸方輶”。“太平天国起事初节节胜利,发展很快,但因几个领袖们互争权利,终至失败,我们要引为鉴戒”。 深知在日本很难再与孙中山共处,加上陈其美、戴季陶、居正等人编造散布他携带巨资在日大兴土木,修建公馆之类 的谣言,弄得黃兴很生气。“现在国事日非,革命希望日见打消,而同志间犹自相戕伐若是,悲愤不胜”,遂决定与孙分手,远赴美国,为“使中国成为一个实至名归的共和国”,继续奋斗。孙中山与黃兴毕竟共处多年,深知其人其才,便在黃兴赴美前夕,单独设宴送行,并集古诗句书联:“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以赠“克強同志”。
孙、黄的分手只是暂时的。黃兴在美国仍然维护孙中山的革命领袖形象。1915年袁世凯悍然帝制自为,孙中山得知,立即开展护国讨袁斗争。1916年,应孙中山的电请,黃兴由美洲坐船回国,重新回到昔日的革命队伍。途中他感慨万端,赋诗述怀:“太平洋上一孤舟,抱载民权与自由;愧我旅中无长物,好风吹送到神州”。 同年10月,因胃出血不治,病逝上海。灵柩安葬长沙岳麓山。北京政府为之举行国葬,以悼念他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所作的不朽功绩。“克强先生心思縝密,措置周详,辅佐总理进行革命,厥功伟矣”。(林森语)“克强先生开国元勳,目光远大,不畏牺牲,为国为民,为万世开太平,文武合一,今之圣人”。(冯玉祥语) 当年在东京时,章太炎、陶成章等光复会攻击孙中山“借募款以肥私”、企图要罢免孙中山,夺取同盟会的最高领导权,是黄兴挺身而出,大力维护孙中山的领袖地位, 其高风亮节,赢得了革命党人的高度赞誉。有人说:“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 这些评价,无疑是十分中肯的。他无愧为近代中国民主革命史一位人格高尚的革命家。
黃兴和孙中山都是立志献身国家和民族的人,他们都将自已的一生无私地献给了伟大的中国民族民主革命。他们的分手是缘于斗争策略和方法上的分歧,他们只是一时“分手”,而不是“分道扬镳”,他们的“道”还是共同的,即使分手时,也还是在同一个“道”上,这个“道”就是推倒专制,在中国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他们的结合与分手,同时也从一个侧面,让我们看到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注释:
1912年5月,黃兴在与李贻燕等人谈话时,说到自已名字的由来。他说少时阅读太平天国历史而萌发“革命动机”,但是看到后来太平军领导人“有了私心,互争权势,自相残杀”,以致功败垂成,不觉“气愤腾胸,为之顿足”,遂取名“轸”字,就是“前车既覆,来轸方輶”,汲取太平天国失败的惨痛教训。文明国编:《黄兴自述》第3頁,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以下简称《黄兴自述》。
黃一中:《先父黄兴和孙中山的革命友谊》。《苏州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黄兴自述》第3頁。
黃兴:《革命之动机》。《黃兴自述》,第3頁。
王杰:《平民孙中山》,第34頁。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
黃一欧:《回忆先君克强先生》。《黄兴自述》第369頁。
黃绍强:《纪念先祖父黃兴》。《黄兴自述》第3一4頁。
黃一欧:《回忆先君克强先生》。《黄兴自述》第369頁。
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第124頁。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刘揆一后来于1907年1月加入同盟会,2月,代理执行部庶务干事。同年因孙、黄去越南,代行总理职务,主持东京本部工作,直至武昌起义。
黄兴:《喜见共和之成功》。上海《民立报》1912年2月15日。
孙中山:《民权主义第四讲》。《孙中山选集》第745一746頁。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蔡元培:《宋教仁“我之历史”序》。湖湘文库《宋教仁集》。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
文明国编:《黃兴自述》第411頁。
胡汉民:《黃兴致总理论革命计划书》阅后题语。上海驰翰拍卖公司印行资料,上海,2013年。
文明国编:《黃兴自述》第411頁。
林增平:《辛亥革命》第287頁。成都,巴蜀书社,1982年。
《孙中山在上海文献档案资料》第87頁。上海,上海书店,2008年。
李新、孙思白主编:《民国人物传》(一)《宋教仁传》第45頁。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一集。《黃兴自述》第62頁。
万迪庥致曾省三书。上海驰翰拍卖公司印行资料。
黃兴:《在旧金山民国公会宴会上的演讲》。《黃兴自述》第300頁。
《黃兴集》第82頁。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李华兴:《人世凯模蔡元培》第56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黃兴:《在美洲中国国民党支部召开的“二次革命”纪念大会上的演讲》。《黄兴自述》第294頁。
黄兴:《在旧金山民国公会宴会上的演讲》。《黃兴自述》第304頁。
黃兴:《在美洲中国国民党支部召开的“二次革命”纪念大会上的演讲》。《黄兴自述》第294頁。
荣朝甲编:《缔造共和英雄尺牍》。《黄兴自述》第78頁。
黄一欧:《回忆先君克强先生》。《黄兴自述》附录,第369、387頁。
黄一欧:《回忆先君克强先生》。《黄兴自述》附录,第369、387頁。
上海《民立报》1913年7月18日。《黃兴自述》第264頁。
黄兴:《关于“二次革命”可能失败的声明》。《自兴自述》第273頁。
黄兴:《在美洲中国国民党支部召开“二次革命”纪念大会上的演讲》。《黄兴自述》第293頁。
孙中山复黃兴书。《黃兴自述》第291頁。
黃兴复孙中山书。《黃兴自述》第293页。
黃兴复孙中山书。《黃兴自述》第293页。
黄彦主编:孙中山著作丛书《论改组国民党和召开“一大”》第138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
《孙中山集外集》第22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又见《中华革命党民国三年十七次会议纪录》(上海驰翰拍卖公司2013年2月刊印资料)
黃兴复孙中山书。《黃兴自述》第293页。
黃兴与梅培的谈话(1914年10月5日)《黄兴自述》第317頁。
黄绍强:《纪念先祖父黄兴》。《黄兴自述》第6頁。
据黃兴说:“二次革命”失败后,为防袁世凯迫害自已在乡下的祖母、母亲和子女,在谭延闓的帮助下,将他们护送至上海。但一家大小十来口开销很大,生活不易。到东京后,租屋也很贵。于是黃兴便不得不变卖手中平昔收藏的字画,在东京郊区购买一块价格比较便宜的土地,建造房屋数间,安置家小。陈其美、戴季陶说他在东京造公馆,意在逼黃兴“顺从”孙中山,“此事实由入会问题(指黃兴拒绝加入中华革命党)”而起。并借此打击黃兴,贬低他在革命队伍中的形象。黄兴赴美,又有人散布说黃兴挟赀逃跑。对此,孙中山也不信,认为这是谣言。
王杰:《平民孙中山》第67頁
王杰:《平民孙中山》第67頁
林森、冯玉祥对黃兴的评价均见上海驰翰拍卖公司2013年1月所刊革命文献资料《黄兴致总理孙中山述 革命计划书》跋文。
黃绍强:《纪念先祖父黃兴》。《黃兴自述》第1页。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从“相见恨晚”到“两情分手”】谢俊美[黄兴诞辰140周年纪念专辑]
2015-01-03 11:25:20 来源: 评论:0 点击:
黄兴,原名黃轸,字廑午,后改名克强,湖南长沙人。 与孙中山一样,都是杰出的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家,辛亥革命的主要领导者,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他们从1905年7月在日本相识,到1914年6月在日本分手,彼此共事有
分享到:
相关热词搜索:黄兴 孙中山
上一篇:【从黄兴之六佚文观其民初的思想实践活动】周兴樑[黄兴诞辰140周年纪念专辑]
下一篇:【法国官方档案中的黄兴】邵雍[黄兴诞辰140周年纪念专辑]
分享到:
频道总排行
频道本月排行
- 20【东汉邓禹其人及晚清重修邓禹墓考】邓继团2023年1期总131
- 11【于光远曾两次来安化马渡调研—一份与“马渡调查”有关...
- 10【浏阳算学社】耿静好 林洪2023年3期总133
- 10【长沙城建大事记(上)(公元前475年—公元1850年)】陈先枢...
- 7【新发现柳直荀1921年三篇文章解读(一)】李忠泽 罗慧...
- 7【纪念辛亥元勋黄兴 揭秘民国建立真相】吴欢[黄兴诞辰1...
- 7【烽火间隙的酬唱和风雅】王金华2022年4期总130
- 7【保存陈毅安烈士五十四封遗书的李志强】焦广2021年4期总126
- 6【走笔洪江古商城】解黎晴2023年2期总132
- 6【长沙县署迁徙与营建史略】杨锡贵2018年3期总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