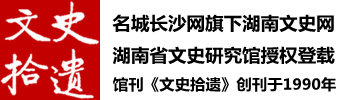辛亥革命时期,黄兴素有“实干家”之称,其反清军事斗争功绩卓著,而对政治思想的阐述甚少。进入民国后,随着时势的变换,黄兴得以陆续就一系列重大政治问题抒发己见,主旨鲜明,内涵丰厚,与占主导地位的孙中山政治思想相比较,同者很多,不同处亦相当明显。对此同异,当年革命阵营内多有重异轻同、是孙非黄的议论,而学界研究见仁见智,专题探究似仍不够充分。
作为齐名并称的革命领袖,黄兴与孙中山一生交谊不解,其民国年间政治思想之同异亦始终环环相扣,大致可分为民国初建到“宋案”之前、“二次革命”到继续反袁、离日赴美到重返故国等三个阶段。每个阶段既彼此贯通,又情形相殊。依此逐一梳理辨析,或可深化对黄、孙二人关系及民国早期民主革命思想流变得失的认识。
一
早在同孙中山联合组党之前,黄兴就具备了坚实的民族民主革命思想基础,这使他能与孙中山一见倾心,彼此产生强烈的思想共鸣。自同盟会成立开始,可以说黄兴就在为三民主义纲领的实现而努力奋斗,孙、黄二人的紧密配合和精诚团结,显示了他们革命理想和价值取向的高度一致,并奠定了此后其政治思想相互关联的基本走向。
从民国诞生到宋教仁被刺,是黄兴与孙中山政治思想的同一性表现最为显著的阶段。这一阶段以清朝的覆亡和共和政体的建立为主要标志,中国历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民主革命的态势亦呈现出全新的格局。孙、黄携手迎来了革命胜利,而又一道无奈向袁世凯代表的北洋军阀让渡了中央政权;他们对如何掀开民国建设新的一页充满期待,而同时又不能不对多有乱象的国家政治深怀隐忧。正是在这种时势和心境中,黄兴与孙中山重新作出他们的政治思考,无论是对革命任务的认定,还是建设目标的选择,抑或民党力量的重组等等,都持有非常相似的态度。
首先,他们都认为民国的成立,意味着民族革命和民权革命已经完成,随后需要进行的是以民生主义作指导的社会革命。
在此方面,孙中山言论颇多。当民初清帝甫告退位以接纳共和之际,他即表示“民国目的亦已达到”,“革命之目的已达”。在宣布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当日所发表的演说中,他更明确地肯定“今日满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此后,民族、民权主义已达之说,相当频繁地出现于其各类演讲和文字之中。既然三民主义已成功其二,那么,尚未实现的民生主义,便成为孙中山主要关注的革命任务之所在。他多次申明中国“惟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所当致力的即在此事”,“政治上革命今已如愿而偿矣,后当竭力从事于社会上革命”,“社会事业,在今日非常重要。……社会事业万万不能缓办。未统一以前,政事、军事皆极重要,而统一以后,而重心又移在社会问题”。这是孙中山面对中国政治新局面,迅速作出的政治纲领上的重大转变。
这一因应大势的转变,在黄兴身上表现得同样明显。在袁世凯被参议院一致举为民国临时大总统之后不久,黄兴针对外界言论怀疑“临时政府诸人意欲恋据要津”的“误会”,致电袁氏,坦然表露心迹:“起义以来,兴等本意全在扫除专制,拥护人权,以立国本。……在北方未实行宣布赞成共和以前,兴等以为大业未竟,各省同胞尚有隔阂,民国基础或致动摇,睹此危机,责无旁贷,则诚不能置身事外矣。今南北一家,总统得人,民国从此万年,迥非当日比也。吾辈十余年兢兢业业以求者,真正之和平、圆满之幸福。今目的已达,掉臂林泉,所得多矣。”话甚诚恳平易,并无理论性的总结,但“目的已达”、如释重负的感怀(更准确地说是一种善良的期盼),与孙中山所言如出一辙。
因此,像孙中山一样,黄兴也顺理成章地将民生主义作为接替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的旗帜,强调社会革命已成为新的当务之急。他在对同盟会会员的演讲中,大力宣扬“孙中山先生夙所主持之民生主义”的重要性,称之为同盟会的“特别之党纲”,指出“虽此主义在他党人多未认为必要,或且视为危险,实则世界大势所趋,社会革命终不可免。而本会所主张之社会主义,又极为平和易行。……平均地权,乃本会与他党特异之点。其详细办法,中山先生于南京、武昌两处均有演说,凡我同志,均当知此主义之必要,力谋进行”,并进一步阐释“中山先生倡三大主义,其特注重者则平均地权一语。……民生主义繁博广大,而要之则平均地权。反而言之,即是土地国有”,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这是民国立国的“根基”。可见,黄兴完全自觉地将孙中山的理想当作自己的理想,不仅奉为指针,而且着力推广,以使更多的革命党人统一到新的认识上来。
其次,对于如何着手实行民生主义和“社会革命”,他们都以国民经济的发展为枢纽,注重兴办各项建设事业。
基于革命重心的转移,孙中山对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作出了新的论述,认为要解决时下“政争”等难题,关键还是要解决根本性的“经济问题”,与政治相比,经济建设更为根本,“必先从根本下手,发展物力,使民生充裕,国势不摇,而政治乃能活动”。他明确表示,目前对中国的社会革新“比党务与政治问题更有兴趣”,由于政治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因而正集中思想与精力“从社会、实业与商务等几个方面”重建国家,而最大的计划就是“专心致志于铁路建筑,于十年之中,筑二十万里之线,纵横于五大部之间”,因为修铁路是“振兴实业”的关键,“但欲振兴实业,必自修造铁路入手”。孙中山的计划当然未能实现,但他为此的确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黄兴将“建设”的重要性提升到革命党转型的高度来认识,提出当“破坏事业”已竟、“革命成功”之际,应以同盟会改组为契机,来一个党型的大转变,这就是“吾党从前纯带一种破坏性质,以后当纯带一种建设性质”,而“建设”中其谈论最多者,就是振兴实业。
在黄兴看来,欲图国基巩固,“尤以实业为发展国力之母”,德国之所以能在短短的三四十年内,便从初兴时的“内讧不绝”、不思进取,一跃而成为压倒欧洲各竞争对手的强国,甚至使手握世界商业霸权的英国也心生“恐惧”,就是因为聚集了一支由高素质的商人和科技人才所组成的大军,与外国展开实业的竞争。如果国人也各以其能“发奋经营实业”,则“国家之繁荣,亦实可计日而待”。更深入地分析,“……二十世纪世界共同解决者,实为发展国民生计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的“锁钥”,则在“国民之企业力与日俱高”。如果不从此点着手,“则小之不能应新文明之要求,……国民生计日即于枯燥,久之且不能保存现有之企业力焉;大之国民总体之企业力不强,则不能利用新器械,计画新组织,纷集大资本,因不能为大开大阖之生产运动,以最少之资本、最少之劳力而出产最大之额,在近世工业革命潮流之中立得住脚。甚也,其可危也”。这些论述,显示了广阔的全球视野,其关于“企业力”(类似“生产力”)的论断,更是一种目光远大之见。
对于孙中山专意倡导的铁路计划,黄兴给以鼎力支持。他将修建铁路的重要性与实业发展乃至国家危亡紧密连在一起,断言“今者共和成立,欲苏民困,厚国力,舍实业莫由。然不速建铁道,则实业绝难发展。盖实业犹人身血液,铁道则其脉络。脉络滞塞,血液不贯注,自然之理也。……先以铁道为救亡之策,急起直追,以步先进诸国后尘,则实业庶几兴勃也乎”,并直接宣讲孙中山的“铁道政策”:“民国经济之发达,全恃铁道。现在政府所发表之铁道政策,即是中山先生之铁道政策。中山先生之铁道政策非自今日始,数年以前已有十分之研究。革命时期铁道政策即包含在内。……兄弟今日对于铁道之成功与革命同一希望。……愿诸君努力进行,使中山先生之政策得以速成,是所希望。”这种具体建设目标的契合,表明了黄、孙之间的高度一致。
第三,他们仍都密切注视着时局的变化,在充满忧患意识的同时,力求通过加强政党建设,为共和的稳固创造必不可少的条件。
民国的成立虽然结束了帝制,但实质上只是将政权转移到了北洋军阀手里。军阀统治所引发的各种问题,在政权南北交接的过程之中和完成之后,一直此起彼伏,从无间断。这些问题的存在和日趋严重,使宣告革命已经成功的孙、黄二人倍感担忧。他们除了就很多具体问题发表政见之外,还尤为重视如何才能巩固民国的根基,使共和制度和民主精神真正能在中国安营扎寨。他们共同的努力,突出体现在政党建设方面。
民国建立后,此前的革命政党同盟会经历了从秘密转为公开,继而与其他政党联合组成国民党的变化。孙、黄二人虽未主导国民党的组建,但对政党发挥作用仍寄予厚望。国民党一成立,他们就联名致电同盟会各支部,称此举“得此多数政团同心协力,将吾党素所怀抱者见诸实行,此非独同人之幸,亦民国前途之福也”,表示“深为赞成”。黄兴对政党建设更为热心,多次发表演讲,希望国民党能发展成为“极大之政党”、“最良之政党”和“伟大政党”,并对党的建设提出了“重道德心”和“重责任心”两大要求。“重道德心”就是要消除个人“权利心”,而代之以对国家的“义务心”,“提倡人人除权利心,以国家为前提”,以此形成“党德”,“党德既高,则希望可达”,不仅本党要有“党德”,各党亦应如此;“重责任心”就是要“凡我党员,均应共负责任,照党纲所定次序办法,人人尽力之所能为……对于内政,复极力研究,以求平靖。对于国际,极力辑睦,以求平和。人人均以此责任为天职”。
总的来看,黄兴在此阶段从各方面都表现出与孙中山政治思想的高度一致。他们延续了辛亥革命时期携手共进的亲密关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追求着民主共和的远大理想,并为此作出彼此非常协调的努力。
然而,在孙、黄二人的一致性中,也存在着一个隐而未显的问题,就是他们此时的政治思想与中国的政治实情之间,并不完全相符甚至相隔甚远,因而其一致性还带有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当真实逐渐显露、理想遭受重挫、重大事变接踵而至之时,他们是否还能继续保持这种一致性,就成为一个很大的挑战。
二
1912年3月,身为国民党代理事长的宋教仁被刺,这是民初政治开始发生重大变化的转折点。“宋案”的出现,证明孙、黄二人此前关于革命成功、实业为先、政党主导等体认,都只是一厢情愿的美好期盼,一切根本之图和权宜之计,皆需根据真实的政情,重新审视,另作决断。正是面对这一严峻的时局,孙、黄二人在猛然醒悟的同时,其政治思想的重大分歧也开始显现,与前一阶段彼此间的完全一致有了很大的不同。
这一阶段的孙、黄分歧,主要围绕“宋案”、“二次革命”和组建中华革命党等三事而展开,其隔膜之深,导致两人日渐疏远,最终各行其是,难以继续并肩奋战。关于这些分歧发生的经过和影响等,论者已多有评述。这里要着重讨论的是,对此分歧的是非得失,究竟应当如何评判。
作为分歧当事人的其中一方,孙中山对黄兴多有批评,认为其主张和行事在在皆错。
在中华革命党即将成立之前写给黄兴的信中,孙中山对双方分歧作了这样的论析:“……宋案发生之后,彼此主张已极端冲突;第二次失败后,兄仍不能见及弟所主张是合,兄所主张是错。何以言之?若兄当日能听弟言,宋案发表之日,立即动兵,则海军也,上海制造(局)也,上海也,九江也,犹未落袁氏之手。况此时动兵,大借款必无成功,则袁氏断不能收买议员,收买军队,收买报馆,以推翻舆论。此时之机,吾党有百胜之道,而兄见不及此。及借款已成,大事(“事”似为“势”之误——引者注)已去,四都督已革,弟始运动第八师营长,欲冒险一发,以求一死所,又为兄所阻不成。此等情节,则弟所不满于兄之处也。及今图第三次,弟欲负完全责任,愿附从者,必当纯然听弟之号令。今兄主张仍与弟不同,则不入会(指不加入中华革命党——引者注)者宜也。……弟所望党人者,今后若仍承认弟为党魁者,必当完全服从党魁之命令。因第二次之失败,全在不听我之号令耳。所以,今后弟欲为真党魁,不欲为假党魁,庶几事权统一,中国尚有救药也。”从“极端冲突”,到一“合”(对)一“错”,再到明示不“完全服从党魁之命令”则不必“入会”,不仅可见双方分歧之深,而且可见孙中山对黄兴的严重“不满”。
收到此信,黄兴曾复一长函,“……请露肝胆,披心腹,为先生最后一言之”,对宋案以来双方分歧的缘由等逐一解释,并“窃附于朋友之义,有所诤谏,终望采纳”。孙中山没有采纳黄兴的意见,“……终以为欲建设一完善民国,非有弟之志、非行弟之法不可”,直言因歧异太大,“此后彼此可不谈公事,但私交上兄实为我良友,切勿以公事不投而间之也”。黄兴作“最后一言”,孙中山则应以此后“可不谈公事”,双方分歧显然已走到了势同水火、不可调和的地步。
时隔大半年之后,黄兴已离日赴美,孙中山再度致函黄兴,望其“即日言旋”,共同开展反袁斗争。但此信的大部分内容,仍是追究黄兴对“二次革命”失败的责任。信中先以“所以失败者,非袁氏兵力之强,实同党人心之涣散”为总括,继而历数黄兴种种“涣散”即与孙中山不相一致之表现,其结论是“文之非欤?公之咎欤?固不待智者而后知之矣”。不仅如此,对黄兴“东渡”即流亡日本之后的言行取舍,孙中山给予了更为严厉的批评,谓其“不维始终之义,遂作中道之弃”,“不复以同志为念”,“……至今日而反退缩不前”,痛言“中国当此外患侵逼、内政紊乱之秋,正我辈奋戈饮弹、碎肉喋血之时。公革命之健者,正宜同心一致,乘机以起;若公以徘徊为知机,以观望为识时,以缓进为稳健,以万全为商榷,则文虽至愚,不知其可”。黄兴本来在前函中,已具体解释过所谓“涣散”之事的隐情苦衷,却未得到任何回应和谅解,反而受责依旧,所作“诤谏”也尽遭否定,在此无法沟通亦无从辩解的情境下,“言旋”自无可能。
对孙、黄分歧认定前者皆是而后者皆非的当时人,还有与两人关系均至为密切的革命党重要骨干陈其美。他于孙中山邀黄“言旋”之前一个月,即致函黄兴,殷切表达了请其“克日命驾言旋,共肩艰巨”这一与孙完全相同的愿望。信写得很长,大都与孙、黄分歧相关。
信中胪列了民国成立以来革命党失败的五件事,以证明凡“吾党重大之失败”,都是由于不听从孙中山之“政见”,误以其只是不切实际的“理想”,以致“有负于中山先生”而造成的。此五事中,后两件直接与黄兴有关。一件是“宋案”发生,孙中山力主“联日”“速战”以反袁,而黄兴等人坚持“静待法律解决”,结果“时机坐失,计画不成;事欲求全,适得其反”;另一件是策动“二次革命”,孙中山认为要取得成功,必须各处迅即“宣告独立”以占先机,而黄兴等人“不听”,“乃迁延时日,逡巡不进,坐误时机,卒鲜寸效”,“设当日能信中山先生之言,即时独立,胜负之数,尚未可知也”。由此五事,陈其美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就是“……理想者,事实之母也。……故中山先生之理想能否证实,全在吾人之视察能否了解、能否赞成,以奉行不悖而已”。这就相当于说,只要不折不扣地按照孙中山的“理想”和指示办事,革命便能无往而不胜。
他还力辩中华革命党“所定誓约,有服从先生、服从命令等语”之事,认为这是孙中山对“前此致败之故”的深度总结,对“统一事权”非常必要,“美以为此后欲达革命目的,当重视中山先生主张,必如众星之拱北辰,而后星躔不乱其度数;必如江汉之宗东海,而后流派不至于纷歧。悬目的以为之赴,而视力乃不分;有指车以示之方,而航程得其向。……故遵守誓约、服从命令,美认为当然天职而绝无疑义者”,期望黄兴能“许为同志而降心相从”。将孙中山奉为众人必须仰望的“北辰”和必得依归的“东海”,宣扬对其绝对服从为“绝无疑义”的“天职”,这可能是革命党史上神化领袖及其主义最早的一个典型例子。
综观孙中山和陈其美的批评,可以看出孙、黄分歧的过错,全被归于黄兴一方,而且被认为错得相当严重。如此否定黄兴,是否符合事实呢?
首先应该指出,孙、陈的批评并非出自私心的恶意攻击,而是为了总结革命的成败得失,以便统一思想认识,重新携手合作,其所表达的主要是一种政见,而不是个人抱怨或追责。这种政见,亦包含着种种程度不一的合理性,例如,注重抓住斗争的“时机”,主张改变党人的“涣散”状态,强调“事权统一”的必要,坚持继续以武力反袁,等等。即使是孙中山勇当全党绝对听命的“真党魁”,陈其美力赞孙中山指路领航的正确性,其实质也不是为了谋取个人私利,而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体现了开展革命斗争的某种现实需要,反映了相当一部分党人的政治心理,不宜简单等同于领袖专权和个人崇拜。
然而,在否定黄兴这一主要之点上,孙、陈的看法并不见得正确。即以前引两人信函而言,就有不少值得质疑之处。
孙中山在信中(见前引),以只要“听我之号令”、吾党便有“百胜之道”作为立论的基点,但实际上只是作了一系列无法证明的推论。其号令是否恰当,听令会受哪些客观制约,听令行事是否必然成功,其实都是影响甚至决定成败的前提性问题。比如,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孙仍“欲冒险一发,以求一死所”,结果为黄兴所阻,这本是明智之举,却也被列为不听令的一个例子,就恰好说明听令并不天然具有正确性。此外,孙中山建立中华革命党反袁,黄兴因反对其绝对听命于一人的组建原则和仍以小暴动为主的斗争方式,不入该党而另作新的政治谋划,这本来含有很大的合理性,至少可以两者并存,也并不能证明后者就是“背弃”和“退缩”。
至于陈其美信中所言,基本思路也与孙中山一样,主要凭推断将听命于孙作为成功的先决条件和是否正确的惟一标准,而并没有提供有力的事实证明。他对孙中山所作的神化宣传,虽有一定的历史依据和现实需求,但终归有悖民主真谛,弊端后患甚多,黄兴坚持不能接受,显然更有道理,从长远看更有利于革命党的建设和发展。就此而言,黄兴之错更是无从谈起。
三
要评判黄兴此时政见的对错,更为重要的一方面,是还需要对其本人何以与孙中山相异的真实原因和思想根源,进行更深入的考察和分析。
一般认为,孙、黄之争的焦点在于斗争方式,孙急图(立刻起兵、马上独立、迅速组党再起等)而黄缓进(先法律解决、等待时机、暂作其他准备等),孙勇猛而黄迟疑,这种差别又似乎说明孙有更强的革命性,而黄的幻想性和动摇性更多。其实不然。
许多史料记载表明,“宋案”后黄兴反袁,同样非常坚决和坚定,也为武力反袁作了很大的努力。之所以在一些具体举措上与孙中山相左,主要还是由于各种客观条件的制约,正如论者所说:“宋案发生后,黄兴从当时实际情况出发,虽主循法律途径解决,实则未尝放弃以武力为最后解决之计划。”关于何以不愿或不能“急图”的个中缘由,黄兴本人也直接对孙中山作过说明。如果单就行事的缓急而言,黄兴也许比孙中山更为激进,“宋案”后,他多次主张进行暗杀,“……以其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而孙表示“极为反对”。
实际上,黄兴之所以与孙中山产生重大分歧,除了各种纷繁复杂的客观因素外,还存在更为深刻的思想原因。这就是对于某些重要政治观念或价值取向,他还有自己独特的思考和认识,与孙中山的差别甚为明显。
强烈期望依法治国,使民国由传统的人治国家转型成为法治国家,这是黄兴极为看重的民主共和原则。早在1912年8月革命党人张振武、方维被杀案发生之际,黄兴就致电袁世凯,严正宣示“凡有法律之国,无论何级长官,均不能于法外擅为生杀。……国民生命财产权专恃法律为保护,即共和国精神所托”,强烈谴责“今不经裁判,竟将创造共和有功之人立予枪毙,人权国法,破坏俱尽”,坚决主张“彻底查办”此案,“庶全国人民皆得受治于法律之下”。对于尽早制定正式宪法,黄兴更是寄予厚望,认为“惟现今最重大者,乃民国宪法问题。……吾党万不能不出全力以研究之,务期以良好宪法,树立民国之根本”。他在宋教仁被害前夕为《国民》月刊所写发刊词中,进一步重申:“今者,正式国会成立在即,建设共和国家之第一著,首在制定宪法。宪法者,人民之保障,国家强弱之所系焉也。……吾党负建设之责任至繁至巨,首先注意宪法,以固国家之基础。善建国者,立国于不拔之基,措国于不倾之地。宪法作用,实有不倾不拔之性质。”当武力反袁开始后,黄兴还通电各国,说明由“法律”解决走到“武力”解决的迫不得已:“惟袁世凯违犯约法,蹂躏国会权限……迹其罪恶,甚于专制暴君。我人先拟依据宪法(指“临时约法”——引者注),令袁世凯退职,以谢人民。法律解决既经无效,乃不得不诉之于武力,作最后之解决。”可见,“宋案”发生后,黄兴坚持首选“法律”而不是“武力”作为对策,不只是选择一种斗争方式,而且是要忠于“共和国精神”和维系民国的“根本”。尽管在法治观念极为薄弱而军阀统治十分强大之时,这扇民主之门未能如愿开启,但这种真心尝试和起步践行的努力,值得给予历史的肯定。
与注重法治原则完全一致,黄兴在价值观上信守“平等自由主义”,将其作为不可逾越的政治思想底线。“平等自由”本来也是孙中山所大力宣扬的民主思想,但其强调“平等自由”重在团体而不在个人,而黄兴对两者并未作明显区分,因此对个人的“平等自由”也同样看得很重。中华革命党以绝对服从领袖个人为组建原则,孙中山可以作这样的变通,而黄兴却难以认同。他写信给孙中山,直截了当地表示“弟自闻先生组织会(指中华革命党——引者注)时,即日希望先生日加改良,不愿先生反对自己所提倡之平等自由主义”。湖南革命党人刘承烈参与筹组中华革命党,对黄兴有所劝说,黄断然不肯听从:“惟兴素性迂拙,主义所在,不敢变换手段以苟同。虽以人之如何毁伤,亦不稍为之动。……至于欲反对自己十余年所提倡之平等自由主义,不惜以权利相号召,效袁氏之所为,虽爱我如兄,兴亦不敢从兄之后。”黄兴还在对日本友人谈到今后打算时,写道:“从此誓漫游世界一周,以益我智识,愿以积极手段改革支那政治,发挥我所素抱之平等自由主义,以与蟊贼人道者战。”可见,“平等自由”原则对黄兴来说,非同小可,决不能轻言变动,更不能弃而不顾。
对于“二次革命”失败后,革命党人如何重新再起,黄兴主张不要急功近利,而要作长远根本之图。在流亡日本期间,黄兴深刻反省革命失败的原因,在致孙中山信中作了这样的总结和展望:“以为此次乃正义为金钱、权力一时所毁,非真正之失败。试翻中外之历史,推天演之公例,未有正义不伸者,是最后之胜利,终归之吾党。今吾党既握有此胜算,若从根本上做去,本吾党素来之主义发挥而光大之,不为小暴动以求急功,不作不近情言以骇流俗,披心剖腹,将前之所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尽披露于国民之前,庶吾党之信用渐次可以恢复。又宜宽宏其量,受壤纳流,使异党之有爱国心者有所向归。夫然后合吾党坚毅不拔之士,学识优秀之才,历百变而不渝者,组织干部,计画久远,分道进行,事有不统一者,未之有也。若徒以人为治,慕袁氏之所为,窃恐功未成而人已攻其后,况更以权利相号召者乎?数月以来,弟之不能赞成先生者以此。”这些论述包含了非常丰富的内容,其中很多设想的前瞻性、正确性和可行性,为后来民主革命的发展所证明。
正因为有这些深层认识的不同,孙、黄分歧一直难以弥合。尽管如此,他们毕竟还是具有反袁专制和捍卫共和的根本一致性(加上孙的坦荡和黄的忠厚),虽有重大歧异,也不至于和不可能走到反目为仇的地步。
在一时无法协同的情况下,孙中山提议:先由自己单独领导“第三次革命”,而黄兴则一切勿图,“静养两年”,不要“分途并进”,以免碍事;如果过期不成功,则再转让于黄兴“独办”。黄兴对“转让”之说很不以为然,但还是以积极的心态接受了孙的建议,表示此后虽处局外,但“如有机会,当尽我责任为之,可断言与先生之进行决无妨碍”。为了彻底让孙中山放心,黄兴决计离开日本,远赴美国,由此,这一阶段的孙、黄分歧就画上了一个令人感慨却也还算圆满的句号。
四
从黄兴离日赴美到返国,再到逝世,其间只有不足两年半的时间。在此阶段,孙、黄都以各自的方式,竭尽全力为反袁倒袁而斗争,其同者愈益显著,异者渐次缩小,呈现出一个动态的转化过程。
大约以1915年9月为界,又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段。前段黄兴充分利用各种机会,大造反袁专制统治的舆论,但同时又明确反对即刻发动反袁的军事斗争;后段面对袁氏称帝步步紧逼的时局,黄兴转而积极支持和多方鼓动武力反袁,并对袁氏的帝制自为严厉抨击、追究到底。在反袁护国的历史大格局中,孙、黄政治思想在很大程度上终于又重合在一起。
进行反袁宣传,这是黄兴抵美后自觉担负的政治使命,也是忠实履行对孙中山所作的“当尽我责任为之”的重要承诺。其在此方面的言论很多,要者如:宣扬革命党人反袁是为“自由”而战,“我们将奋斗到底,使中国成为一个实至名归的共和国,让人民享有和美国公民同样充分的自由。目前中国的情况比满清统治时期更为险恶。……本人直接奉孙先生之命向美国转达他的意见,我们认为美国公民必须知道真相。……中国人知道自由的真谛。这种认识将使大家仇恨暴政,一旦时机成熟,必会揭竿而起”;揭露袁世凯早有“帝制自为”的野心,“他是利用虚伪的承诺骗取了今日的地位,他用所有的方法来标明重视共和,但却把自己形成绝对独裁的地位”,但“袁世凯是绝对不会成功的。因为在有思想的中国人的脑海中,仍然充满了强烈的共和意识,对于袁世凯以及任何人想做皇帝,他们绝不会长久的缄默不言”;号召人们“同心合力”,一起投入反袁斗争,“惟诸君奋起精神,驱此妖魔。此非国民党一部分之事,实为全国人民应为之事也”,“我先烈流血断头,然后造成共和,宁忍坐视袁氏之推翻乎?……故望诸君同心合力,拥护共和,将袁氏驱除,中国前途,庶有豸耳”,“夫政治不良,人民有改革之责任,西哲所谓革不良政治之命,被治者之天职是也。……今日谋政治上之革命,当无疑义。然究非空言可以收成效,一乃心,同乃德,古人所谓众志可以成城”,等等。这些主张,可以说完全同于孙中山的政治思想。
不过,对于以革命党人之力,马上就再度兴兵反袁,黄兴还存在诸多顾虑。
1915年,他与陈炯明、柏文蔚、钮永健、李烈钧等人联名发表通电,澄清国内关于他们五人正密谋重起“革命”,甚至“假借外力”以推翻政府的流言谤语,否认已经选择“兵战”,言其原因是“兵凶战危,古有明训,苟可以免,畴日(“日”似为“曰”之误——引者注)不宜?重以吾国元气凋伤,盗贼充斥,一发偶动,全局为危。故公等畏避革命之心,乃同人之所共谅”,“至于假借外力,尤为荒诞。……窃览世界诸邦,莫不以民族立国。一国以内事,纵为万恶,亦为族人自董理之。倚赖他族,国必不保。殷鉴未远,即在平南”,对当下并不打算发动革命的理由,一一作了说明。
通电还对“革命”本身,作了两方面的反思:一方面指出“须知革命者,全国心理之符,断非数十百人所能强致。辛亥已事,即为明证。国人既惩兴等癸丑(指“二次革命”——引者注)之非,自后非有社会真切之要求,决不轻言国事。……国政是否必由革命始获更新,亦愿追随国人瞻其效果”,表现了对革命所需社会条件的重视和静观时变以定是否革命的态度;另一方面,着重强调“惟革命之有无,非可求之革命自身,而当卜之政象良恶”,如今民国“空尸共和之名,有过专制之实,……内政荒芜,纲纪坠地,国情愈恶,民困愈滋。……今吾国不见国家,不见国民,而惟见一人。……经此惩创,实乃迷梦猛醒发奋独立之秋”,并不否定革命的正义性和必要性。
在此后回复孙中山的一封信中,黄兴对其正在“兼程并进”的“三次革命”虽表“同情”,却认为时机尚不成熟:一是革命党人元气未恢复。“二次革命”后,许多同志沦落海外,温饱难求,“兴闻而痛之”,此时若还“谆谆以革命相劝”,以为“正可利用”,“岂使之冻馁者不足,复将驱之炮火中耶!此兴之期期以为不可者也”。 二是借助他国之力不理智。以为“中日交涉未解决”,就可乘时而起,取得外援,大获成功,实属似是而非之语,“我同志既以爱国为标帜,以革命相接橥,无论借他国以颠覆宗邦,为世界所窃笑,而千秋万岁之后,又将以先生为何如人也”。三是敌我力量对比很悬殊。回顾“壬癸(即1912—1913年——引者注)之际,本党声威若何,权力若何,然举宁湘粤之众,犹不能抗少数之北军,岂民党之兵力之不逮耶,亦以民心之向背为之转移耳”,对比之下,“今日既无稳固之根据,又无雄厚之财力,乃必欲以求一逞,恐必有覆辙折足之虞”。因此,不赞成此时“乘隙急进”,力劝审时度势,“卧薪尝胆,待之十年”,不要“孟浪从事”。
然而,时势的变化,往往超出人们的意料。就在黄兴还在作“待之十年”之想的时候,袁世凯称帝的紧锣密鼓却已然敲响,国内各方反袁的策划也悄然速行。1915年8月,直接为帝制造势的筹安会宣告成立。9月底,蔡锷派专人给黄兴送来长达17页的密信,指斥袁氏称帝的阴谋,商讨将赴西南发难的计划。经过仔细研究分析,黄兴断定武力讨袁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打掉种种顾虑,开始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倒袁武装起义的各种筹划之中,其中包括受孙中山之托,积极在东京进行借款购械的活动。
在此时段,黄兴政治思想以反袁帝制自为为中心,与孙中山又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
当袁氏悍然称帝,黄兴迅即宣布“袁世凯废共和,行帝制,中国必立起革命,声讨其罪。此时吾定返中国,再执干戈,随革命军同事疆场,竭物最后之气力,驱逐国贼……中国五千年来,至今乃得改为共和政体,国民始得享自由幸福,吾国民断不能坐视袁氏任意复行帝制”,主张“袁逆谋叛,凡属国民,均宜联合一致,同时挞伐”,破除门户,消灭党界,力赞孙中山在上海发表的第二次讨袁宣言“豁然大公,无任钦仰”。
袁死后,孙中山就“复约法、召国会”和“息纷争、事建设”的大政方针征求意见,黄兴衷心赞成,“无任感佩”,并期望孙出面“主持”大局,“使国人晓然于吾人之无私无偏”。为了推进既定方针的落实,黄兴致电新任总统黎元洪,力陈“恢复旧约法,召集旧国会,按诸法理,及此次起义之民意,实如矢赴的,如水归壑,万无反理。……凡百建设鸿猷,当以此两事为最急切。务望排除莠言,迅速解决……立即施行,以救危局”;又致函国务总理段祺瑞,促其顺应“回复元年约法、召集旧国会”之民意,“盖以根本不决,则新政府之进行无所依据。深冀迅颁明令,借慰薄海望治之诚”。这与不久后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宗旨完全吻合。
孙中山在袁氏倒台前写给黄兴的一封信中,曾提出过“已往将来,中国问题实为新旧之争。换言之,则为民党与官僚派之争”,及民党应在主义相同的基础上,“求最大之团结力,以挡彼官僚一派”的重要思想。对此思想,黄兴颇为认同,于袁氏覆灭后多次加以阐释和引申发挥,明言“今日政治进行方法,可以官、民二字为标准。凡官僚中腐败而恶劣者,当极力澄清之。民党处今日情势,当互相亲爱,决不可彼离此贰。……固不可以党为界限,然精神当有直接之觉悟。凡一国民权被制于恶劣官僚者,其国必危弱;民权伸张,官邪扫荡,其国必强盛”;又更为细致地分析“此次政变(指反袁斗争——引者注),简单言之,乃新势力与旧势力之争,官僚派与民党之争。然……犹有未尽。盖新派与民党不必皆善,而旧派与官僚亦未必尽恶。故以正确之义言之,实正义派与非正义派之争也。……正义派苟不团结一致,则非正义派之势力,不惟不能打消,反将乘隙潜进,死灰复燃,国家前途仍有可虑。……切望凡属于正义派之人,宜结合为一……以为国内势力之中坚,不致使非正义派仍有恢复旧势力之一日,则吾国前途其庶几矣”,不仅与孙中山异口同声,而且作了重要补充。
总之,民国建立后黄兴与孙中山的政治思想,可以说经历了从大同到歧异、再到大同的变化。整个看来,同者是其根本,异者只是支流。他们共同追寻建设新国家的理想,坚决反击袁世凯的专权和帝制自为,矢志不渝地捍卫民主共和制度,宣扬民主革命精神,留下了相互印证补充的宝贵思想遗产。其歧异作为不同政见,对双方都有纠偏防错、免蹈极端的意义;虽可析其利弊的大小,却不宜作截然对错的评判。二人对政见歧异开诚布公,只持公义之争,不作私欲之斗,始终互相敬重,也为现代政治提供了一个足资参照的范例。
注释:
相关研究成果可参见:[美]薛君度著:《黄兴与中国革命》,杨慎之译,第九章《对袁世凯的斗争》、第十章《一代伟人的凋谢》、附录《纪念黄公克强并论辛亥革命》第五部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前言》,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方志钦:《论孙中山和黄兴的关系》,《辛亥革命史丛书》第1辑,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陈宇翔:《孙中山、黄兴政党思想异同述论》,《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2期;萧致治:《五十年来黄兴研究述评》,《湖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等。这些著述多有中肯切当之见,不过就孙、黄政治思想的同异而言,似还有必要作更为深入细致的讨论。
《咨参议院辞临时大总统职文》,1912年2月1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研究院历史研究所合编:《孙中山全集》第二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84页。
《致黎元洪及各省都督电》,1912年2月15日,《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99页。
《在南京同盟会会员饯别会的演说》,1912年4月1日,《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319页。
见《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332、335、337、338、340、354、408、472、476页。
《在南京同盟会会员饯别会的演说》,1912年4月1日,《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319页。
《在上海答﹤文汇报﹥记者问》,1912年4月4日,《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332页。
《在湖北军政界代表欢迎会的演说》,1912年4月10日,《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335页。
《致袁世凯电》,1912年2月24日,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33页。
《在中国同盟会上海支部夏季常会上的演讲(二件)》,1912年6月30日,《黄兴集》,第238—239、240页。
见《在上海与﹤民立报﹥记者的谈话》,1912年6月25日,《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382页。
《致宋教仁函》,1912年8月22日,《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404页。
《中华民国》,1912年7月中下旬,《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392页。
《致宋教仁函》,1912年8月22日,《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404页。
《在塘沽与某报记者的谈话》,1912年8月23日,《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405页。
见《在中国同盟会上海支部夏季常会上的演讲(二件)》,1912年6月30日,《黄兴集》,第239—240页。
见《在旅沪湖南同乡会欢迎会上的答谢词》,1912年7月30日,《黄兴集》,第243—244页。
《筹办旅沪湖南公学募捐启事》,1912年7月,《黄兴集》,第244页。
《﹤铁道杂志﹥序》,1912年8月,《黄兴集》,第252页。类似论述,还可见于黄兴的多次演讲,如《在北京湖南同乡会欢迎会上的演讲》(1912年9月16日)说“惟欲兴实业,当谋铁路,铁路不发达,实业即不振兴。此不可不注意者”(《黄兴集》,第265页),《在北京西北协会欢迎会上的演讲》(1912年9月18日)说“铁路为交通利器,蒙藏以道路不通,致滋疑惑。……西北进行之障碍,交通上实一大原因。故铁路政策,实为今日必要之图也”(《黄兴集》,第269页)等。
《在北京铁道协会欢迎会上的演讲》,1912年9月22日,《黄兴集》,第274—275页。
《与孙中山致中国同盟会各支部电》,1912年8月13日,《黄兴集》,第246页。
见《黄兴集》,第261、282、288页。
见《在北京国民党欢迎大会上的演讲》,1912年9月15日,《黄兴集》,第261—262页。关于“党德”和党员“责任心”,黄兴还作过更多的论述,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还在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之前,他就提出了“党德”的命题,主张“本会本有特别之党纲,更当有宏大之党德”,“至政党道德,吾人尤宜以宏大之心理对待他党。……切勿与他党谩骂”,“……欲宏党风,须有包含一切之宏量。他党之攻吾也,虽含种种疾忌而不好之点,吾人亦当引以为戒,认彼反对者为好友,不必反报,含养大度,培植党德,成一个最大政党,于攻击风潮中特立不移,以一特别党风造成一种党德”。(《在中国同盟会上海支部夏季常会上的演讲(二件)》,1912年6月30日,《黄兴集》,第238、239、240页)后又进一步发挥说:民国建设事业“非一党所能自私”,“故对于他党,亦务期互相提携,交换意见,俾克砥砺观摩,收他山之助。凡他党之所主张,不可为无意识之反对,只当以国利民福为前提,平心静气,为稳健之批评,以待民国之抉择。盖政党必具此党德,方能光辉发达,成极伟大之政党,否则亦终归失败而已”。在党员“责任”方面,党员应负责任极多,归结起来就是“指导人民、代表人民意思之责”和“监督政府、维持政府之责”,“约言之,即政党者,对于国家负完全维持之义务,为国民之耳目,使全国之人免于盲人瞎马半夜深池之危险者也”。(《在国民党鄂支部欢迎会上的演讲》,1912年10月28日,《黄兴集》,第289、290页)
《孙中山复黄兴书》,1914年5月29日,《黄兴集》,第358—359、360页。
《复孙中山书》,1914年6月1日或2日,《黄兴集》,第356—357、358页。
《孙中山复黄兴书》,1914年6月3日,《黄兴集》,第360页。
《孙中山致黄兴书》,1915年3月,《黄兴集》,第406—407页。
《陈其美致黄兴书》,1915年2月4日,《黄兴集》,第405页。
见《陈其美致黄兴书》,1915年2月4日,《黄兴集》,第399—404页。五事中的前三事分别是:当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临时参议院坚决反对孙中山向俄国借款,以致影响经济,妨碍政府行动;袁世凯当选临时大总统后,孙中山提出袁氏必须就职于南京等三项重要政见,因党人不同意,最终“格而不行”,结果导致了抛弃约法、推翻共和的“后患”;孙中山退职后,“欲率同志为纯粹在野党,专从事扩张教育,振兴实业……而尽让政权于袁氏”,而党人反对,“且时有干涉政府用人行政之态度”,终使得“朝野冰炭,政党水火,既惹袁氏之忌,更起天下之疑”。(见同前,第400—401页)这些事与黄兴亦有间接关联。
见《陈其美致黄兴书》,1915年2月4日,《黄兴集》,第404—405页。
这种神化领袖和主义的作法,后来逐渐强化,难以阻遏,在中国政治生活中造成很多负面影响,此为后话。
毛注青编著:《黄兴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386页。有关史料记载,见该书第371—386、389—398页。
见《复孙中山书》,1914年6月1日或2日,《黄兴集》,第357页。
《复孙中山书》,1914年6月1日或2日,《黄兴集》,第357页。又见《孙中山复黄兴书》,1914年6月3日,《黄兴集》,第360页。
《复袁世凯电》,1912年8月20日,《黄兴集》,第249页。
《致袁世凯电》,1912年8月27日,《黄兴集》,第251页。
《在国民党上海交通部欢迎会上的演说》,1913年1月26日,《黄兴集》,第309页。
《﹤国民﹥月刊出世词》,1913年3月,《黄兴集》,第316页。“宋案”发生于3月20日,“出世词”中未提此事,似应写于案发之前。
《致各友邦通电》,1913年7月20日,《黄兴集》,第342页。
《复孙中山书》,1914年6月1日或2日,《黄兴集》,第358页。
《复刘承烈书》,1914年6月3日,《黄兴集》,第360、361页。
《复宫崎寅藏书》,1914年5月21日,《黄兴集》,第355—356页。
《复孙中山书》,1914年6月1日或2日,《黄兴集》,第357页。
见两封《孙中山复黄兴书》,1914年5月29日、6月3日,《黄兴集》,第359、360页。
《复孙中山书》,1914年6月1日或2日,《黄兴集》,第358页。关于革命并无“转让”之理,信中作了这样的分析:“惟先生欲弟让先生为第三次之革命,以二年为期,如过期不成,即让弟独办等语,弟窃思以后革命原求政治之改良,此乃个人之天职,非为一公司之权利可相让渡、可能包办者比,以后请先生勿以此相要。”(引同前,第357—358页)
《在檀香山与美国新闻记者谈话》1914年7月9日,《黄兴集》,第363、364页。
《对美国﹤旧金山年报﹥记者谈话》,1914年7月15日,《黄兴集》,第365页。
《在美洲中国国民党支部召开“二次革命”纪念大会上的演讲》,1914年7月15日,《黄兴集》,第371页。
《在旧金山民国公会宴会上的演讲》,1914年7月16日—22日间,《黄兴集》,第378页。
《在屋仑华侨欢迎会上的演讲》,1914年7月26日,《黄兴集》,第379、382页。
见《与陈炯明等联名通电》,1915年2月25日,《黄兴集》,第397—398页。
见《与陈炯明等联名通电》,1915年2月25日,《黄兴集》,第398—399页。
见《申报》,1915年5月23日。转引自《黄兴年谱长编》,第451—452页。
见《黄兴年谱长编》,第453、470—471页。
《致美国驻华公使电》,1915年12月14日,《黄兴集》,第412页。
《复谭人凤电》,1916年6月1日,《黄兴集》,第433页。
见《孙中山致黄兴电》,1916年6月13日,《黄兴集》,第442页。
《复孙中山电》,1916年6月14日,《黄兴集》,第441页。
《复黎元洪电》,1916年6月20日,《黄兴集》,第443页。
《致段祺瑞书》,1916年6月21日,《黄兴集》,第444页。
《孙中山致黄兴书》,1916年5月20日,《黄兴集》,第438页。
《在驻沪国会议员欢迎会上的答谢词》,1916年7月10日,《黄兴集》,第446页。
《在欢送驻沪国会议员北上大会上的演讲》,1916年7月13日,《黄兴集》,第447—448页。相关论述,还可见于《在驻沪国会议员留别茶话会上的演讲》(1916年7月14日,薛君度、毛注青编:《黄兴未刊电稿》,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04—105页)、《在广东省驻沪国会议员举行的茶话会上的演讲》(1916年7月15日,《黄兴集》,第449—450页)、《在上海报界茶话会上的演讲》(1916年7月22日,同上书,第451页)等。
(宋德华系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民国建立后黄兴与孙中山政治思想的同异】宋德华[黄兴诞辰140周年纪念专辑]
2015-01-03 14:21:19 来源: 评论:0 点击:
辛亥革命时期,黄兴素有实干家之称,其反清军事斗争功绩卓著,而对政治思想的阐述甚少。进入民国后,随着时势的变换,黄兴得以陆续就一系列重大政治问题抒发己见,主旨鲜明,内涵丰厚,与占主导地位的孙中山政治
分享到:
相关热词搜索:同异 民国 建立 黄兴 孙中山 政治 思想
上一篇:【民国成立前后黄兴的民族观念】田涛[黄兴诞辰140周年纪念专辑]
下一篇:【“民强则国强”——论黄兴的强国思想和主张】林家有[黄兴诞辰140周年纪念专辑]
分享到:
频道总排行
频道本月排行
- 30【铁血铸丰碑——浏阳党史人物简述】邓继团2021年3期总125
- 26【元代名人邓谦亨及其浏阳后裔族群考】邓继团2022年4期总130
- 19【烽火间隙的酬唱和风雅】王金华2022年4期总130
- 11【文强非毛泽东表弟考】邓继团2018年2期总112
- 9【近现代长沙旅馆业史略】乐兵2023年1期总131
- 7【白果园33号:一座名宅与一位名医的往事】彭坚2022年4期...
- 7【革命情深两世家——陈、黄两家的交往】陈崇孝[黄兴诞辰...
- 6【芋园、芋园主人与芋园文化】李崧峻2011年2期总84
- 5【论黄兴故居的恢复及如何发挥其爱教宣传作用】胡群义[黄...
- 5【长沙欧阳家族迁徙考】邓继团2022年2期总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