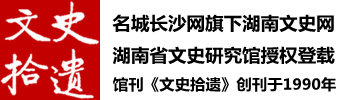王闿运是晚清知名学者和文学家,然因相距较近,接受积淀不深,加上历来毁誉参半的评价等,导致今天对其文学、学问地位依然聚讼纷纭。但不可否认的是,王闿运是晚清成就突出,地位显赫的文学家。在诗学上,王闿运也匠心独运,特色鲜明。这里说下他的诗学观。
一、自发性情的诗歌本质论
王闿运旗帜鲜明地倡导陆机《文赋》中所说“诗缘情而绮靡”观念。其《湘绮楼说诗》卷四收录《答陈复心问》,有曰:
诗缘情而绮靡。诗,承也,持也,承人心性而持之。风上化下,使感于无形,动于自然。故贵以词掩意,托物起兴,使吾志曲隐而自达,闻者激昂而思赴。其所不及设施,而可见施行,幽窈旷朗、抗心远俗之致,亦于是达焉。非可快意骋词,自状其偏颇,以供世人之喜怒也。
强调诗歌“承人心性而持之”,指出《毛诗序》中所说诗歌的教化功能,但主张以文辞修饰文意,托物起兴,含蓄蕴藉,自然而然的表达,反对驰骋辞藻,直接说明文意,抒发偏激之论,诱导读者喜怒于色。自周至中唐的诗歌,尽管有偏于玄理、藻饰山川或寓言闺闼之作,但都没有偏离“言情”本色:
自周以降,分为五七言,皆贤人君子不得意之所作。晋人浮靡,用为谈资,故入以玄理。宋、齐游宴,藻绘山川。梁、陈巧思,寓言闺闼,皆言情之作。情不可放,言不可肆,婉而多思,寓情于文,虽理不充周,犹可讽诵。唐人好变,以骚为雅,直指时事,多在歌行,览之无余,文犹足艳。韩、白不达,放弛其词。下逮宋人,遂成俳曲。近代儒生,深讳绮靡,乃区分奇偶,轻诋六朝。不解缘情之言,疑为淫哇之语。其原出于毛、郑,其后成于里巷,故风雅之道息焉。
在王闿运看来,从韩愈、白居易的诗歌议论化、理性化和世俗化之后,直到宋代,诗歌成为俳优之曲。清代的儒生,更是讳忌诗歌缘情绮靡的本质,导致风雅之道中断。这些评论都有偏颇之处,完全忽视了诗歌发展的流变性,但也具有重情重藻的积极意义。在《杨蓬海诗集序》中,王闿运辩证地论述了诗歌与情感的关系:
诗贵有情乎? 序诗者曰:发乎情,而贵有所止;则情不贵。人贵有情乎? 论人者曰:多情不如寡欲;则情不贵,不贵,而人胡以为诗? 诗者,文生情;人之为诗,情生文。文情者,治情也。孔子曰:“礼之用,和为贵。”有子论之曰:和不可行。和不可行,而和贵;然则情不贵,而情乃贵。知此者,足以论诗矣。
《诗大序》中强调“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从政教角度来说明情感抒发的限度与维度。王闿运强调诗歌贵于有情,但不是情感泛滥无度;诗歌、文辞、情感、作者的关系环环相扣。文辞有情,才为诗;作者有情,才有文辞,才写诗歌,因此文章之情,是调剂之情而不是泛滥之情;不以情感为唯一归宿,情感才显得珍贵,才可以论诗。杨蓬海对世俗所溺的“昏宦功名”,非常淡薄;对人情所忽视的嬉戏、酣醉等真性情的行为却喜好,形成无情与有情的强烈反差。其诗歌则一往情深:“情之绵邈,愈淡远而愈无际。情之宕逸,如春云触石,时为惊雷。其往而复,如风止雨霁,云无处所;其往而不复,如成连泛舟,而涛浪浪。……善文情者,杨子邪?善文杨子之情者,杨子之诗邪?”全文围绕“情”字立论,以杨蓬海善于治情来说明“诗之贵情”的主张。
深受辞赋熏陶的王闿运,对诗歌抒发性情及含蓄的表达方式非常看重。“如果要对王闿运的诗学精髓作一简单的概括,一言蔽之,则为‘诗缘情而绮靡’。”这种情感不是平铺直叙,直接暴露在诗中,而是以词掩意,托物言志。同时,这种情感也不是儒家论理道德规定的理想抱负、天理伦常,而是包含个人的难言之隐与私密之情。他在《论诗示黄镠》中说:“词章莫难于诗,而人皆喜为之。诗以养性,且达难言之情。”这种难言之情,可以是哀怨、愤懑之情,也可以是亲情、爱情,甚至是违反世俗标准的情感。为了表达这种情感,需要“选词”“持志”,含蓄蕴藉地呈现:
诗既分和、劲两派,作者随其近,自极诣。当其下笔,先在选词,斐然成章,然后可裁。诗者,持也。持其志,无暴其气;掩其情,无露其词。直书己意,始于唐人,宋贤继之,遂成倾泻。歌行犹可粗率,五言岂容屠沽?无如往而复之情,岂动天地鬼神之听?……乐必依声,诗必法古,自然之理也。欲己有作,必先蓄有名篇佳制,手披口吟,非沉浸于中必不能炳著于外。
强调诗歌言志抒情的含蓄性,特别重视五言诗的持志、掩情,即表达的含蓄蕴藉,情感的浓郁深沉。为此,需要效法古人,沉潜把玩,这样才能融会贯通,自成一家。“直书己意,始于唐人,宋贤继之,遂成倾泻”,当指诗歌直接议论说理,抒怀明志。杜甫、韩愈已开先河,到宋代苏轼、黄庭坚发扬光大,这也是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所批评的以文字、议论和才学为诗的主要指向。直接抒发作者情感或志向的诗歌,是对《诗经》至汉魏六朝诗歌审美理想的破坏,是对古典诗歌审美传统的背离。王闿运在晚清社会风云激荡、西学东渐、旧学衰微的潮流下,还站在传统文学内部立场来反对宋诗,这说明了其文学观念的传统与守旧,但也隐含了他对汉魏六朝诗歌多以比兴抒情,而不直白显露的传统的坚守。在社会变革与文学新变的特定时段,总有拥抱新生与坚守传统的不同人群,我们不能以其立场来判断其文学主张是否先进与落后,而应该以文学主张本身的是否合理来判断其优劣。
王闿运重视诗歌的性情,特别是情感表达的曲隐,离不开他对明代诗学的继承。王闿运的模拟诗学,他自认为是对明代七子派的复古主张的超越;同时,王闿运本身也多次提到明代七子派的诗歌与主张。明代七子派是诗文复古运动的代表,重视诗歌情感的表达。徐祯卿《谈艺录》有曰:“情者,心之精也。情无定位,触感而兴,既动于中,必形于声。故喜则为笑哑,忧则为吁戏,怒则为叱咤。然引而成音,气实为佐;引音成词,文实与功。盖因情以发气,因气以成声,因声而绘词,因词而定韵,此诗之源也。”对诗歌的感发性及其与作者情感、气脉、声音、辞藻、声韵的渊源关系。但王闿运并不认同他们的拟古方法,否定其诗歌成就。王闿运《论作诗之法》有曰:“诗法既穷,无可生新,物极必返,始兴明派。事事摹拟,但能近体,若作五言,不能自运。不失古格而出新意,其魏、邓乎?” 诗歌发展到明代,难以创新,七子遂走向复古。但只能作近体诗,五言古诗则亦步亦趋,失去古格且没有新意,不像清代同乡魏源和邓辅纶的五古创新性强。王闿运甚至认为七子派的古体诗连优孟衣冠的程度都没有达到:
明人拟古,但律诗可乱真,古体则开口便觉。诗亦自有朝代,唐以前诗不能伪为,宋以后诗大都易似。此又先辨朝代,后论家数也。近人卤莽,谬许明七子为优孟,以杨诚斋、陆务观配苏、黄,不知七子之全不能《文选》,杨、陆之未足成家数也。
七子不能为《文选》中的汉魏晋宋齐诗歌,杨万里、陆游诗歌也无法与苏轼、黄庭坚并列,都是因为他们没有自成家数。在王闿运看来,近体诗比古体诗容易模拟,因为前者的技法易学,但后者的浑融难师,故他批评明代七子派的拟古“但律诗可乱真,古体则开口便觉”。在《论诗绝句》中,王闿运也对七子派加以批评。评何景明、李梦阳曰:“何李功夫在七言,却依汉魏傍高门。能回坡、谷粗豪气,岂识苏、梅体格尊。”指出其长于七言,学习汉魏,但冷落五古,体裁选择有误。评王世贞、李攀龙曰:“七子重将古调弹,潜搀唐宋合苏韩。诗家酿蜜非容易,恐被知音冷眼看。”指出其复古却掺和唐宋韩愈、苏轼诗风,路径不对。评王夫之曰:“江谢遗音久未闻,王何二李枉纷纷。船山一卷存高韵,长伴沅湘兰沚芬。” 指其继承了江淹、谢朓等汉魏六朝诗传统评,比七子派路径为正。
诗歌的性情除了外物的感发外,本身的形式也有要求,即王闿运所说的“格律”。他在《论诗法答唐凤廷问》中说:“诗主性情必有格律,不容驰骋放肆,雕饰更无论矣。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无所感则无诗,有所感而不能微妙,则不成诗。”这里的“格律”指把握诗歌章法结构和起承转合的技巧。自发性情需要多用兴,这样才能至于醇雅。王闿运认为当时诗歌于六义之兴,不同于《诗经》中的风雅颂三体,因而反对论诗以《诗经》为法,主张效法荀子、宋玉的赋以及相传是枚乘、苏武所写的诗。其《论汉唐诗家流派答唐凤廷问》中说:
今之诗歌,六义之兴也,与风、雅、颂异体。论者动言法《三百篇》,亦可法荀、宋赋乎?上古之诗,即《喜起》《麦秀》之篇。具有章法,唯见枚、苏,皆在汉武之世。则学古必学汉也。
二、以词掩意,托物起兴的诗法论
《毛诗序》中提到“诗有六义”,即风、赋、比、兴、雅、颂,并从政教的角度对风、雅、颂的内涵作了明确的阐释,但对赋、比、兴仅仅指出它们是《诗经》“文之异辞”和“所用”,是风、雅、颂成体的表达方法,因此而同称为六义。诗大序堪称中国诗学的开山纲领,其讽谏、主文而谲谏、发乎情,止乎礼义、诗歌与政治、盛德等紧密相关的观念影响深远。
王闿运强调诗歌情性的涵养,表达时需要“以词掩意”,而不是“以意为重”。在这样的诗学主张下,王闿运选择了五言诗和汉魏六朝诗歌作为其理想诗歌的代表。在《论诗示黄镠》中,他认为:
作诗必先学五言,五言必先读汉诗。而汉诗甚少,题目种类亦少,无可揣摩处,故必学魏、晋也。诗法备于魏、晋,宋、齐但扩充之,陈、隋则开新派矣。自来推曹子建为大家,无一灵妙句。阮嗣宗稍后之,便高华变化,不可方物;而不为大家者,重意不重词也。诗之旨则以词掩意,如以意为重,便是陶渊明一派。钟嵘以为陶诗出于《百一》,不言出《咏怀》者,陶语句更明白易晓也。学阮、陶只可处悲愤乱世,若富贵闲适便无诗。学曹尚有可发舒,比老庄、山水、宫体为阔大,可以应用。此外诸家皆其枝流,虽各有妙,而不外此。曹以后则大陆足继之。
阮籍、陶渊明的诗歌重意不重词,没有达到以词掩意的要求;曹植、陆机则相反,因而最被王闿运推重。
王闿运熟悉“六义”,但反对诗歌的讽谏和抑制情感,认为诗歌是兴之所至,情之所感的自然结果,强调晚清诗歌的“托兴”功能。在推崇兴体的前提下,他将诗歌分为五言、七言两派,认为五绝、七绝才是真兴体,五律是五言的别派,七律是五律的加增。五言源于唐、虞时代,而不是《诗经》;七言出于《离骚》,而不是五言的拓展。王闿运主张不直接表露诗意和情感,反对议论点题,主张婉转表达,因此对托物言志的兴体手法非常重视,在《巫山神女庙碑》中也特意说:
而宋玉之赋有《高唐》《神女》,小儒俗吏不通天人,罔识神女主山之由,莫察诗人托谕之心,苟见奇异,肆为诙嘲。山灵清严,固不降惩,然不正其义,而欲守土之虔祀,弗可得已。往者常说朝云之事,其必曰王因幸之者,托先王后长子孙之义,以讥楚后王弃先君之宗庙,去故都,远夔、巫,而乐郢、陈,将不保其妻子。使巫山之女为高唐之客,高唐齐地,朝暮云散,失齐之援,见困于秦。至后作《神女赋》,则不及山川,专以女喻贤人。屈子之徒,义各有取,比兴意显。
王闿运不满《诗大序》以来的诗教传统,反对诗歌创作为外在因素的刺激,而将之归为主体内在性情的自然抒发与含蓄表达:
诗有六义,其四为兴。兴者,因事发端,托物寓意,随时成咏。始于虞廷‘喜’‘起’及《琴操》诸篇,四、五、七、言无定,而不分篇章,异于《风》《雅》,亦以自发情性,与人无干。虽足以讽上化下,而非为人作,或亦写情赋景,要取自适,与《风》《雅》绝异,与《骚》、赋同名。明以来论诗者,动称《三百篇》,非其类也。
《诗经》六义,是明清诗学中的焦点话题。明代诗文复古派倡导五言源于《诗经》,王闿运明确反对。明末许学夷以风雅颂为三经,赋比兴为三纬,强调经纬交错的关系:“风者,王畿列国之诗,美刺风化者也。雅颂者,朝廷宗庙之诗,推原王业、形容盛德者也。故《风》则比兴为多,《雅》《颂》则赋体为众;《风》则微婉而自然,《雅》《颂》则齐庄而严密;《风》则专发乎性情,而《雅》《颂》则兼主乎义理:此诗之源也。徐昌谷云:‘《卿云》《江水》,开《雅》《颂》之源;《烝民》《麦秀》,建《国风》之始。’语虽不谬,但古今说诗者以《三百篇》为首,固当以《三百篇》为源耳。”许学夷:“风人之诗既出乎性情之正,而复得于声气之和,故其言微婉而敦厚,优柔而不迫,为万古诗人之经。”对《国风》性情之正、声气之和以及微婉敦厚风格的强调,正与王闿运诗学性情为本说一致。又说:
风人之诗,不特性情声气为万古诗人之经,而托物兴寄,体制玲珑,实为汉魏五言之则。而文采备美,一皆本于天成。大都随语成韵,随韵成趣,华藻自然,不假雕饰。退之谓“诗正而葩”,盖托物引类,则葩藻自生,非用意为之也。
对性情声气与托物兴寄的凸显,与王闿运的诗学观念高度吻合,可见王闿运深受许学夷的影响。不同的是,许学夷没有将“兴”独立于风雅颂,特别是风之外,只是将赋比兴视为表达方式,而王闿运则单列“兴”,强化“兴”的功能与作用。这里的“兴”,“乃同钟嵘《诗品》序所云‘文已尽而意有余’之兴,亦是杨载《诗法家数》所云:‘绝句之法,要婉曲回环,删芜就简,句绝而意不绝。’” 在《湘绮老人论诗册子》中,王闿运再次表明作诗不是源于《诗经》,当代诗歌为“兴体”:
今人论作诗,皆托源于《三百篇》,此巨谬也。《诗》有六义,今之诗乃兴体耳,与《风》《雅》分途,亦不同貌。苏、李以前,则《卿云》《麦秀》《暇豫》《猗兰》是其先行;至汉则大开法门,演其章句,参以比赋之体,乃成一篇。离合回互,起承转结,作者斐然,互相师化。经数万人之才智,数千年之陶冶,分五、七、长、短、古、律,遂成六体,而四言、六言不预焉,绝无词意可通《风》《雅》。盖《风》《雅》国政,兴则己情;《风》《雅》反复咏叹,恐意之不显,兴则无端感触,患词之不隐。……今之诗乃古之兴。虞廷《喜起》,箕子《麦秀》,各从其志,托之讴吟,所以自持,无于人事;间以示人,实则自陈耳。若用以代章疏告示,则嫌其隐情廋词,无从捉摸。轺车制废,谁为搜采?而论者欲以比古经,岂不谬哉?六义之旨,同于温柔敦厚,非以问世也。犹之“思无邪”,非五经有邪也。邪姑不论,而温柔敦厚,固词赋之所同。诗不论理,亦非载道,历代不误,故(今)去之弥远。
明代诗学中,已有人质疑诗源于《诗经》。徐祯卿《谈艺录》有曰:“《卿云》《江水》,开《雅》《颂》之源;《烝民》《麦秀》,建《国风》之始。览其事迹,兴废如存;占彼民情,困舒在目。”王闿运继承明人旧说,提出新论,强调诗歌的兴体手法及抒发性情的功能,指出诗歌不论理,也不载道,这无疑具有打破诗教牢笼,倡导自由抒怀的社会意义。
王闿运反复提出当时诗歌重在愉悦性情,而不是古诗的教化讽谏,多次强调诗歌的兴体功能:
古之诗以正得失,今之诗以养性情。虽仍诗名,其用异矣。故吾尝以汉后至今,诗即乐也,亦足感人动天,而其本不同。古以教谏为本,专为人作;今以托兴为本,乃为己作。史迁论诗,以为贤人君子不得志之所为,即汉后诗矣。主性情必有格律,不容驰骋放肆,雕饰更无论矣。情动于中而行于言,无所感则无诗,有所感而不能微妙,则不成诗。
因为重视诗歌抒发性情,故他反对一味模仿大家之诗,好大求全,耽于形式,主张提升自我内在修为,自成一家:“优孟舍己从人,全无本色,衣冠散后,乃后知之。当其登场,俨然孙叔也。此如魏武之学周公,谢监之慕子牟,内外有殊,而形声无异。古今有几优孟哉!论至此而诗道乃贵,凡内外如一者,孙叔也;殊者,优也。欲善其外,先修于內,可矣。心发为诗,诗不可伪,伪则优矣。必有真性情而后有真诗,故诗关于学也。由学为诗顺而易,由诗成学逆而难。难者所获恒倍于易,由诗知学,其学猛进而无退转,尤可贵也。” 在外人看来,王闿运是摹拟汉魏六朝诗歌,缺乏创新;但在他自己看来,他也反对单纯摹拟,而是主张内外兼修,以内为本,向外摹拟不过是他练习诗歌创作的方式。建国后游国恩等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简单地将王闿运的诗歌贬为腐朽的假古董,自然是特点时代背景下的偏激之论。
三、重情尚兴的文学史意义
作诗需要才思、学力、志气,才能卓然自立,抗衡古人。否则,亦步亦趋地模仿古人,终究是优孟衣冠,难以自立。以王闿运为首的晚清诗坛湖湘派的形成,楚文化崇尚个性的精神与南方文学的抒情传统是其产生根源,初唐陈子昂以来推崇汉魏古诗的复古传统是其思想基础,清代诗坛或宗唐或祧宋的诗学生态是其产生的时代背景。陈书良先生指出“自楚汉时期屈原流寓沅湘、贾谊谪宦长沙之后,流波所及,始开湖南文学风气。尤其是屈原的辞赋,怀着对祖国、对人民的深厚情感,写下了许多描述湖南山水景物、风土人情、民间祭祀、神话传说的辞章,表现了古代湘楚人的生活和情感,在开创了一个与《诗经》风格迥异的南方楚辞、离骚文学流派的同时,也奠定了湖南文学的基石。屈、宋一直是古代湖南士子引为骄傲的文章和道德的楷模。” 中国古代文人在复古观念的影响下,多认为诗体代降。顾炎武就认为:“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辞,楚辞之不能不降而汉魏,汉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也,势也。”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和《楚辞》,就成为历代文人推崇的典范。诗歌创作,由唐代而追寻汉魏,由汉魏而溯源《风》《骚》,由《风》《骚》而抗衡《雅》《颂》,是推崇唐诗逆流而上的必然归宿。
明末许学夷(1563-1633)批评明代七子派、公安派、竟陵派论诗偏颇,于道分别为“不及”“过”和“离”后,接着为明代诗歌复古派遭受公安派和竟陵派的攻击加以辩护:“汉魏六朝,体有未备,而境有未臻,于法宜广;自唐而后,体无弗备,而境无弗臻,于法宜守。论者谓‘汉魏不能为《三百》,唐人不能为汉魏’,既不识通变之道,谓我明诸公‘多法古人,不能自创自立’,此又论高而见浅,志远而识疏耳。……夫体制、声调,诗之矩也,曰词曰意,贵作者自运焉。窃词与意,斯谓之袭;法其体制,仿其声调,未可谓之袭也。今凡体制、声调类古者谓非真诗,将比俚语童言、纤思诡调而反为真耳。”观点较为通达,论述也较为深刻。王闿运强调诗歌以性情为本,法古而自成一家,表达情感要以词掩意,含蓄蕴藉,崇尚藻采与醇雅,反对议论说理,体现了他追求诗歌的古典审美理想特征。虽多画地为牢,自以为是,但也有其历史的合理性。身处近代的他,反对“意多于词”,正揭示了“同光体”倡导宋诗好议论、好说理,忽视藻饰的特征,并非强调诗歌要“词多于意”,而是以词掩意,因而并不一定就是形式主义。他对诗歌缘情和绮靡属性的强调,对中唐至宋代的诗歌背离古典诗歌审美传统的批判,与近现代文学以西方纯文学观念为宗,希望摆脱古代杂文学观念的思潮,殊途同归。
王闿运以其85岁的高寿,加上广泛交游、在湖湘、江西和四川的书院讲学、个性鲜明的诗学主张和丰富的创作实践等,深刻影响了湘赣蜀地的诗风,特别是家乡所在地的湖湘诗风。近代著名诗人程颂万(1865-1932)、陈锐,早年诗歌就深受王闿运影响。汪辟疆《近代诗派与地域》有曰:“程子大初为选体,中岁以后,乃不为湘绮所囿,而以苍秀密栗出之,体益坚苍,味益绵远,诗歌意境格调已不大同。”陈衍(1856-1937)在1927年成书的《石遗室诗话》中,概括近代以来的诗坛情况曰:
道、咸以来,何子贞绍基、祁春圃寯藻、魏默深源、曾涤生国藩、欧阳磵东辂、郑子尹珍、莫子偲友之诸老,始喜言宋诗。何、郑、莫皆出程春海侍郎恩泽门下,湘乡诗文字,皆私淑江西,洞庭以南言声韵之学者,稍改故步;而王壬秋闿运,则为《骚》《选》、盛唐如故。都下亦变其宗尚张船山、黄仲则之风。潘伯寅(潘祖荫)、李莼客(李慈铭)诸公,稍为翁覃溪(翁方纲)。吾乡林欧斋布政寿图亦不复为张亨甫(张际亮),而学山谷(黄庭坚)。
此时的诗坛,流行宋诗,名家辈出,成果丰富,包括曾国藩写诗都效法黄庭坚为首的江西诗派,影响深远,各地望风而从。一般认为,道咸年间宋诗派发轫,以程恩泽和祁寯藻为代表,效法杜甫、韩愈、苏轼和黄庭坚的诗歌,彼此唱和。咸同年间,何绍基、魏源、曾国藩等推崇宋诗,互相唱和。光绪年间,沈曾植、陈三立、陈衍等又推崇宋诗,推波助澜,形成“同光体”,盛行于诗坛。“纵观整个清代诗歌的唐宋之争,发展到晚期,宗宋势力已是主流,占据了上风,融通唐宋也有一定的势力,而宗唐势力相对较弱,显示出唐诗在晚清日益受到冷落,宋诗受到尊崇的局面。”晚清湖南诗坛虽然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有的由宗汉魏六朝、盛唐转向祧宋。但王闿运作为湖湘派的代表,仍然坚持效法《骚》《选》及盛唐诗歌,不改初衷。在陈衍还对王闿运的五古、七古、五律和七绝等作了点评:“湘绮五言古沉酣于汉魏六朝者至深,杂之古人集中,直莫能辨。正惟其莫能辨,不必其为湘绮之诗矣。七言古体必歌行,五言律必杜陵《秦州》诸作,七言绝句则以为本应五句,故不作,其存者不足为训。盖其墨守古法,不随时代风气为转移,虽明之前后七子,无以过之也。”进一步指出了王闿运坚守自我,不随时代风气转移的执拗性格与独特诗风。
夏敬观(1875-1953)为陈锐的《抱碧斋集》作序云:“咸同间,湘人能诗者,推武冈邓先生弥之、湘潭王先生壬秋。邓先生祖陶称杜,王先生则沉潜汉魏,矫世风尚,论诗微抑陶。两先生颇异趣,然皆造诣卓绝,神理绵邈,非若明七子、清乾嘉诸人所为也。”陈锐(1859-1923)从王闿运学诗,专攻五言。曾去拜谒张之洞,座上论诗以王派遭到轻视。其实,诗道广大,探源发微应纵览列代以察其情变。唐宋、汉魏、六朝各有长短,应该兼容并蓄,因人而异。
湖南文学自清代以来,逐渐兴盛,特别是晚清,诗文创作堪称全国重镇。汪国垣《近代诗派与地域》将近代十家分为湖湘派、闽赣派、河北派、江左派、岭南派、西蜀派六派,其中湖湘派居首。王闿运重情尚兴的文学主张,虽然遥接先秦汉魏,但在近代的张扬,与现代文学的主情论不谋而合,相得益彰,共同推动了古典文学向受到西方文学观念影响的现代文学的过渡。鲁迅、周作人等一批现代作家,深受西方文学抒情、移情观念的影响,强调文学在于动人情感,与学问有别,都与王闿运的重情尚绮的文学观有契合之处。章太炎曾问鲁迅文学的定义,鲁迅答道:“文学和学说不同,学说所以启人思,文学所以增人感。”(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从章先生学》)周树人、周作人《红星佚史序》强调学与文的不同:“学以益智,文以移情,能移人情,文责以尽,他所所益,客而已,而说部者,文之属也。读泰西之书,当并函泰西之意,以古目观新制,适自蔽耳。”正如何荣誉所指出:“章氏(太炎)推崇汉魏,与王氏(闿运)合流,这使得汉魏六朝派在清民之际得以进一步延续传承,并得以壮大。章氏弟子黄侃的诗歌,好友刘师培、弟子鲁迅等对魏晋六朝文学的研究,都扩大了魏晋文学在民国的影响。”
当然,正如郭延礼先生所说:“王闿运在诗歌理论上最大的弱点是强调‘摹拟’,仍然走着‘复古主义’的老路。这就使他的许多有价值的见解最终仍陷入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泥坑。而这一点,与他所处的那个风云变幻、变革求新的时代显得极不和谐。”但从传统诗歌发展的角度来说,王闿运为首的湖湘派诗学对汉魏六朝诗,特别是汉魏诗的推崇,打破了当时诗坛崇尚宋诗的潮流,丰富了晚清诗坛的内容,增加了文学发展中的个性化色彩和性情化风格,为近代诗歌的转型提供了思想基础和作品铺垫。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
【论王闿运本情重兴的诗学观】吕双伟2018年1期总111
2018-05-07 10:15:31 来源: 评论:0 点击:
王闿运是晚清知名学者和文学家,然因相距较近,接受积淀不深,加上历来毁誉参半的评价等,导致今天对其文学、学问地位依然聚讼纷纭。但不可否认的是,王闿运是晚清成就突出,地位显赫的文学家。在诗学上,王闿
分享到:
相关热词搜索:诗学 王闿运
上一篇:【关于谭嗣同研究的六点建议】周秋光2018年1期总111
下一篇:【时务学堂的历史定位】刘泱泱2018年1期总111
分享到:
频道总排行
频道本月排行
- 14【“沩痴寄庐”及新民学会人才群体】陈先枢 梁小进2021...
- 13【梁启超与湖南时务学堂】丁平一2015年4期总102
- 11【毛泽东长沙早期革命活动的三个“大本营”】朱习文2021...
- 8【浅析杜甫湖南诗中的政治情怀】糜良玲2012年4期总90
- 7【辛亥革命后长沙知识分子对学习西方文化的探索】杨锡贵...
- 7【湖南近代著名教育家曹典球述评】丁平一2020年4期总122
- 7【七十年中国湘菜研究史述略】尧育飞2021年1期总123
- 7【毛泽东与船山学社】王兴国2021年2期总124
- 5【身在潇湘第一州—元代中越交往中的若干资料】汤军2013...
- 4【诚信——湖南老字号的商业精神】陈先枢2015年2期总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