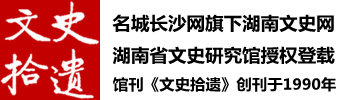自1914年船山学社成立开始,至1951年学社停止活动前后,毛泽东在不同时期都与它有着不同程度的联系:或聆听其讲演,接受船山思想的熏陶;或利用其社址和经费,开展国际交往和创办湖南自修大学,为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培养人才;或为学社题名。
一
正当1914年上半年毛泽东所在的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并入第一师范的时候,刘人熙在思贤讲舍社址上创立了船山学社。毛泽东最尊敬的老师杨昌济对王船山特别推崇。据杨氏这年6月12日日记记载:“胡子靖介绍余入船山学社,余颇为踌躇。因担任学校功课颇无暇日,一切党会均不愿插身其间,因一入会即须费精神目力也。但第一次开讲,当往一亲刘先生之丰采耳。”胡子靖即胡元倓(1872—1940),字子靖,湖南省湘潭县人,时任明德中学校长。杨氏在这段日记中说明了他不参加船山学社的原因,主要是课程负担太重。胡氏在邀请杨氏入社的同时,肯定已经告知船山学社成立的时间,所以他说学社第一次开讲,当一往亲睹刘人熙先生之丰采。6月14日,是船山学社第一次开讲,也是正式成立。在15日的日记中,杨氏写道:“今日至船山学社,刘艮生先生白须飘拂,唇红异常。吴凤笙先生自岳麓冒雨渡水至,亦可谓高兴者。”杨氏的“15日”是将14日的内容与15日混在一起了。因为其日记有13日而无14日,接着就是15日。据《湖南公报》关于这次开讲的报道,船山学社的成立应该是6月14日。刘艮生即刘人熙(1844—1919),字艮生,号蔚庐,浏阳人,这年他已经70岁。吴凤笙即吴獬(1841—1918),字凤笙,湖南省临湘市桃林镇人。时任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国文教授,与杨昌济为同事。
杨昌济虽然自已无暇经常参加船山学社的活动,但却十分支持他的学生去听其讲座。在1914年10月19日的日记中,杨氏写道:“阅熊、萧二生日记,知船山学社切实讲船山所著之书,此事深惬鄙意。刘艮老之绪论亦甚平实,青年肯往听讲,必有益也。”熊、萧二生都是一师与毛泽东同一个年级的学生。毛泽东的同学萧三曾回忆:“长沙城里曾有人举办过‘船山学社’,每星期日设座讲学,讲王船山的种种,泽东同志也去听讲。王夫之的民族意识特别引起他的注意。”而这种影响也是与杨昌济的宣传和启发分不开的。对此,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也是肯定的:在杨昌济的“倡导下,研究船山学问在一师成为风气。毛泽东尤其用功,还经常到杨的好友刘人熙创办的船山学社听课”。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船山思想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重民族气节。在船山学社成立10天之后的1914年6月24日,杨昌济在日记中写道:“学社以船山为名,即当讲船山之学。船山一生卓绝之处,在于主张民族主义,以汉族之受制于外来之民族为深耻极痛。此是船山之大节,吾辈所当知也。今者五族一家,船山所谓狭义之民族主义不复如前日之重要,然所谓外来民族如英、法、俄、德、美、日者,其压迫之甚非仅如汉族前日之所经验,故吾辈不得以五族一家,遂无须乎民族主义也。”这样,杨昌济便把中国古代传统的民族主义转变成反对帝国主义的现代爱国主义。而且杨氏当时还把其关注的目光集中指向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所以他在分析了《春秋》三世说之后接着说:“余前在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听其西洋历史讲义,谓中国人与罗马人同,惟宝爱其文化,虽外人入主其国,苟不伤其文化,即亦安之。私心揣测,谓日人不怀好意,颇有继满洲人入主中国之思想,此吾国人所当深念也。”杨昌济的这一认识,深深地影响了青年毛泽东。1915年5月7日,当日本国政府胁迫中国签订旨在独占中国的“二十一条”时,船山学社在5月23日的讲会上印发了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吴雁舟就五七事件的《训学生词》,后面还加有刘人熙的后记。吴氏的《训学生词》说:“民国四年五月七日,某仇敌恃厥坚甲利兵,蔑弃公理,提灭国条件,限晷刻逼勒我政府如约,我政府为延旦夕命,亦既不敢逾晷刻,低首下心以画诺。……孔子曰:‘亡国而勿知,不智也;知而不争,非忠也。’吾愿吾诸生,知所以为争。”在社会普遍的激愤情绪影响下,第一师范的学生集资刊印了一本《明耻篇》,全书辑有七篇文章和一个附件,包括《救国刍言》《中日交涉之前后状况》《已签字之中日新约及交换照会》《请看日本前此计灭朝鲜之榜样》《日本祸我中国数十年来之回顾》《高丽亡国后归并日本之惨酷情形》《越南亡国惨状略述》等。毛泽东在此书封面上沉痛地写道:“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他还在此书的《感言》后写了以下说明:“此文为第一师范学校教习石润山先生作。先生名广权,宝庆(今邵阳)人。当中日交涉解决之顷,举校愤激,先生尤痛慨,至辍寝忘食,同学等爰集资刊印此篇。先生则为序其端而编次之。云云。《救国刍言》亦先生作。”石氏时任一师国文教员。1915年夏,船山学社社长廖名缙去职,公推石广权继任主讲。1919年,公推石广权任社长兼任船山中学校长,至1919年夏去职。有石氏这样一位充满爱国心的老师出任船山学社社长,更增加了青年毛泽东对船山学社的亲切感。1916年7月25日,毛泽东在致萧子升信中说:近日朝野有动色相告者一事,曰“日俄协约”。此约业已成立,两国各尊重在满蒙之权利外,俄让长春滨江间铁路及松花江航权,而日助俄以枪械弹药战争之物。今所明布者犹轻,其重且要者,密之不令人见也。驻日公使有急报归国,《大公报》登之,足下可观焉。“大隈阁有动摇之说,然无论何人执政,其对我政策不易。思之思之,日人诚我国劲敌!感以纵横万里而屈于三岛,民数号四万万而对此三千万者为之奴,满蒙去而北边动,胡马骎入中原,况山东已失,开济之路已为攫去,则入河南矣。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而国人犹沉酣未觉,注意东事少。愚意吾侪无他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孙,止有磨砺以待日本。吾之内情,彼尽知之,而吾人有不知者;彼之内状,吾人寡有知者焉。吾愿足下看书报,注意东事,祈共勉之,谓可乎?”《毛泽东传》在引用上述这段话后评曰:“一九三七年,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爆发,这位二十四岁的师范生果然言中。”
其二,重知行统一。刘人熙在船山学社的讲演中说:“本社崇拜船山,即是尚友古人。读其遗书,如亲謦咳,即是诏我以途径者也。”意思是说读《船山遗书》要善于将思想指导自己的行动。杨昌济在日记和给学生讲课时,多次引用王船山有关格物致知和知行统一的论述。他在《论语类钞》中说:“某君专重力行,不重学问;某君则专恃天才与经验,不重学问。不知学之不讲,则力行只是盲行,行之愈力,危险愈大。”青年毛泽东受此影响,十分重视知与行、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早在一师读书期间,他就与同学结伴到湖南农村进行调查。在五四运动期间,他说:“吾们讨论各种学理,应该傍着活事件来讨论。”这里已经接触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理论必须联系实际。它说明理论固然是重要的,但是它的重要性恰恰在于它能指导人们的行动。所以毛泽东在这个时期不仅十分注重对理论问题的研究,而且更加重视运用这种理论去分析实际问题,认真进行调查研究。他认为,要实现改造中国社会的远大理想,没有对中国实际情况的周密调查和真切了解,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他在积极组织湖南的进步青年赴法勤工俭学的同时,自己则做了暂时不出国的打算。他说:“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工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在现在做了,一来无方才所说的困难,二来又可携带些经验到西洋去,考察时可以借资比较。”为此,他抓住一切机会深入社会和群众之中进行实地考察和调查。例如在他第一次去北京的途中,河南郾城车站附近沙河涨水把路基淹没了,他便利用火车暂时停驶的时间,到车站附近的漯河寨向工人、农民和市民调查当地的灾情与人民的生活情况;到北京以后,他又多次利用到长辛店了解赴法勤工俭学预备班学员情况的机会,深入工人比较集中的长辛店机车车辆厂调查了解工厂的生产、收益和职工的生活情况。这样,他就为自己从工农群众中吸取政治营养,逐步加深对中国现状的了解,并且为往后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其三,重个人之独立。刘人熙在船山学社的讲演中,十分重视“船山先生固空所依傍,有独来独往之精神”。杨昌济在《论语类钞》中解释孔子“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时,曾引用的王船山在《俟解》中说的一句话:“有豪杰而不圣贤者矣,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杨昌济在解释船山这句话时指出:“圣贤,德业俱全者;豪杰,歉于品德,而有大功大名者。拿(破伦)翁,豪杰也,而非圣贤。”这说明,只有道德和功业俱全的人才能成为圣贤,而豪杰则是虽有大功大名,但其品德却有所欠缺。杨氏进一步论述道,近世教育学者之说曰,人属于一社会,则当为其社会谋利益。若己身之利益与社会之利益有冲突之时,则当以己身之利益为社会之牺牲。虽然牺牲己之利益可也,牺牲己之主义不可也。不肯抛弃自己之主义,即匹夫不可夺志之说也。吾国伦理学说,最重个人之独立。观历史之所载,经训之所传,莫不以守死善道为个人第一之义务。臣之于君,子之于父,妇之于夫,照吾国昔圣先贤之理想,皆有委身以事,爱敬终身,效死勿去之义。然忠臣、孝子、贞妇之志,有非其君、其父、其夫之所能夺者。王船山曰:“唯我为子故尽孝,唯我为臣故尽忠,忠孝非以奉君亲,而但自践其身心之则。”船山重个人之独立如此。杨昌济的这种说法,实际上是为了论证个性解放这一西方观念也是中国古圣贤哲所主张的。他在讲修身课时曾将这些思想向学生宣讲,而毛泽东将王船山的话和杨氏的讲解记录在其《讲堂录》之中。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过程中,毛泽东对个性解放十分感兴趣。他把个性解放作为实现五四时期的两个基本口号,即民主与科学的基本动力。在谈到个性解放与民主的关系时,他特别强调人格独立:“人格这件东西,是由于对手方面的尊崇才有的。他的先决问题,是要意志自由。赵女士的意志自由么?不自由的。怎么不自由?因为赵女士有父母。”“西洋的家庭组织,父母承认子女有自由意志。中国则不然,父母的命令,和子女的意志完全不相并立。赵家父母明明迫着他的女儿恋爱不愿意恋爱的人,遗容有什么自由意志?”在谈到个性解放与科学发展的关系时,毛泽东特别强调独创。他指出:“现代学术的发展,大半为个人的独到所创获。最重的是‘我’是‘个性’,和中国的习惯,非死人不加议论,著述不引入今人的言论,恰成一反比例。我们当以一己的心思,居中活动,如日光普天照耀,如探海灯之向外扫射,不管他到底是不是(以今所是的为是),合人意不合人意,只顾求心所安合乎真理才罢。老先生最不喜欢的是狂妄。岂知道古今真确的学理,伟大的事业,都系一些被人加着狂妄名号的狂妄人所发明创造来的。”
正是个性解放的思想,促使青年毛泽东成为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又正是坚定的爱国主义思想,促使青年毛泽东沿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从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最终转变成为共产主义者。在这一过程中,船山思想是起了某种潜移默化作用的。
二
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时最要好同学之一萧子升(瑜),在谈到他1921年3月从北京回到长沙与毛泽东相会的情况时说:“在长沙,有一幢叫‘船山学社’的房子。是为纪念学者王船山(1619—1692)而命名的。现在有五十多个信仰共产主义的人接管了这幢房子,因为毛泽东是其中成员之一,所以我也受到邀请到那里去住。”罗章龙在《回忆新民学会(从湖南到北京)》一文中也说:“新民学会后来把船山学社接收过去,表面上宣传王船山的学说,实际上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宣传爱国主义思想,教育青年。当时大家把这叫做‘旧瓶装新酒’,即古为今用的意思。”萧子升和罗章龙的“接管(接收)”之说,是有根据的,也基本上是符合事实的。
说它基本上符合事实,是因为从1920年夏天起,何叔衡就出任船山学社社长。何叔衡(1876—1935)在1918年8月加入新民学会,1919年11月被选为该学会委员长(总干事)。在“驱张运动”中,受毛泽东之命参加驻衡驱张请愿代表团的活动。他于1920年3月1日到达衡阳, 利用驻衡阳直系军阀吴佩孚与张敬尧的矛盾,动员群众向吴请愿,促使吴对张施加压力,并联络湘军首领谭延闿等以军事实力向张敬尧进逼。在舆论严厉指斥和湘军步步进逼下,张敬尧不得不于1920年6月26日狼狈撤出湖南省境。驱张结束之后,公推何叔衡出任船山学社社长。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民学会“接管”了船山学社是符合事实的。但是,到了这年9月,何叔衡由湖南省教育委员会委任为湖南通俗教育馆馆长,并接办该馆发行的《湖南通俗报》。由于公务繁忙,他于1920年年底辞去了船山学社社长的职务。继任的社长为贺民范,他不是新民学会会员,却是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成员。贺民范又名贺希明(1866—1950),湖南邵阳人。早年为秀才,1907年留学日本法政大学,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任临时省议会议员兼秘书长,安化、岳州知事,福建向安、宁德知事。1918年弃官回湘,寄寓长沙。五四时期他任船山学校校长。金冲及主编的《刘少奇传》对这个时期的贺民范有一段介绍:他同陈独秀一直有联系,是湖南的著名进步人士。他受陈独秀的影响和委托,在湖南热心传播马克思主义,支持先进青年组建革命团体。毛泽东、何叔衡等组织长沙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都借用他的声望出面号召。所以,很多湖南青年想参加革命团体,都来找贺民范。刘少奇这时和毛泽东还互不相识,也不知道俄罗斯研究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是毛泽东、何叔衡等实际负责的,所以同其他一些湖南青年一样,也到船山学校去找贺民范,请他介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帮助联系赴俄勤工俭学。贺民范对刚从保定留法预备班毕业回来并且立志追求真理的刘少奇很是赞许,随即介绍他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但湖南的社会主义青年团这时尚在筹建过程中,还没有具体活动。关于赴俄留学的问题,贺民范要刘少奇先去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俄语,学习后由那里统一组织赴俄勤工俭学。他为刘少奇写了封致上海外国语学社负责人杨明斋的推荐信。在这期间,贺民范还陆续介绍任弼时、萧劲光、周兆秋、胡士廉等14个湖南俄罗斯研究会会员和青年去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刘少奇自己回忆这一过程说:“在1920年冬天,(我)即由湖南一位相信社会主义的老先生贺民范介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
鉴于新民学会在1921新年大会以后基本上停止了活动,而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在1920年就开始活动,并且其成员毛泽东和何叔衡在1921年7月参加了创立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以准确地说,自从1920年6月驱张运动结束,至1923年11月10日赵恒惕封闭湖南自修大学近三年半的时间里,船山学社是被新民学会和一些早期共产主义者和共产党员所“接管”。应该说,这是船山学社发展史上最光辉的一页。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做了两件大事。
其一,是组织中韩互助社。《毛泽东年谱》1921年3月14日条:“同何叔衡、贺民范等二十八人发起组织长沙中韩互助社,支持朝鲜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朝鲜原来是中国的属国,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失败,朝鲜脱离中国受日本控制。1910年8月22日,朝鲜被迫接受《日韩合并条约》,被日本灭亡。但朝鲜民间的抗日斗争从未中止。1919年3月1日,朝鲜半岛爆发了反抗日本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爱国运动,逐步扩大为全民族的反日起义。同年4月,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上海成立。1920年冬至次年初,临时政府派遣临时宣传员赵铁君、李松根、李愚氓、赵重九、黄永熙等到中国南方各省,揭露日本侵略韩国的罪行,宣传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及韩国反日独立团体开展之反日斗争。其中,李愚氓、李基彰和黄永熙等人前往湖南进行宣传活动,进一步加深了湖南人民对韩国独立运动的同情,促成了长沙中韩互助社于1921年3月14日在船山学社成立。在成立大会上,通过了《互助社简章》,确定互助社以“联络韩中两国人民,敦修情谊,发展两国人民之事业”为宗旨。据金正明的《朝鲜独立运动》可知,长沙中韩互助社的发起人共31人,其中韩方3人,即李愚氓、黄远熙、李基彰。中国方面28人,有易培基、贺民范、仇鳌、陶毅、任培道、任慕尧、李崇英、刘寿康、罗宗翰、李凤翔、张泉山、肖旭东、王季范、魏浚明、何叔衡、熊梦飞、陈菱会、刘馥、毛泽东、谢焕南、李成于、李抱一、匡日休、方维夏、刘驭皆、易礼容、王世珍、夏丐尊。会上选举了互助社的干部:宣传部主任李基彰、何叔衡;通信部主任黄永熙、毛泽东;经济部主任李愚氓、贺民范。社址即设在船山学社。长沙中韩互助社是中韩友好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它促进了中朝(韩)人民共同抗日的革命运动。
其二,创办湖南自修大学。《毛泽东年谱》1921年8月中旬条在谈到毛泽东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回到长沙,住船山学社……与何叔衡创办湖南自修大学。自修大学是在船山学社董事会总理仇鳌和社长贺民范支持下,利用船山学社社址和经费创办的。贺民范为首任校长,毛泽东任指导主任,负实际领导责任”。鉴于有关湖南自修大学的具体情况,介绍的文章很多,本文不拟再作过多的重复,而只想着重指出两点:
1.现在人们在谈论湖南自修大学时,往往都说它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所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培养革命干部的新型学校,其实湖南自修大学在酝酿和筹备过程中,只是为了创办一个青年的自学机构。早在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写给黎锦熙的信中说:“弟对于学校甚多不满之处,他日当为书与阁下详论之。……弟久思组织私塾,采古讲学与今学校二者之长,暂只以三年为期,课程则以略通国学大要为准。……怀此理想者,四年于兹矣。”这说明他早有创办自学机构的设想。1920年2月,他在写给陶毅的信中说:“湘事平了,回长沙,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或径名自修大学),预计一年或二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然后组一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 同年3月14日,他在写给周世钊的信中又说:“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之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这时虽然已经明确提出自修大学的名字,但是如毛泽东在致周世钊同一封信所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 。就是说,这时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直到这年夏天,毛泽东才从理论上完成世界观的转变。此时,中国共产党尚没有成立,创办自修大学的努力当然不可能是建立共产党的党校。正是因为湖南自修大学的初衷是作为青年自学机构而提出的,所以才能得到自由主义者胡适的大力支持并为之取名。还必须指出,1921年上半年,即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毛泽东和他的好友萧子升虽然在政治思想上开始分道扬镳,但在办自修大学上的意见却是十分一致的。萧氏说过,毛泽东和他提了个建议,将船山学社改为自修大学。大家都同意这个建议,他成了主要策划人之一。萧氏认为,自修大学始终是一种理想的制度,因为它强调自已学习,就像中国古时候的书院,没有固定的作息时间,也没有教师。只是必须有大量丰富的参考书籍和一间好的实验室,还必须有人组织学生开会和讨论。我向北京上海的知识界教育界询问意见,得到了一些好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国学大师章太炎都以漂亮的字体给我写了长信,表示他们的赞同。我还接到吴稚晕的一封长信,分析自学制度的可能性。这说明,湖南自修大学即使到了正式开始筹备时,也还是以自学组织的名义进行的。1921年8月发布的《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开篇称:“人是不能不求学的,求学是要有一块地方并且要有一种组织的。从前求学的地方在书院,书院废而为学校,世人便争毁书院,争誉学校。”这时毛泽东已经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他心中要办的湖南自修大学已经是为党培养干部的学校,但是为了争取更多人支持,包括像国民党的元老、船山学社董事会总理仇鳌这样人物的支持,他还是不得不把自修大学的性质泛化,把它说成是一个青年自学机构。要说这是一种策略也未尝不可。
2.毛泽东等人选择船山学社创办湖南自修大学,从物质方面说,固然是利用了船山学社的经费和社址,从精神方面来说,则应该说是继承了船山学社的前身思贤讲舍这个由郭嵩焘创办的改良式书院的优良传统。思贤讲舍是郭嵩焘于1881年所创办的一所近代书院。郭氏在19世纪70年代出使中国驻英法首任公使以前,就对中国的书院沦为科举的附庸这一状况十分不满;出使英法之后,亲见西方学校比中国的先进,“大抵规模整肃,讨论精详,而一皆致之实用,不为虚文”。所以他回国后说:“予谋别立书院 ,讲求征实致用之学。”郭嵩焘在创办思贤讲舍的过程中,还曾积极支持恢复湘水校经堂,当时有一份《伪校经堂奇闻》的匿名帖,攻击郭氏“不讲时文试帖,而讲天文算学,其计狡毒”。而思贤讲舍也是开设了天文算学课的。讲舍还利用屈原、周敦颐、王夫之、曾国藩的生日举行祭祀讲会,议论时政,实际上是引导学生讲求征实致用之学。青年毛泽东对郭嵩焘是十分尊崇的,对思贤讲舍的历史比较熟悉。所以他所写的《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中,对学校和书院的各自利弊进行了深刻剖析:学校的第一坏处,是师生间没有感情。先生抱一个金钱主义,学生抱一个文凭主义,“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什么施教受教,不过是一种商行为罢了!学校的第二坏处,是用一种划一的机械的教授法和管理法,去戕贼人性。学校的第三坏处,是钟点过多,课程过繁。书院的好处在于:一来是师生的感情甚笃。二来没有教授管理,但为精神往来,自由研究。三来课程简而研讨周,可以优游暇豫,玩索有得。所以《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在谈到学校的宗旨时指出:“本大学鉴于现在教育制度之缺失,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使文化普及于平民,术学周流于社会,由湖南船山学社创设,定名‘湖南自修大学’。”
湖南自修大学的学友,大部分是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自修大学学友人数,在1923年3月有24名。同月,又公开招生,“征求确实能自修的新同学10名”,前后合计30余名.计有毛泽东、何叔衡、李维汉、贺民范、夏明翰、易礼容、罗学瓒、姜梦周、陈佑魁、毛泽民、陈章甫、陈子传、陈子展、彭平之、曹典琦、廖锡瑞、刘春仁、戴晓云、刘大身、邹亮、夏曦、贺果、王梁、傅昌饪、黄衍仁、王会悟、杨开慧、许文煊等。附设补习学校学生,初办时有陈赓、贺尔康、毛泽覃、高文华、张琼等114人,结束时有补习班3个,初中班1个,共计200余人。它不愧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干部学校。1923年11月10日被湖南省长赵恒惕封闭。在它存在的两年多时间里,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美国著名的毛泽东研究专家施拉姆说:“‘自修大学’设在船山学社。这决非一个偶然的枝节问题,恰恰相反,它可以被看作日后在毛泽东领导下所形成的中国革命道路的象征。因为‘自修大学’虽然极其强调新思想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但也非常重视中国的文化传统,其中特别包括像王夫之这样的持批判态度的唯物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家。中国共产党许多未来的干部,都是这个学校的学生,毛泽东在参加那里举行的各种讨论会的过程中,继续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奠定基础,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正是他后来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最大成就。”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
船山学社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不久停止活动,而毛泽东深带感情为它两次题额。1950年农历九月初一是王船山诞辰日,毛泽东亲自书写“船山学社”四个大字寄来。1953年,中央政务院颁发文物保护条例,船山学社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根据这个条例的规定,湖南省文化局于1954年拨款5万元重新修建湖南船山学社社址。1956年,湖南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陈文骏(?)函请毛泽东为重建的船山学社题额。毛泽东接信后,再次题写了“船山学社”四字。
(作者系本馆馆员)
注释:
1《杨昌济集》(一),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505页。
2《杨昌济集》(一),第506页。
3《杨昌济集》(一),第568页。
4 萧三:《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湖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7页。
5《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0页。
6《杨昌济集》,第512页。
7《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0页。
8 刘志盛、刘萍:《王船山著作考》附录《湖南船山学社大事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8—314页。
9《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4—45页。
10《毛泽东传》(1893—1949),第24页。
11《杨昌济集》,第250页。
12《毛泽东早期文稿》,第377页。
13《毛泽东早期文稿》,428页。
14《船山全书》第12册,第479页。
15《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31页。
16《杨昌济集》,第252—253页。
17《毛泽东早期文稿》,第378页。
18《毛泽东早期文稿》,第337—338页。
19萧瑜:《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第160页。
20《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07页。
21《刘少奇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4—25页。
22《毛泽东年谱》(198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82页。
23 参见李永春:《长沙中韩互助社述论》,《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年第6期。
24《毛泽东年谱》(1983—1949)上卷,第86页。
25唐振南:《船山学社与湖南自修大学》,《船山学报》1986年第2期;李永春:《毛泽东创办湖南自修大学的几个问题》,《 毛泽东思想研究》2007年第3期,等等。
26《毛泽东早期文稿》,第76页。
27《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20页。
28《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29页。
29萧瑜:《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第161页。
30《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东方杂志》第20卷第6号,1923年3月26日出版。
31《郭嵩焘诗文集》,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196页。
32《郭嵩焘日记》第3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19页。
33《郭嵩焘日记》第3卷,第935页。
34、1921年8月16日至20日湖南《大公报》。
35 参见唐振南:《船山学社与湖南自修大学》,《船山学报》1986年第2期。
36 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红旗出版社1987年版,第46页。
37刘志盛、刘萍:《王船山著作考》附录《湖南船山学社大事记》,第339—341页。
【毛泽东与船山学社】王兴国2021年2期总124
2021-08-03 15:52:37 来源: 评论:0 点击:
分享到:
相关热词搜索:
上一篇:【毛泽东长沙早期革命活动的三个“大本营”】朱习文2021年2期总124
下一篇:【关于湖南早期党组织的回忆】易礼容2021年2期总124
分享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