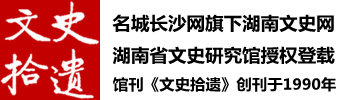开放求变与固步自封
——“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湘学特征和湖南社会
道光二十年(1840),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古老的中国从此陷入“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①中,闭关锁国、天下一统的封建旧格局被列强侵夺、危机四伏的世界新秩序所替代,自然经济体式在封建经济内部滋生的资本主义因素和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双重夹击下不可抗拒地走向解体,“以夏变夷”的传统文化状态和固有思维模式遭遇历经工业革命、实力突飞猛进的欧洲资本主义诸国的严峻挑战,中国社会的转型开始了极其艰难的历程。
在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文化和中国封建文化的激烈冲突中,一批较早觉醒的开明官员和知识分子摒弃传统文化本位的立场,倡导吸收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和技术。尽管从根本上说,他们仍然固守着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纲常伦理和教育制度,只是从器物层面上提倡向西方学习,颇有一种文化折衷的意味,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萌发了以西方科学和技术为我用、革新政治、改变学风的意识,即具有了惊世骇俗的思想启蒙作用,促使中国迈出了有效应对亘古未有的时代巨变的第一步。
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发展时期,也是湘学发展史上极为关键的复兴并走向繁盛的时期。
清代嘉庆、道光、咸丰年间,湘学迎来了得以复兴的发展阶段。这时,湖南出现了近代史上颇有影响的人才群体——中国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人,包括贺长龄、贺熙龄、魏源、邓显鹤、汤鹏、邹汉勋、严如熤等,学术上称为经学主变派。他们最早接受和宣传王夫之的学术思想,重经世,讲躬行,以追求“朴”、“实”的学风横扫理学的虚矫、汉学考据的琐碎、文章辞藻的浮华。他们的观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敬天、法古、重农抑商发展到顺人、通今、本末并重,从拒“夷”发展到师“夷”以制“夷”。他们交往甚密,为清廷的腐败软弱、西人的强势入侵而忧心,苦苦探寻救国利民之道,并以经世致用的杰出成就闻名于政治界、思想学术界。
在这个群体中,魏源的影响最大,被视为湘学复兴的旗帜。他以研究春秋公羊学为阶梯,在继承和发扬湖湘重躬行的学风、强化经世致用理念的同时,富有独创地融入近代西方文化的元素,全面提出改革吏治、开通言路、吸收外资、振兴工业、提拔人才、开启民智、严禁鸦片、增强国防等救世治国之道,屡开学术新风。他一生著述四十七种,六百余卷,约八百万字,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历史、地理、文化、教育、外交和近代自然科学等。成书于道光六年(1826)的《皇朝经世文编》是他的第一部经世之作,以切于事、合于今为选文原则,从清初至道光五年(1825)的官方文书、官员奏议、学者论著书札和方志中,采录具有实用价值的二千二百三十六篇文章,是晚清经世思想复兴的公开宣言,有力促进了晚清务实、改革思潮的兴起。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魏源有感于林则徐罢官、鸦片战争失败,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写成《圣武记》这部探索清代盛衰的史书和军事理论著作,探讨兵制兵饷、攻守策略、发展经济等问题,推求盛衰之理,筹划消防之策,警示人心、匡时治世的用心尤为显豁。同年年底,闭关锁国时代第一部由中国人自编的最为详备的介绍世界各国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宗教和社会风情、民俗文化等知识的百科全书式的巨著《海国图志》五十卷完成(道光二十七年增补为一百卷),这部“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②的书籍广为传播,加快了中国冰冻已久的土层复苏的步伐,为近代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提供了有效的思想资源和改革途径。
魏源不仅通过著书立说实现了湘学的近代转型,而且投身到重大的经世实践活动中,立下了彪炳后世的经世事功。由于屡遭官场排斥,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充当地方督抚的幕僚,其经世才干得到充分发挥,成为当时著名的海运、河工、盐政、币制四大改革的专家。如清廷实施漕运由河改海的领导者名义上是陶澍和贺长龄,实际上,这一改革的顶层方案的设计者和具体实施的督办者却是他。他代为拟写的《复魏制府询海运书》化解了来自两江总督魏元煜对改革的阻碍,他编制的《海运全案》序、跋和《筹粮篇》论述了漕运改革的必要性和实施海运的要点,不仅因为合理利用海运优势、商人资力以及提高航道、船只的工作效率而节省了大量的输漕费用,减轻了百姓的负担,而且整治了敲诈勒索、贪污贿赂等漕运弊端,革除了长期困扰政府的一大顽疾。又如时任两江总督的陶澍奉命整顿两淮盐务,魏源以幕僚身份成为盐法改革的实际筹划者。他制订改革章程,力主裁减各流通环节的浮费以消除弊政、降低盐价,改变固定的销售配额和区域以保证流通渠道的顺畅,挤占私盐市场以增加朝廷的税收,在淮北地区试行盐票制以打破引商对盐务销售的垄断。这一系列改革举措使许多盐务陋规失效,遏制了腐败的滋生,调动了盐商的积极性,扭转了淮北盐课长期亏欠的局面。
在经学主变派开启时代新风后,出现了以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等人为代表的湘学名家以及湘军集团人才群体,群贤的影响力整体性地发挥出来,使湘学发展到极盛的阶段。这些湘学名家大都尊崇理学,强调内圣与外王并重,把经世之学与讲求大本大原的天道性命之学结合起来,通经学古而致诸用。他们通过整顿吏治、治理军队以及改革河工、海运和盐政等发扬湘学经世致用的特征,在实学中增加了西方自然科学的内容。
湘军集团的核心人物、洋务运动的领袖之一曾国藩影响颇大。他主持刊刻《船山遗书》三百二十卷,有诗文集、《经史百家杂钞》等一百八十五卷。他毕生服膺程朱理学,于朱熹受益颇多,是正统理学的传人。他认为“理”是世界的本质,是万事万物的本源,主张以理学治国平天下。他倡导仁爱信恕的道德观念,标榜忠孝至上的人伦价值,恪守淡泊勤俭的立身准则,被视为中国传统人格的典范人物。他讲求经世济时之道,追求治术上的“综合名实”、学术上的“笃实践履”。他崇尚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气节,注重从《船山遗书》中吸取思想资源,以求治国、用兵之道。
作为近代在理学上造诣颇深的一位大儒,他的卓越贡献在于他不是沉溺于对心性之学的玄谈中,而是着意于实行、实用和实功,通过倡导和推行洋务运动来实现经世致用、富国强兵的目的,成为最早将经世之学引入洋务运动的士大夫之一。他率先筹设了中国第一家近代军事工厂——安庆内军械所,制造出中国第一艘轮船“黄鹄号”;他派最早留学美国的容闳赴美购买机器,谋划在中国建立正式的近代机器工业;他与李鸿章共同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近代军事综合工业大厂——江南机器制造局,制造出中国第一艘军舰“恬吉”号,还生产出4800吨的民用轮船“江华”号;他设立翻译馆,大量翻译西方科学技术书籍;他附设机械学校,培养生产技术力量,开我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先河;他几次听取容闳派遣留学生学习军事、船政、步算、制造诸学的建议,相信通过西方教育可以使中国走向富强之路,并亲自把关考试,从同治十二年(1872)起,分4批选派120名中国青少年精英赴美留学,揭开了我国向西方派遣留学生的历史。这些举措促进了我国科学技术和近代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也促使了近代人才群体的崛起。
要之,中日甲午战争之前,一批站在时代前列的湘学名家崭露头角,他们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以及他们的躬身实践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在洋务运动的先驱和领袖人物中,湖南人占了多数,正如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所言:“中国首讲西学者,为魏源氏、郭嵩焘氏、曾纪泽氏,皆湖南人。”③
然而,与这种学术发展极不相称的是,在这一时期,湖南绅民的思想极为保守而又顽固。他们大多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盲目自信,固守仇夷排外的封闭立场,持续不断地营造抗拒洋务的声势,以至于在外国传教士眼中,长沙乃至湖南已经成为《圣经·创世纪》中“拒绝文化洗礼”的“铁门之城”④——一个与时代脱节的顽固保守的大本营,以至于湖南在洋务运动中陷入沉寂,如张朋园所言:“自鸦片战争至英法联军之役,中国所发生的‘三千年变局’,湖南人是无动于衷的。湖南人的守旧态度,有似一口古井,外在的激荡,没有引起些许涟漪。所以,当自强运动在沿海地区进展的时候,湖南人仍然在酣睡之中,三十余年的自强运动(1860至1894),于湖南人几乎完全是陌生的。”⑤由于湘人的极力抵制,这块封闭保守的土地并没有接受多少新知识和近代科学技术的叩击。
湖南在近代素以反洋教著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自咸丰十年(1860)至光绪二十年(1894),湘人不顾朝廷的三令五申,发动了十余起较大规模的打教、反教事件,他们或焚毁教堂,或驱逐教士,或散发揭帖,或杀死教士教民,引起了外交上的严重交涉。其中,咸丰十一年(1861)发生在长沙的数千人聚集于明伦堂口诛笔伐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将反教檄文散发至湖南各地和临近各省的事件,确立了长沙作为近代反洋教宣传中心的地位;寄居长沙的宁乡士绅周汉等人在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持续的反洋教活动中编印、刊刻、散发大量宣传资料,促使长江流域各省人民反洋教的情绪高昂,引发各国领事要求清政府出面干预,凸显了近代长沙在反教浪潮中的重要作用。咸丰八年(1858)签订的《天津条约》规定增开通商口岸、外国人可到内地游历和通商、外国传教士可在中国自由传教,但至光绪十六年(1890),湖南还没有一座新教总堂(广东已有近50座)、一所教会学校(全国已有1000多所)。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以前,没有一个国家的传教士能在长沙立足。当时的《国闻报》载时人言:“中国通商数十年,而洋人之车辙马迹于湘省独希,即一切泰西利国新法,亦丝毫不能举行。”⑥《申报》亦云:“湘中向不与外人通,读书积古之儒,几至耻闻洋务,西人所谓守旧之党,莫湘人若也。”⑦
此外,曾国藩、郭嵩焘、张之洞、吴大澂等人因宣传、推行洋务而饱受湘人冷眼相待的遭遇也是典型的例证。同治十一年(1872)五月,曾国藩在金陵病逝,其灵柩由新式轮船“威靖”号运返湖南故乡。当轮船到达长沙时,仇视洋物的士绅为之哗然,议论数年而不休。光绪二年(1876),郭嵩焘奉旨赴英处理“马嘉理案”的善后问题,成为中国第一位驻外使节。此事在朝野上下引起轩然大波,守旧的湖南士绅群情激愤,将他看作出卖中国利益的汉奸,指责他给湖南人蒙羞。有人编写了一副尖刻的对联羞辱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见容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⑧甚至在郭嵩焘出使这一年的湖南秋闱考试期间,岳麓、城南两书院的诸生和各地来长沙参加乡试的士子会集于玉泉山声讨郭嵩焘,并在宁乡绅士崔暕的鼓动下,纵火焚毁了他倡议修复的上林寺,并一度冲击他的老宅。后来,郭嵩焘记录出使见闻的《使西纪程》因被长沙和各地守旧士绅鄙夷和攻击而遭毁版。他在一片指责、唾骂声中提前结束任期黯然回乡时,立即引来湖南守旧势力的围攻,他们阻止拖带他坐船的小火轮驶入省河,贬斥他“勾通洋人”等揭帖布满长沙街头,甚至出现在他的老家湘阴。这位饱尝酸甜苦辣的西学先驱在长沙郁郁而终,死后仍有人要求开棺鞭戮其尸,以谢天下。湖广总督张之洞为方便行政管理,在光绪十六年(1890)前后着手架设汉口至长沙等地的电报线,却因沿途湘民拔杆毁线而作罢,使湖南电讯业的创建延迟了数年,至光绪二十二年(1896),长沙与北京才有收发电报的记载。光绪十八年(1892),具有洋务意识的吴大澂出任湖南巡抚,保守士绅周汉等人发布《湖南通省公议》,斥责他“夙讲洋务,勾结夷鬼”,号召湘人把他驱除出境,可见地方保守士绅的声势之大。
凡此种种,都生动表现了湖南绅民拒绝“睁眼看世界”和顽固抵制洋务的情状,这一切严重阻碍了湖南向现代化转型的步伐。与沿海各省相比,湖南的现代化变迁至少落后了二三十年,直至进入二十世纪才开始有明显的变化。如在城市近代工业的创始方面,长沙第一家近代企业湘裕炼矿公司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建立,比上海晚30年,比天津晚28年,比兰州晚17年。又如在近代电讯业的建设方面,使用电话最早的中国城市是上海,光绪七年(1881),英国伦敦东洋电话公司在上海取得专利权18年,湖南电话则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由巡抚端方指派候补知县朱文学筹设电话局后才有,且因费用昂贵,应者寥寥。此外,至1894年,全国已有数百家民族资本主义、官办、官督商办和外国资本主义在华企业,湖南却无一家。
综观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三十年的湖南社会,基本上处于发展停滞的状态。在这三十年里,湖南社会经济依然是传统的小农经济,农业改革尚未起步。湖南没有出现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工矿企业,以及交通、邮电设施,直至陈宝箴抚湘的新政时期,才陆续成立了湖南矿务总局、宝善成机器制造局、鄂湘善后航船局等。湖南没有产生近代化的新闻、出版、印刷和公共图书事业,也没有出现一所改革旧模式、传授新知识的新式学堂,更无人顾及有关政治制度、法治制度、军队制度的改变。湖南的文化复古之风根深蒂固,文人学士大多固步自封,或空谈心性理学,或醉心考据训诂,或沉湎八股制艺,在学术建构上未能突破传统儒学的藩篱。总之,此时的湖南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守旧排外的独立王国,几乎谈不上有什么进步;此时的湖南人普遍缺乏发展变化的新观念、新视野,沉浸在死气沉沉的守旧氛围中,丧失了勃发的生机。
探究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首先,从湘学思想的传承和近代早期湘学的特征看。如前所述,湘学于南宋形成,盛极一时的湖湘学派包容众家之长、尊奉理学思想、注重经世务实的学风氤氲于三湘四水间,对湖南一代代士人产生了久远而深刻的影响。湘学的发展进入近代,具有相当深厚的维护道统和经世致用的特点。维护道统与“华夷之辨”的民族主义思想相通,包含“尊王”和“攘夷”两个基本原则,“尊王”宣讲的是“君为臣纲”的政治理论,为封建统治者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需要提供伦理支撑和理论依据;“攘夷”倡导的是反对外族侵略的民族精神,突出华夏文化的优越性。经世致用与心性之学相结合,奠定了湖湘学人践行知行合一、自强不息、敢为人先的实学思想和实干作风,逐渐凝聚成湖湘文化的优良传统,铸造着湖南人的性格。湘学的这两个特点对近代早期的湖南产生的作用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维护道统容易滋生保守自大、封闭排外的心理,形成阻碍湖南现代化进程的不利因素;另一方面,经世致用造就了近代早期一批湖湘经世派、洋务派的优秀人物,他们才识卓荦,强调理学的“躬行”、“践履”,在开放中求变,成为推进湖南乃至全国现代化进程的先知先觉者,他们富有成效的建树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导夫先路、开启未来的重要作用和深远影响。封闭、守旧势力与开放、求变力量各自生成,彼此纠结,而在当时的湖南,前者牢牢地占据着主导地位,后者也时刻在谋求有所突破。在近代思想启蒙和洋务运动的进程中,湖南就一直处于这种不谐调的状态中。
其次,从湖南的地域特征、历史发展和湖南人的主导性格看。湖南东、南、西三面环山,东为幕阜、罗霄山脉,南有五岭山脉,西是武陵、雪峰山脉,五分之四的地域为山区,近代以前,交通极不便利。湖湘大地史前时期主要是三苗、南蛮人活动的区域,而在湖南中部地区,丘陵与河谷盆地相间,湖南境内奔流着湘、资、沅、澧四大水系,优厚的生存条件吸引了大量外来民迁入,土著与移民的相互争斗从未间断。相对闭塞的地理因素和长期的竞争环境磨砺出剽悍、倔强的湖南民性,湖南人一旦认定了追求的目标,就会团结一致,无所顾忌,勇往直前,不屑改变。这种性格既能够培育出摧枯拉朽的建设性力量,也可以造成对社会发展的破坏性后果。前者酝酿出的是激进的思想火花,后者则容易滋生虚妄骄狂、顽固保守的情绪,形成抑制、扼杀前者的逼仄的社会环境,引发抗拒一切外来文化和超越时代观念的行为。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湖南的有识之士一旦离开本土,放眼外部世界,就会大显身手,成就一番事业,陶澍、贺长龄、魏源、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曾纪泽等等,莫不如此。而他们一旦回到湖南,就难以施展拳脚,甚至遭受围攻和打压。
再次,从湘军集团的崛起和完胜太平军的战绩看。清代咸同之前,湖南人在全国的政局中默默无闻,如杨毓麟所言:
咸同以前,我湖南人碌碌无所轻重于天下,亦几不知有所谓对于天下之责任。知有所谓对于天下之责任者,当自洪杨之难始。⑨
咸同年间,湘军集团的领袖和精英人物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胡林翼、罗泽南等将经世致用的湖湘学术精神转换为忠君卫道的政治实践,组建湘军以对付席卷东南的洪秀全队伍。他们笃宗理学,以传统的儒家思想为治军要诀,用维护传统的儒家伦理为旗帜号召天下,使镇压太平天国叛军的朝廷保卫战带上了浓厚的捍卫名教圣统的文化保卫战的色彩,这有效地触动了湖南人固有的倔强、勇敢、执拗的性格,激励着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这场你死我活的战争中。在历经十余年的对抗后,湘军将雄踞金陵的用上帝教武装起来的异教大军打得一败涂地,不仅挽救了清王朝岌岌可危的命运,也完成了延续正统文化的光荣使命,使湖南一时跃升到传统文化的中心地位,并在政坛上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全国各省的地方大权几乎都落在了湘人手中。就是这场战争的胜利,进一步助长了湖南人坚守儒家道统的荣誉感和使命意识,形成一种极端热忱的卫道意识和救世观念,以及“守先待后,舍我其谁”的英雄气概。同时,也进一步强化了湖南人鄙夷西方、耻闻洋务的自负心态,演变为一种深厚的文化本位主义和顽固的保守排外理念,造成湖南本土的洋务运动在这一时期几乎无所建树,这样的结果是令人感到悲哀的。
因此,中日甲午战争之前的湖南既产生了最早认识世界、改良社会的人,又被视为中国最保守的大本营,激进与守旧难以想象地并存于这片土地上。湖南巡抚陈宝箴后来就此评价道:
咸丰以来……名臣儒将,多出于湘,其民气之勇,士节之盛,实甲于天下。而视其忠肝义胆,敌王所忾,不愿师他人之长,其义愤激烈之气,鄙夷不屑之心,亦以湘人为最。⑩
值得一提的是,在同时代的湘学名家中,郭嵩焘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现实社会的认识更敏锐,他意识到中国学习西方的富强之术,最关键的是效法西方的政治制度,而不仅仅是在固守孔孟之道和君主专制制度的基础上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工艺技术和坚船利炮。他的洋务思想超越了同时代的洋务实践家,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切中了三十余年洋务新政的要害,其中的一些观念还成为维新思潮的滥觞。特别是他由于为官屡遭败绩,大部分时间在湖南著述讲学、宣传和推行洋务新政,使闭塞的湖南开始吹进一股讲求洋务的新风。不过,因为他并没有完全冲破洋务运动“中体西用”的理论框架,兼之个体的力量终究单薄,湖南的保守势力依然强大,更富有声势、更激荡人心的变革还有待后来者的精彩演绎。
注释:
①康有为《上清帝第四书》,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三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75页。
②《魏源集》上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07页。
③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00页。
④《湖南历史资料》1958年第4期,第38页。
⑤张朋园《湖南现代化的早期进展》岳麓书社2002年版,第137页。
⑥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03页。
⑦《申报》,1898年第9074号,上海书店影印本,1982年。
⑧王闿运《湘绮楼日记》第一册,光绪二年三月三日,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460页。
⑨杨毓麟《新湖南》,《湖南历史资料》1959年第3期,第70页。
⑩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四),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051页。
(作者单位:湖南商学院)
分享到:
评论排行
频道总排行
频道本月排行
- 14【“沩痴寄庐”及新民学会人才群体】陈先枢 梁小进2021...
- 14【毛泽东长沙早期革命活动的三个“大本营”】朱习文2021...
- 13【梁启超与湖南时务学堂】丁平一2015年4期总102
- 11【毛泽东与船山学社】王兴国2021年2期总124
- 8【湖南近代著名教育家曹典球述评】丁平一2020年4期总122
- 8【浅析杜甫湖南诗中的政治情怀】糜良玲2012年4期总90
- 7【辛亥革命后长沙知识分子对学习西方文化的探索】杨锡贵...
- 7【七十年中国湘菜研究史述略】尧育飞2021年1期总123
- 5【先驱之血与后见之明:关于谭嗣同评价的几个问题】张玉...
- 5【身在潇湘第一州—元代中越交往中的若干资料】汤军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