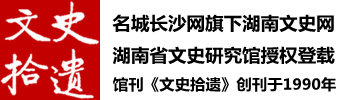谭嗣同是近代历史上著名的维新变法先驱,也是“戊戌六君子”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人。近年来,学界和媒体对谭嗣同的评价越来越丰富,甚至出现争议,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本文拟就有关谭嗣同评价的几个问题,如“卖地说”、《仁学》思想驳杂缺乏体系、盲目激进破坏多于建设以及思想究竟反清还是忠君等问题,结合谭氏本人著述与史实,略作考辨,以就教于方家。
一、关于“卖地说”
谭嗣同在面对民族与国家危机进行探索时,提出过一个在今天看来骇人听闻、极不“靠谱”的设想,那就是将广袤的边陲土地让与列强以换取资金以应对数额巨大的战争赔款和变法改革的资金缺口。这一设想,无论从观念的正确性还是操作层面的可行性,在今人看来,固然都令人咂舌。有一些观点把“卖地说”归为维新派独有的观点,进而认为,戊戌变法期间,谭嗣同位列军机四章京,可谓权力中枢的国家决策架构师,因此得出结论:幸亏戊戌变法失败,否则上述设想若付诸实施,国家与民族不堪设想。如刘岭峰《梁启超谭嗣同传中有关史料辨伪》中,在引述谭嗣同“卖地说”后就总结道:“由此可见维新人士说话办事,远没有袁世凯说话谨慎可靠。”除了专业学者以外,一些媒体作家也持类似意见,如谌旭彬发表在《短史记》上的题为“谭嗣同欲‘尽卖西藏于英吉利’”的文章,导语谓:“以康有为、谭嗣同为核心的‘康党’曾一度占据了晚清改革的中心舞台,最终却以悲剧告终。究其根源,康党自身之浮躁实乃主因。康、谭师徒戊戌前后念念不忘卖掉藏满疆蒙之地以筹措改革经费,即是明证。”
这一观点有许多值得商榷之处。谭嗣同服膺南海固是事实,然两人观念绝非一致。以概念模糊的“戊戌前后”笼统而固化地概括谭嗣同的思想,耸动观听则颇有余,以昭信实则尚不足。兹就谭嗣同“卖地说”稍加辨正,略述己意,以供方家批评。
(一)提出场合
这一提法,是谭嗣同在给师友的信函中作为试行方案提出的,并非公开出版物。写给老师欧阳中鹄的书信中云:
试为今之时势筹之,已割之地,不必论矣。益当尽卖新疆于俄罗斯,尽卖西藏于英吉利,以偿清二万万之欠款。以二境方数万里之大,我之力终不能守,徒为我之累赘,而卖之则不止值二万万,仍可多取值以为变法之用,兼请英俄保护中国十年。……费如不足,则满洲、蒙古缘边之地,亦皆可卖,统计所卖之地之值,当近十万万。盖新疆一省之地,已不下二万万方里,以至贱之价,每方里亦当卖银五两,是新疆已应得十万万,而吾情愿少得价者,以为十年保护之资也。
写给友人贝元征的书信中云:
若无内国债可举,而择祸莫如轻,莫如俗谚“与其欠钱,不如卖田”。……今夫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大而寒瘠,毫无利于中国,反岁费数百万金戍守之。地接英俄,久为二国垂涎。一旦来争,度我之力,终不能守,不如及今分卖于二国,犹可结其欢心而坐获厚利。……计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不下二千万方里,每方里得价五十两,已不下十万万。除偿赔款外,所余尚多,可供变法之用矣。
固然,前者后来以《兴算学议》为题,由欧阳中鹄删削后刊行,后者也发表在维新同志麦仲华编纂的《皇朝经世文新编》中,但其最初,是在作为师友间交流思想的私人书信中提出的。这与康有为明显不同,其目的不是宣扬政治实践主张,而是探索救国方案。
(二)提出时间
前引两信,皆成于光绪二十一年乙未(1895),其时,谭嗣同尚未得与康有为结识。也就是说,谭所提出的“卖地说”,是独立思考的结果,并非成为“康党”后;谭提此方案,更非所谓成为“国家高层政治政策架构师”的时候,而是早在甲午战败马关签约、三国干涉还辽的1895年。那时举国知识分子笼罩在败亡瓜分的阴影里,有志之士探索救亡之路的方案,且当时认为台湾膏腴之省、辽东“龙兴”之地尚不可守,新疆西藏青海等更无力保护,“卖地说”自有其理路。
而同样重要的是,根据现有文献,除前引两处与师友探讨之外,谭嗣同此后发表的文章不少,似未见再提出过此一方案。前引谌旭彬先生于《短史记》所谓“康、谭师徒戊戌前后念念不忘卖掉”之说,稍嫌粘连,戊戌后谭氏何时提出,未知何所据而云然。
(三)提出者
其时卖地之说不仅仅是维新派独有的方案,许多在一些研究者眼中“谨慎可靠”、更具政治操作经验的清廷重臣,也有此议。
《光绪朝东华录》记载了张之洞致总署的电报:“威、旅乃北洋门户,台湾乃南洋咽喉。今朝廷既肯割此两处与倭,何不即以此与倭者转而赂英、俄乎?所失不及其半,即可转败为胜。惟有恳请饬总署及出使大臣与俄国商定密约,如有助我攻倭,胁倭尽废全约,即酌量划分新疆之地或南路回疆数城或北路数城以酬之……若英肯助我,酌量割分西域之后藏一带地让与若干……”张之洞割让之目的在利诱俄、英助我而胁日废约,与谭嗣同、康有为等换取经费发展改革的“逻辑”固然有别,但以挽救当时危机为目的却并非“大有不同”,计划中所割亦并非如一些引者所云“亦止数城”,而是还包括“割分西域之后藏一带地让与若干”。
这一情况恰可证明,无论是换取列强支持制衡日本减少割地损失还是换取经费进行改革,出于挽救当时危机,不管在朝还是在野的有志之士,在积极探索救国方略时,想到割让土地的不是孤例,也不仅限于稳重老臣抑或维新分子。割地或者卖地,只是换取支持还是经费的差别;所拟割让的土地,也只是区域、面积不同而已。
至于在当时的可行性有多少、以现在看来的合理性有多少,则是我们今人根据现在的历史知识与领土观念做出的判断,当时的谭嗣同固然不能有此后见之明,当时更具政治操作经验的重臣如张之洞、“说话更谨慎可靠”的袁世凯是否同样有此后见之明,也需要论证才可服人。
将谭嗣同“卖地说”与康有为“打包捆绑”、视为“康党”主张,是值得商榷的。我国领土神圣不可侵犯,但历史人物处在历史环境当中所做之事、所持思想,不应“以今度古”,以今人的后见之明强加于古人、将古人直接套在现代国家观与政治观当中来立论,以求传播效果则可,以求历史真相则似非明智之举。
二、关于“杂糅说”
谭嗣同最有代表性的著作《仁学》,自问世之初,就不乏关于“杂糅”的批评。在章太炎自定年谱中,于光绪二十三年记载:“会平阳宋恕平子来,与语,甚相得,平子以浏阳谭嗣同所著《仁学》见示,余怪其杂糅,不甚许也。”自兹以往,历代学人对《仁学》之杂糅抵牾,不无批评。2018年许知远的纪录片《十三邀》关于谭嗣同的一集,也以“大杂烩”称之。那么,杂糅矛盾、缺乏系统,是否是谭嗣同为自身知识与能力所限而留下的不足呢?还是有其他什么原因被论者忽略?对此,罗福惠先生在《解读谭嗣同》一文中,征引了谭嗣同给好友唐才常书信中的夫子自道,并有非常精辟的阐释:
这番话则表明他有意按王夫之的主张立论,不避漏失,不求面面俱到,尽管只是从某一角度出发的见解,也力求发挥到极致,形成今人所谓“片面的深刻”或“深刻的片面”。虽然“换位思考”之后,结论可能全然相反,因而自相牾。但是只有把各个“片面”充分展开、将理论讲透之后,才真正有利于比较和综合。
在此笔者想就王夫之著作补充几例,以资佐证。
《诗广传·卫风》云:
“如金如锡”,刚柔际也。“如圭如璧”,方圆契也。明乎刚柔方圆之分合者,崇道而不倚于术者也。不知其分,恒用其半而各不成。不知其合,两端分用而不相通。
《老子衍》第二十九章云:
或雄或雌,或白或黑,或荣或辱,各有对待,不能相通,则我道葢几于穷,而我之有知有守亦不一矣。知者归清,守者归浊,两术剖分,各归其肖,游环中者可知已。
《庄子解·天下篇》云:
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
《尚书引义·咸有一德》云:
道一而已矣,一以尽道矣。
通过前引可知,谭嗣同对王船山关于偏与全、多与一、剖分与相通的思想,是有认真思考的,在《仁学》的写作过程中,固然有无暇等时间紧迫等因素,但我们目前所见看似“杂糅”“牴牾”,绝非他的无心之失。所以在信中他借圣人立言为例说道:
孔子之发言为经,类皆因材施教。因材施教者,佛家所谓因众生之根器当以某等得度者,即为现某等身而为说法。故孔子之言,或大或细,有半有全,犹佛家之有大乘、小乘,有实教、权教,非圣言有异,众生根器不同也。记者误浑连为一编,漫不为区别,复不详记其某一言之发为何地何人何时何事,某为粗、某为精。精杂于粗,则以粗概精而精者亡,粗杂于精,则以精疑粗而粗者亦亡,是以牴牾羼乱而不可就理也。
发言必须有针对性,而若忽略了这一针对性,“不详记其某一言之发为何地何人何时何事,某为粗、某为精”,难免导致对前人立言的理解精粗相杂,甚至会认为其“牴牾羼乱而不可就理”。谭嗣同在此不啻对后之读《仁学》者做了一个很有效也很有必要的提醒。
三、关于“盲目说”
后人评价谭嗣同,固然有敢为人先、勇于革新的褒扬,也不乏缺乏经验、盲目冲动、破坏多于建设的指责。笔者无意于在众多品评之上再加一条,仅就谭嗣同著述与行实中相关材料分析其性格中不惧流血之底蕴。
当然,这一工作前人已做过,如前引刘岭峰《梁启超谭嗣同传中有关史料辨伪》一文,在辨析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所录谭嗣同“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一语,作为对立面引用了袁世凯《戊戌经略》:“谭云:自古非流血不能变法,必须将一切老朽全行杀去,始可办事。”接下来文章论证袁世凯在《戊戌经略》中的许多记述都与事实相符、袁世凯并无与维新派交恶且政变后还营救过维新人士、无理由亦无必要造假。由此认为“袁世凯《戊戌经略》可信度远高于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进而得出结论:“梁启超篡改了谭嗣同关于变法要流血的本意。把一个想‘杀人’成仁的斗士,描述成了一个‘杀身’成仁的斗士。”即便袁氏此作可信度更高,此处关于谭之描述是否即可确信,也缺少必要的论证。
谭嗣同留下的为数有限的文字里,对于“流血”,记述颇多。其中固然有“杀人”者,但更多的是对他人流血的悲悯。如《儿缆船并叙》:“北风蓬蓬,大浪雷吼,小儿曳缆逆风走。惶惶船中人,生死在儿手。缆倒曳儿儿屡仆,持缆愈力缆縻肉。儿肉附缆去,儿掌惟见骨。掌见骨,儿莫哭,儿掌有白骨,江心无白骨。”这种悲悯,通过作者的深刻思考,上升为其思想“仁学”,其中表达了对破除人我之见的追求,和对因人我之见、上下之隔而形成的专制杀人的反抗,如《六盘山转饷谣》:“马足蹩,车轴折,人蹉跌,山岌嶪,朔雁一声天雨雪。舆夫舆夫尔勿嗔,官仅用尔力,尔胡不肯竭?尔不思车中累累物,东南万户之膏血。呜呼!车中累累物,东南万户之膏血。”在《酬宋燕生见赠诗》的自注里,他说:“伦而不言天人,已足杀尽忠臣孝子弟弟,于吞声饮泣莫可名言之中,乃复有纲之残酷济之,所谓流血遍地球,染大地作红色,未足泄数千年亿兆生灵之冤毒,悲夫!”
谭嗣同对于反抗专制而流血,则是推崇的,《仁学》第三十四则云:“法人之改民主也,其言曰:‘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以泄万民之恨。’”他在给老师欧阳中鹄的一封书信(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初六日,1898年6月24日)中云:“平日互相劝勉者,全在‘杀身灭族’四字,岂临小小利害而变其初心乎?耶稣以一匹夫而撄当世之文网,其弟子十二人皆横被诛戮,至今传教者犹以遭杀为荣,此其魄力所以横绝于五大洲,而其学且历二千年而弥盛也。呜呼!人之度量相越岂不远哉!今日中国能闹到新旧两党流血遍地,方有复兴之望。”诚然,谭嗣同所言变法之流血,固然有“杀人”而流血者,但更多的是对耶稣自我牺牲精神的崇尚与自勉。
谭嗣同的破坏绝非杀戮流血,而在于对吃人旧制度与封建社会根基之破坏,这是近代以来仁人志士的共同追求。要而言之,谭嗣同不是破坏多于建设,而恰是为了建设才去破坏;不是不恤流他人之血,而恰是为了众生不再流血而甘愿流自己之血以及阻碍变革者之血。
其实,如果对谭嗣同有足够深入的了解,不难发现,谭嗣同的所谓激进更多是在反对专制的思想层面和相关举措,在具体政治事务的实操层面他有相当稳健的一面。如乙未年(1895)代龙湛霖奏请变通科举时提出的举措,对于变通科举的步骤、试点范围、特例处理,都做了周密妥帖的考量与规划。又如戊戌年(1898)提出试行印花税的方案,也进行了限时、限地等稳妥筹划。以上所举,以当下的眼光衡量无论是否可行,至少可以看出谭嗣同在态度上是较为谨慎周到的。一些论者所谓躁进无措、幸亏未能主持大局否则不堪设想之论,其实还有商榷的余地——姑不论其入军机时尚无权力在实操层面影响中枢决策,即便有此影响力来实施,他是否必然会贸然行事,也是需要实证才能成说的。
更且,谭嗣同一生践行着日新思想,他时时对自己早先探索中不成熟不正确之处进行完善与补正。如在《思纬吉凶台短书》所附早年《治言》的按语里,就大胆坦承自己早年思想的错误,并借以通过对比展示自己思想逐步完善的轨迹。所以,在无确切史料支撑时,我们虽无法断言,但至少没有理由排除他随着时局发展和修为精进而吐故纳新的可能性。
四、关于“反复说”
谭嗣同在《仁学》中,对清政府的专制统治大加挞伐,他也以实际行动践行了其反抗专制政府的思想。著述中的反清思想与早年多次参加科举考试、戊戌年受徐致靖保举进京召见并被任命为军机章京结合起来看,一些人认为这是谭嗣同表里不一的污点——屡试不售则著为高论以炫世自奇,有机会进入权力中枢则毫不推却。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尝试从学理上弥合这种前后看似矛盾或反复之处,以李细珠先生《谭嗣同戊戌进京前后的思想变动及其原因》为代表。
该文试图将这一问题解释为,谭嗣同在戊戌进京前,思想已“由洋务而维新并趋向革命”,达到激进的顶点,但在戊戌蒙保举进京受召见时,由于传统意识的限制,引发“圣恩高厚”、感激涕零的“酬圣主”意识。文章进而总结,以谭嗣同为代表的维新派知识分子,作为“由传统士人向新式知识分子转化的过渡的一代”,在“陶铸新型理想人格——近代人格”之时,也同时“深受传统思想的限制”。该文对谭嗣同思想的探讨,比起片面认为反清或犹疑反复的观点已更进一步,惜其展开论证时有可商之处数端,今不揣浅陋条辨于下,并附己见,敬请方家指教。
(一)“圣恩高厚”
这是谭嗣同进京前写给妻子李闰信中之语,要考虑谭嗣同在与妻子交流时的语境。谭嗣同对于其激进思想是否与其妻分享,目前无史料支撑。更为正常的情况似乎是,蒙举奉召入京事件,在谭嗣同与家人对话的语境中,感戴圣恩本是常语,一如在书信中嘱咐妻子“免得人说嫌话”或仅系夫妻家常语甚或具体实指某事、未必能得出谭嗣同思想上渐趋保守之结论。但这是否是真实想法、以及是否因此便可推论其思想从顶点向传统回退,尚需史料证实。相反的史料倒是有。李文所引谭嗣同得知召见的消息后致李闰之书信,最早的写于五月初二,而在五月初六、初七写给其师傅欧阳中鹄的书信中,却有“平日互相劝勉者,全在‘杀身灭族’四字,岂临小小利害而变其初心”,“今日中国能闹到新旧两党流血遍地,方有复兴之望”等激烈言词,并引佛语波旬曰:“今日但观谁勇猛耳。” 据此,则谭嗣同是否存在一个奉召后就从激进顶点回退的所谓“戊戌进京前后的思想变动”,是值得再深入探讨的。
(二)对“毕士马”之“仰慕”
李文引谭氏于丙申春季候补浙江前留别师友诗,以证其此行既遵父命又有自己的政治追求,似亦可商。如引“海国惟倾毕士马”,谓谭“仰慕‘铁血宰相’俾士麦的功业”,正如前文所述,谭嗣同虽然不惧流血,但其所不惧者乃为反对专制、追求仁与通的理想世界而流血,与发动普法战争在先、镇压工人运动之铁血宰相固自有别,他对毕士马所倾之处,还是从其著述本身寻找答案更为妥帖。谭嗣同在《仁学》和南学会讲演《论学者之不当骄人》中都提到过,俾斯麦虽然赢得普法战争之胜利,但未灭法国以存疆域,惧法之以学反制也。
(三)“建立霸业的政治抱负”、对候补官之“迷恋”
其他阐释这组诗亦多有可商之处,由于误解了诗句典故,而将谭氏的栖迟感慨,解释为“建立霸业的政治抱负”,与谭氏本义恰恰相反。
李文认为谭嗣同“迷恋”候补官,并列出三个理由:(1)引《江上闻笛诗奉怀陈义宁公也连辱见招竟不自拔》“亡命向江海”,认为谭嗣同拒绝回湘协助新政;(2)谭嗣同未能参加挚友吴铁樵之葬礼乃热衷“衙事”;(3)既自言政治上无上升空间、经济上也无保障,却仍不肯舍弃。(2)不必深辩,观李文所引谭氏书信中“本局总办病故,新旧交代之时,局中公事万分纷杂”即可知,因突发事件无暇分身乃人之常情,似不必下一“迷恋”候补官之考语。(1)(3)当注意谭氏当时处境。其时谭嗣同是被迫离湘,这在其致欧阳中鹄书信中说得非常明白,“缘事而去,觉得不值”,“悔恨交并,不知所措”,“贻累亲友,尤觉不安”。唐才质《戊戌闻见录》亦载:“乙未、丙申间,复生以兴算及拟强学会于湘,为拘虚者流所訾,复以告讦贪冒者而开罪簪缨,言官将登白简。斯时也,复生可谓穷矣。顾卢氏闻而益憎之,乃于敬帅前媒蘖其短。敬帅怒,迫复生赴京引见,且送传赞考荫。复生怏怏,然不能违父命,故借此而北游访学焉。”也就是说,谭嗣同的“亡命向江海”、“连辱见招竟不自拔”,乃是迫不得已,并非自愿,更非“迷恋”候补官,其之后的栖迟官场,虽不能断然排除苦撑待变的可能性,但忽略其因父亲盛怒驱之赴任的实际处境,就认为其“迷恋”候补官未加舍弃,似非知言。
(四)结论
纵观谭嗣同之生平与活动可以发现,“反清”与“忠君”并不矛盾,谭嗣同猛烈抨击的是阻绝仁通的专制制度,而非具体一家一姓之政权,只要能冲决此网络,在地方还是在中央权力机构内部推行变法,都是可以接受并值得珍视的机会。他的思想发展轨迹是相对清晰的。甲午之后受“创巨痛深”之震撼毅然与旧学决裂,在地方兴算学、襄实务,固然是探索救国之路的具体方式;限于当时矛盾、迫于严父命令而候补为官,尽管惋悼自伤,但北游访学而真访学,江南宦隐而非宦隐,他力学新知,广交时贤,将新的收获充分融汇贯注于自己的思考,形成了以《仁学》为代表的思想;湖南新政情形好转、客观条件逐渐宽松时,他弃官归里热心参与,时务学堂、南学会、《湘报》等都留下他的心血;新政因保守势力阻挠而陷入困境时,他虽也发出过慨叹,但维新变革之心一以贯之,地方上的自下而上之路遇到阻滞,戊戌蒙举奉召入京、意外获得自上而下推行新政的机会,他也欣喜若狂、义无反顾。这种看似反复的表象之下,是谭嗣同一以贯之的追求。他早已把个人价值系于维新事业、系于对仁通的理想世界的追求。惟其如此,“反清”与“忠君”也就不成矛盾,听闻保举、入京召见的欣喜与感恩有多少是为个人升迁、多少是为维新事业,或已难于剖分也不必剖分,因为维新先驱用其鲜血书写了答案。
结 语
以谭嗣同为例,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笔者认为,当努力排除今人视角下的后见之明。以今天的领土观念和公民意识,谭嗣同的“卖地说”固然绝对荒唐透顶,但还原到当时的历史场景中,则自有其合理因素和思想逻辑。以今天的学术眼光审视《仁学》,当然也有诸多可商之处。以今天的认知和判断标准衡量一百二十年前变法先驱的言行,他们无论思想的成熟性还是方略的可行性都很成问题。但若对比当时的其他人,比如一些论者所言深谙官场权谋、更具政治经验者,他们的主要精力抛于何处?袁世凯姑且不论,即以张之洞在戊戌前夕的活动来看,其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维系信息网络,及时刺探朝局动态,其初始动机是什么?老成诚固然矣,谋国则恐未必。对谭之学说亦当作如是观,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说:
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否则数千年前之陈言旧说,与今日之情势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
治史不易,尤须警惕以今人的后见之明,轻轻抹去炽烈的先驱之血。笔者深为服膺陈寅恪先生“了解之同情”的教诲,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谨以此自勉。(作者单位:中华书局)
注释:
1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2 https://view.news.qq.com/intouchtoday/h215.html
3 《致欧阳瓣姜师》,《谭嗣同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255—256页。
4 《报贝元征》,《谭嗣同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486—487页。
5 康有为是在向皇帝阐述自己政治主张时提出“卖地说”的。在《上清帝第六书》中,他向光绪帝推荐了自己所著的《日本变政考》和《大彼得变政记》,而前书谓日本“割桦太及其地营房于俄”,乃“日人度不能自保,故卖与俄,得其金钱以为兴内利之计”,康有为进而认为,“其边远之荒地不毛,以虚名悬属、不关国本者,则去留不足计,且以易金钱而兴内利。且亦恐既名为属地,一有边事,不救则不可,救之道远莫及,则连兵之后,终必割以与人,故不如早易金钱而修内政,大政可以备举,又不必搜刮民财,此诚善之善也”。
6 茅海建先生根据档案史料,详细考证了军机四卿的具体职能,这四位新进章京并非掌握决策权,详见其《戊戌变法史事考》中相关章节,三联书店2005年版。
7罗福惠:《解读谭嗣同》,《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1期。
8 《与唐绂丞书》,《谭嗣同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207页。
9 《乙未代龙芝生侍郎奏请变通科举先从岁科试起折》,《谭嗣同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178—179页。
10 《试行印花税条说》,《谭嗣同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446—448页。
11 谭嗣同在《治言》小序中说:“此嗣同最少作,于中外是非得失,全未缕悉,妄率胸臆,务为尊己卑人一切迂疏虚骄之论,今知悔矣,附此所以旌吾过,亦冀谈者比而观之,引为戒焉。” 《谭嗣同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507—508页。
12 如联络会党进行活动等,参见邓潭州:《谭嗣同传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3 见田伏隆、朱汉民主编:《谭嗣同与戊戌维新》,岳麓书社1999年。又见李细珠:《变局与抉择:晚清人物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本文引自后者。
14 《致欧阳中鹄》二三(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初六日,1898年6月24日),《谭嗣同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563—564页。
15 《仁学》四一,《谭嗣同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379页。《论学者不当骄人》,《谭嗣同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433—434页。
16 参见拙文《纠结的思考:书籍史、文献学与近代史交叉视域下的仁学》,《中国出版史研究》2020年第4期。详见李让眉、张维欣、张玉亮《谭嗣同诗笺注》,未刊本。
17 《申报》第8795号(九月初八日)“金陵官场纪要”载:“候补道曾广照观察向办筹防局差务,谙练老成,素为上游器重,忽于本月初八日溘然长逝,旋由知府谭嗣同太守赴督辕禀知。”曾广照去世,谭嗣同负责前往两江总督署禀告,系职分安排,无可如何,唯有尽责而已。谭氏于不能参加挚友葬礼,自己颇有分身乏术之叹,不意却蒙后人迷恋官位之讥。
18 《致欧阳中鹄》九(光绪二十二年正月廿八日,1896年3月12日),《谭嗣同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542页。
19 康有为于海外述谭虽多有附会,然亦可做参考。在1901年8月致赵必振书信中,他记述了谭嗣同对张之洞讥诮的反驳:“复生之过鄂,见洞逆,语之曰:‘君非倡自立民权乎?今何赴征?’复生曰:‘民权以救国耳。若上有权,能变法,岂不更胜?’复生至上海,与诸同人论,同人不知权变,犹为守旧论。”
【先驱之血与后见之明:关于谭嗣同评价的几个问题】张玉亮2021年1期总123
2021-08-02 15:00:05 来源: 评论:0 点击:
分享到:
相关热词搜索:
上一篇:【“沩痴寄庐”及新民学会人才群体】陈先枢 梁小进2021年2期总124
下一篇:【齐白石与佛门弟子瑞光交游初探】吕晓2021年1期总123
分享到:
频道总排行
频道本月排行
- 13【梁启超与湖南时务学堂】丁平一2015年4期总102
- 8【“沩痴寄庐”及新民学会人才群体】陈先枢 梁小进2021...
- 8【毛泽东长沙早期革命活动的三个“大本营”】朱习文2021...
- 8【蔡锷与袁世凯】谢本书2019年1期总115
- 7【湘军名将席宝田述论(上)】刘泱泱2019年4期总118
- 7【辛亥革命后长沙知识分子对学习西方文化的探索】杨锡贵...
- 6【湖南近代著名教育家曹典球述评】丁平一2020年4期总122
- 6【七十年中国湘菜研究史述略】尧育飞2021年1期总123
- 6【浅析杜甫湖南诗中的政治情怀】糜良玲2012年4期总90
- 5【身在潇湘第一州—元代中越交往中的若干资料】汤军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