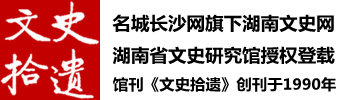郭嵩焘(1818—1891),湖南湘阴人,我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外交家。他一生十分推崇王船山,最早对船山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作出全面的评价。
一
据郭嵩焘自已的记载,他至少从1852年即34岁时起,就系统地阅读船山著作。他在《礼记质疑自序》中说:“咸丰壬子,避乱山中,有终焉之志。读船山《礼记章句》,寻其意旨。”根据郭嵩焘的日记和文集的记载,在同治五年(1866)金陵本《船山遗书》出版之前,他除了系统地阅读过这套《船山遗书》之外,还读过衡阳学署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刊刻的《船山遗书子集五种》。金陵本《船山遗书》出版后,郭嵩焘在得到曾氏兄弟的赠书之后,又于同治七年自费加刷二部。这说明郭氏对船山著作的重视。
金陵本《船山遗书》出版之后,王船山的主要著作都已先后问世,这时要进一步引起人们对船山的重视,就必须加强对船山的宣传。而宣传的最好方式之一,就是为他建祠立庙。恰好在同治九年(1870)郭嵩焘掌教城南书院,于是他利用这个机会,征得巡抚刘崐的支持,在书院内的南轩(张栻)祠旁,修建了一座船山祠。郭嵩焘在船山祠修好后,围绕此祠先后写过几篇文章,实际上是为船山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做出综合的评价。在《船山先生祠安位告示文》中,郭氏写道:
惟吾夫子,笃生衡阳。悟关、闽之微言,寻坠绪之渺茫。当明季之厄运,隐船山以徜徉。校诸子之得失,补群经之散亡。其立身大节,皭然不滓,与河汾、叠山以颉颃。而其斟酌道要,讨论典礼,兼有汉、宋诸儒之长。至于析理之渊微,论事之广大,千载一室,抵掌谈论,惟吾朱子庶几仿佛,而固不逮其精详。盖濂溪周子与吾夫子,相去七百载,屹立相望。揽道学之始终,亘湖湘而有光。其遗书五百卷,历二百余年而始出,嗟既远而弥芳。咸以谓两庑之祀,当在宋五子之列,而至今不获祀于其乡。如嵩焘之薄德,何敢仰希夫子而为之表章!意庶以乡贤之遗业,佑启后进,辟吾楚之榛荒。
让我们来分析一下这段话:
“悟关、闽之微言,寻坠绪之渺茫。”关是指以张载为代表的关学,闽是指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这两派都是宋明理学中的重要派别。这句话是说船山深入领悟了宋明理学的精深微妙的理论,在渺茫的学术海洋中寻找其湮没了的源头。
“校诸子之得失,补群经之散亡。”是说船山在学术上所从事的主要工作,是比较、研判诸子百家在理论上的得失,对儒家的经典散失了义理进行增补和发掘。
“其立身大节,皭然不滓,与河汾、叠山以颉颃。”河汾,指陏末思想家王通(503—574),字公达,南朝大臣。他开创的河汾之学在中国思想史上的主要贡献,是重新发明和发展了先秦儒家的道高于君的道统思想,开启了唐代中叶和宋代的新儒学。叠山,指谢枋得(1226—1289),字君直,号叠山,信州弋阳(今江西省上饶市弋阳县)人。南宋末年著名的爱国诗人,文章奇绝,学通六经,淹贯百家。担任六部侍郎,带领义军在江东抗元,被俘不屈,在北京殉国。这句话是说,船山的的志节高尚,纯净洁白不受任何污染,与王通和谢枋得不相上下。
“斟酌道要,讨论典礼,兼有汉、宋诸儒之长。”汉、宋诸儒,指汉学家和宋学家,前者长于考证,后者长于义理。这句话是说,船山在思考哲理或研究典章制度时,吸收了汉学和宋学两家之长,既善于说理,又善于考证。
“至于析理之渊微,论事之广大,千载一室,抵掌谈论,惟吾朱子庶几仿佛,而固不逮其精详。”“千载一室”,出自明人张元凯《东览篇》“考槃一室已千载”。考槃,直译为成德乐道,喻意为隐居。朱子指朱熹。这句话是说,船山分析理论的渊博和精微,论述史事和时事的广阔和博大,犹如隐居一室,眼观千载,击掌而谈,这种水平只有朱熹差不多相似,但朱氏不及船山之精确和详尽。
“盖濂溪周子与吾夫子,相去七百载,屹立相望。揽道学之始终,亘湖湘而有光。”周子,指周敦颐。周氏生于1017,船山生于1619,二者相去七百个年头。揽,指包揽。亘,空间和时间上延续不断。这句话是说,周敦颐和王船山在历史上相距七百个年头,魏然屹立,遥遥相望。他们包揽了宋明道学的始终,一个是其开山祖,一个是其总结和终结者,他们在湖湘文化的历史上也是光辉万丈。这句话是这篇告示文中最关键、重要的一句话,它明确地指认了周敦颐和王船山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这一观点得到当代学术界的公认。 “其遗书五百卷,历二百余年而始出,嗟既远而弥芳。”王氏守遗经书屋《船山遗书》刊刻于1842年,金陵本《船山遗书》刊刻于1866年,它们距船山诞辰的1619年是二百余年,而距其逝世的1692年则只有一百余年。也可以是越陈越香了。
“咸以谓两庑之祀,当在宋五子之列,而至今不获祀于其乡。”两庑,此处特指文庙大成殿东西两侧的房子,为先贤从祀之处。宋五子指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张载,他们都在历史上先后为朝廷批准从祀于文庙。这句话是说,人们都认为,在文庙的祭祀中,王船山可以挤身于北宋五子之列,可是至今连乡祀都没有享受到。
“如嵩焘之薄德,何敢仰希夫子而为之表章!意庶以乡贤之遗业,佑启后进,辟吾楚之榛荒。”此处的“夫子”指船山。这句话是说,我郭嵩焘德薄能鲜,不敢仰望船山先生并为之表彰。我不过是希冀以船山这位乡贤遗留的业绩,佑助启发后人,使湖南这块荒辟之地得到开发。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郭嵩焘的这篇《船山先生祠安位告示文》虽然其直接目的是要“安”船山的“神位”,但更重要的是安了船山在中国思想史的“地位”。
郭嵩焘还在有关船山祠等的的文章中,对船山学术思想作了简要的概述。他在《船山祠碑记》中说:
其学一出于刚严,闳深肃括,纪纲秩然,尤心契横渠张子之书。治《易》与《礼》,发明先圣微旨,多诸儒所不逮。于《四子书》研析尤精,盖先生生平穷极佛老之蕴,知其与吾道所以异同,于陆王学术之辨,尤致严焉。其所得于圣贤之精,一皆其践履体验之余,自然而忾于人心。至其辨析名物,研求训诂,于国朝诸儒所谓朴学者,皆有以导其源,而固先生之绪余也。
所谓“其学一出于刚严,闳深肃括,纪纲秩然,尤心契横渠张子之书”,是说船山学术根底纯正,究理深入,条理清晰,尤其是对张载的《正蒙》一书理解特别深邃。这句话与《船山祠祭文》中所说的“惟先生根柢六经,渊源五子。养气希踪于孟氏,正蒙极诣于横渠”的意思是一致的。
“治《易》与《礼》,发明先圣微旨,多诸儒所不逮”,是说明船山在治经方面的成就。在《船山祠祭文》中,郭氏对“诸儒所不逮”有更明确的说明:“于《易》、《礼》尤极精求,视陈、项更标新旨。”陈指陈澔(1260—1341),字可大。南康路都昌县(今江西都昌)人,宋末元初著名理学家、教育家,朱熹四传弟子。他最有影响的著作是《礼记集说》,乃明清两代学校、书院,私塾的“御定”课本,科考取士的必读之书。项指项安世(1129—1208),字平父(一作平甫),其先括苍(今浙江丽水)人,后家江陵(今属湖北)。官至户部员外郎、湖广总领。所著《周易玩辞》一书在宋末元初颇为盛行。此书宗法程颐《易传》,而又折中诸家,断以己意,适足以补《程氏易传》尽略象数之失,一时俊彦如陈振孙、徐之祥、马端临、虞集之辈皆盛相推挹,为之作序刊刻。郭嵩焘认为,船山对《周易》和《礼记》的研究上,比陈澔和项安世的新意更多。
“于四子书研析尤精,盖先生生平穷极佛老之蕴,知其与吾道所以异同,于陆王学术之辨,尤致严焉”。这是说明船山一遵孔孟正统,反对佛老和陆王的虚玄之学。在《湘阴县图志》中,郭氏说船山“辨正陆王得失,精于陆氏陇其。”陆陇其(1630—1692),字稼书,浙江平湖人,学者称其为当湖先生。是清代初期尊崇朱熹理学、力辟陆王心学的重要思想代表。他痛切地指出明代的覆灭皆因于阳明心学的兴盛流行,以及程朱理学的沉沦衰微,断然地认为今之为学当尊崇程朱理学,力黜阳明心学。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是非明而学术一、人心正而风俗淳。郭氏认为,船山对陆王的辨析比陆陇其更加精密。
“至其辨析名物,研求训诂,于国朝诸儒所谓朴学者,皆有以导其源,而固先生之绪余也。”这段话是说,船山在考据训诂方面也取得了巨大成就,并且开清代考据学(朴学)之先河,但这些不过是他学术成就的次要部分。
二
光绪二年(1876),也就是在城南书院修建船山祠六年之后,时郭嵩焘在朝廷署礼部左侍郞,向皇帝上了一道《请以王夫之从祀文庙疏》。这道奏疏是按照咸丰十年大学士军机大臣遵旨定议:“从祀文庙,以阐明圣学、传授道统为断。”所以郭氏的奏疏就是以这个调子叙述船山的学术成就:
我朝经学昌明,远胜前代,而暗然自修,精深博大,罕有能及衡阳王夫之者。夫之为明举人,笃守程朱,任道甚勇。值明季之乱,隐居著书。康熙时,学臣潘耒进呈其书,曰《周易稗疏》,曰《书经稗疏》,曰《书经引义》,曰《诗经稗疏》,曰《春秋稗疏》,曰《春秋家说》,皆采入四库全书。《国史·儒林列传》称其神契张载《正蒙》之说,演为《思问录》内外二篇,所著经说,言必征实,义必切理,持论明通,确有据依。亦可想见其学之深邃。而其他经史论说数十种,未经采取甚多。其尤精者《周易内传》、《读四书大全》,实能窥见圣贤之用心而发明其精蕴,足补朱子之义所未备。生平践履笃实,造次必依礼法,发强刚毅,大节懔然。张献忠据衡州,闻夫之积学高行,索之甚急,踪迹得其父为质。夫之引刀毁割肢体几遍,舁往易父。献忠见其创甚,释之,父子皆得脱。更莅吴三桂之乱,避地深山,流离转徙,读书讲道,未尝暂辍,卒能洁身自全。艰贞之节,纯实之操,一由其读书养气之功,涵养体验,深造自得,动合经权。尤于陆王学术之辨,析之至精,防之至严,卓然一出于正,惟以扶世翼教为心。
奏疏中将船山几种经典稗疏及《书经引义》(《尚书引义》)、《春秋家说》被收入四库存全书,并引述四库全书对船山经学著作的评价“言必征实,义必切理”,还特别强调,“其尤精者《周易内传》、《读四书大全》,实能窥见圣贤之用心而发明其精蕴,足补朱子之义所未备”,从而具体地说明了船山“阐明圣学”的巨大成就。奏疏还突出地强调船山的“大节”,既不应张献忠之召,又不为吴三桂写劝进表。而其神契张载《正蒙》之说,于陆王学术之辨,析之至精,防之至严,则是说明他扶世翼教之诚,传授道统之忠。
郭嵩焘这个奏疏上于光绪二年八月二十日,这年底他奉命任出使英国大臣。此时王夫之从祀案还在礼部讨论。次年,远在伦敦的郭嵩焘风闻礼部议驳,在不满之余,更担心此次驳斥将会给以后的请祀造成障碍,因为根据各部的惯例,“凡奉旨议驳之件,部臣辄援引原案,以为格于成例,不复查议”,所以又于当年十二月九日从伦敦发出一封奏折,重申王夫之应予从祀的各种理由,并请将王夫之从祀一案“饬部存案”,暂时搁置,以待嗣后论定。在第二封奏折中,郭嵩焘直斥徐桐对他个人的偏见是礼部议驳的根本原因:“署礼部左侍郎徐桐以臣出使西洋,为清议所不容,所请应从驳斥,昌言于众,远据曾国藩序文内‘醇驳互见’之言议驳。”所以郭氏在这篇奏疏中再一次申述了船山的学术成就
窃见王夫之发明程朱遗旨,博大精深,元、明诸儒,罕能及者。尤究心张子之书,以礼为宗,以复性为本,以刚毅正大为学,穷极讨论,本末完备,体用兼赅。原任刑部侍郎臣吴廷栋称:“于性理所得最深,推王夫之为朱子以后一人。”
吴廷栋(1793—1873),字彦甫,号竹如,安徽霍山人。道光五年拔贡,授刑部七品小京官,洊迁郎中。廷栋少好宋儒之学,入官益植节厉行,蹇蹇自靖。郭嵩焘引用吴廷栋的话,是为了表明,不只是湖南人说船山好,外省人也说他好。
所谓“曾国藩序文”,是指曾氏的《王船山遗书序》。序中有句话:“虽其著述大繁,醇驳互见,然固可谓博文约礼,命世独立之君子已。”正是针对“醇驳互见”一语,郭氏这篇奏疏中指出:
臣尝与曾国藩辩论王夫之遗书“醇驳”之旨,曾国藩亦以吴廷栋之言为允当。而谓“醇驳互见”,在考证之疏密,无关学术之精微,即朱子经说,国朝诸儒纠正其失,有证之经传,确然见朱子之疏略,而固无损其大端。宋儒蔡沈《书传》,元儒陈浩《礼记集说》,所释只一经,一皆循用孔安国、郑康成旧说,稍加疏暢,列在学宫,并得从祀。王夫之经说繁多,疏证推衍,或间有缺误,而如《周易内传》、《读四书大局(全)》,实能羽翼经传,示人以规矩准绳之极则,方之诸儒,尤为纯实。
郭嵩焘上折请饬部存案以后,又“分咨礼部及湖督及南抚(湖南巡抚)”,动用一切资源来挽回。但是无济于事,上谕认为“从祀典礼关系綦重,部臣议准议驳,自有公论。郭嵩焘因廷臣议驳明儒王夫之从祀文庙,辄以私意揣测,疑为故意驳斥,并请饬部存案,语多失当,殊属非是。原折着掷还。”这次被驳,背后主其事者是署礼部左侍郎徐桐。掷还的日期,《德宗实录》系于“光绪四年二月壬寅”,但是《翁同龢日记》在同年八月初五日有如下记载:“是日巳刻,内阁会议张伯行、王夫之从祀庙廷,张清恪准,王船山驳,皆礼部主稿。”日记中还有小字注解:“驳稿略摭《四库提要存目》中语,断为不足羽翼圣经,继承运统”,同日的《王文韶日记》也证明了这一点。这说明,郭嵩焘第二次上疏的确是“以私意揣测,疑为故意驳斥”,所以“语多失当”。尽管如此,但却反映郭嵩焘对船山充满了感情。所以光绪六年(1880)四月十三日当他听友人说宋儒广辅已经在一年前经浙江巡抚梅小岩之奏,入祀文庙时,他说,广辅之言“皆浮浅无甚精意。一经浙抚奏请,部臣无肯议驳者。因忆及光绪二年署礼部左侍郎,奏请王船山先生从祀两庑,而请饬南抚查开其事迹并其遗书。寓书乡人,属具呈另行题奏。而为李辅堂(桓)所持,事寝不行。徐桐〔荫〕轩方任礼部尚书,立意议驳。船山之学,胜于庆源(广辅)奚止百倍,即王蘷石(文韶,时任湖南巡抚)之声光,亦百倍胜于梅小岩。吾楚人不务表章先达,竟无一能主其事者。闻浙抚此奏,为之垂涕竟日。”
既然朝廷不批准船山从祀文庙,郭氏在家乡闲居时便创立思贤讲舍,专祀船山先生。讲舍在光绪七年(1881)九月初一日船山生日这一天开讲。郭嵩焘在这一天的讲会上说:“禁烟公社与思贤讲舍相附丽。初定章程岁凡四集,以屈子(原)、周子(敦颐)及船山先生及曾文正公生日,略志景仰先贤之意。今岁开立思贤讲舍,专祀船山先生,即日开馆,及九月朔日祭期,为春秋两次会讲,以后当遂为定例。”郭氏还将从衡阳船山祠摹拓而来的船山像悬挂在思贤讲舍,并写了《船山先生像赞》:
濂溪浑然,其道莫窥,幸于先生,望见端厓。
约礼明性,达变持危,阐明正学,是曰先知。
二百余年,星日昭垂,私心之契,旷世之师。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郭嵩焘等人的努力,在郭氏有生之年,船山虽未能从祀文庙,但却入祀了乡贤祠。据王闿运在《船山书院记》中说,1885年,彭玉麟向朝廷报告已将衡阳船山书院迁至东洲,请求指示衡州分巡道将书院应办事宜议定举行,并且请求将南城的书院“旧址改作船山祠宇,饰有司春秋致祭”时,当年七月十八日,湖南巡抚准礼部咨开五月二十四日本部覆奏:“王夫之既入乡贤,例由地方官春秋致祭,改建祠宇,未免重复。至所建船山书院,应如所奏,责成衡州分巡道主持。”这一批复可以确证船山已经入祀乡贤祠。
三
郭嵩焘对船山在中国学术史上地位的深刻认识,是与他对船山著述的深入学习和研究分不开的。限于篇幅,此处不拟详论。往下,我想介绍一下郭氏是如何“师船山之言以立身”的。郭嵩焘在同治九年(1870)10月的日记尝言:“玩圣人‘吾非斯人之徒与而与谁与’一言,有多少包涵,多少运量,使人褊急狭隘之心,至此全无所容。船山处乱世,几欲离人而立于独,气象又别。师船山之言以立身,体圣贤之心以应物,其庶几乎。” 写这段日记时,郭氏正以城南书院山长的身份,修建船山祠。联系前面介绍的他有关船山祠的文稿,可以看出,郭氏不仅认为船山的著作学术价值很高,而且还对人的身心修养有益。所以郭氏自觉地将船山思想运用到自已的生活和工作之中,以之作为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方法论指导。
其一,用船山思想观察人物。郭氏曾多次引用船山在《俟解》中说的一段话:“末俗有习气,无性气。其见为必然而必为,见为不可而不为,以婞婞然自任者,何一而果其自好自恶者哉?皆习闻习见而据之,气遂为之使者也。习之中于气,如瘴之中人,中于所不及知。而其发也,血气皆为之懑涌。故气质之偏,可致曲也,嗜欲之动,可推以及人也;惟习气移人,为不可复施斤削。”在咸丰十一年(1861)四月十二日的日记中,他在引用了此段话之后说:“以此观天下之人才,考求士大夫之议论,其超出习气之外者,能几人哉。”这些话告诉我们,立身处世,不要为一时的所谓“士气”所左右,要有自已的主见。咸丰十一年三月十四日,郭氏日记记道:“船山先生云:‘气之泓(急也)也,其中消也,如老疾者之喘气,本不盛而出反促也。’明以来之所谓气节也,皆气之消也。非知道之君子,谁与辨之。”这段话与前面所说的意思大体上是相同的。
其二,用船山思想制驭夷狄。在同治元年(1862)四月间,郭嵩焘在日记中抄录了王船山《诗广传》中不少论述,其中有一条是:“善御夷者,知时而已矣。我戍未定,靡使归聘,守也。岂敢定居,一月三捷,战也。采薇之诗,迭言战守,而无成命,斯可以为御夷之上策矣。”这里讲的“成命”指既定的方案。就是说,对付夷狄没有固定的方案,一切都以时机为转移。两天之后,郭氏又在日记中记道:
沅浦(曾国荃)寄示冯敬亭(桂芬)《驭夷宜知夷情议》。敬亭所知者,今日之夷情也。其于理势相因之数,利害倚伏之原,古今立国自强之大略,则尚未之及也。三年前有知此义者,犹可控御夷人,使不致横决。今日只是将就而已。举世尽恍然于夷情之不能越也,而于事固已无济矣。
郭嵩焘是当时中国最了解洋务的人,朝廷大臣都以“精透洋务”来称赞他。而郭氏洋务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吸收王船山的哲学思想,反复强调要以理致胜:
天下事,一理而已。理得而后揣之情,揆之以势,乃以平天下之险阻而无难。汉、唐以来,控御夷狄之规模有得有失,而理、势、情三者必稍能辨其大概,然后可以制一时之胜而图数十年之安。南宋以后,议论胜而士大夫之气嚣,此道遂绝于天下数百年。天下大势之功效,亦略可睹矣。
船山在《诗广传》中说过:“顺逆者,理也,理所制者,道也;可否者,事也,事所成者,势也。以其顺成其可,以其逆成其否,理成势者也。循其可则顺,用其否则逆,势成理者也。故善取者之虑民,通乎理矣;其虑国,通乎势矣。”从前面郭嵩焘对《诗广传》的重视,我们不难理解他对船山理势观把握的纯熟。
其三,运用船山思想观察和处理各种事务。这突出地表现在对“几”的重视。
几这个概念在周敦颐和王船山的著作中用的比较多。郭嵩焘继承了他们的思想,十分重视几。他说:
尝论天下事只坐一‘几’字。非徒大政之行,大变之生,知几之君子所必争也,一事之成毁,一言之从违,与夫人心一日之向背,皆有几焉。几一滞而百端为之壅塞。周子屡言几,诚哉其知天人之变而妙理势之通者也。
郭氏认为,具体来说,知几有以下好处:首先,有助于增强人的预见性。其次,有助于个人进退出处,身心修养。最后,有助于增强人们处理问题的识力。
(作者为本馆馆员)
注释:
1、《郭嵩焘全集》第3册,岳麓书社2012年版,第1页。
2、5、18、《船山全书》第16册,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602、595、663页
3、4、15、21、23、《郭嵩焘诗文集》,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538、512—513、544、149、153页。
6、7、9、11、《郭嵩焘全集》第4册,岳麓书社2013年版,第798—799、837、836—837、838页。
8、《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278页。
10、《郭嵩焘日记》第3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7页。
12、段志强:《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从祀孔庙始末新考》,《史学月刊》 2011年第3期。
13、14、《郭嵩焘日记》第4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3、216页。
16、《湘绮楼诗文集·文》,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458页。
17、20、《郭嵩焘日记》第2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25、28页。
18、19、22、《郭嵩焘日记》第1册,第450、470、443页。
【最早全面评价王船山历史地位的郭嵩焘】王兴国2018年4期总114
2019-01-26 21:47:32 来源: 评论:0 点击:
郭嵩焘(1818-1891),湖南湘阴人,我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外交家。他一生十分推崇王船山,最早对船山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作出全面的评价。一据郭嵩焘自已的记载,他至少从1852年即34岁时起,就系统地
分享到:
相关热词搜索:
上一篇:【两次鸦片战争中的郭嵩焘】梁小进2018年4期总114
下一篇:【《郭嵩焘全集》集外著述闻见录】杨锡贵2018年4期总114
分享到:
频道总排行
频道本月排行
- 14【“沩痴寄庐”及新民学会人才群体】陈先枢 梁小进2021...
- 13【梁启超与湖南时务学堂】丁平一2015年4期总102
- 11【毛泽东长沙早期革命活动的三个“大本营”】朱习文2021...
- 7【辛亥革命后长沙知识分子对学习西方文化的探索】杨锡贵...
- 7【湘军名将席宝田述论(上)】刘泱泱2019年4期总118
- 7【湖南近代著名教育家曹典球述评】丁平一2020年4期总122
- 7【浅析杜甫湖南诗中的政治情怀】糜良玲2012年4期总90
- 7【毛泽东与船山学社】王兴国2021年2期总124
- 6【七十年中国湘菜研究史述略】尧育飞2021年1期总123
- 5【身在潇湘第一州—元代中越交往中的若干资料】汤军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