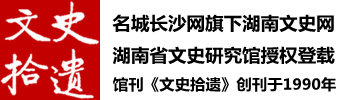一、颜昌峣的生平履历
颜昌峣(1868—1944),原名颜可铸,字仙岩,号息庵,湖南湘乡县神童镇(即今涟源市石狗乡人)。为了躲避元兵之难,颜昌峣的祖先千伯府君“自庐陵避地来湘,侨居珍涟山下高溪桥头湾”,[颜昌峣:《颜氏世典诸序》,《珍涟山馆文集》上卷,长沙:民国十九年振华印刷石印本,第4页。]死后葬在附近的太公山,湘乡颜氏从此定居于此,直至颜昌峣的父亲为第二十一世,“世有浅德,隐而弗曜”。[颜昌峣:《先考灵表》,《珍涟山馆文集》下卷,第23页。]颜昌峣的父亲颜泽首,字锦堂,“生性敦厚,仁友孝悌,型家厉俗,严恭有威”。他平生“嗜学能文,缕困童试入资为国子监生”,在洪杨之乱的时候曾经受曾国藩之令在当地办过团练,但是不愿出仕,之后一直在家以躬耕为生,“家居辟园林,号曰锄经园”。[颜昌峣:《先考灵表》,《珍涟山馆文集》下卷,第23页。]以后终生生活在珍涟山下,常常“锄经名园以教子孙”,[颜昌峣:《息庵新居记》,《珍涟山馆文集》下卷,第6页。]因此,颜昌峣说“昌峣总角甫出就传读四子书”[颜昌峣:《先考灵表》,《珍涟山馆文集》下卷,第24页。]。在父亲的教导下,颜昌峣有着良好的家学渊源。在“锄经家法”的熏陶下,颜昌峣幼年就读于乡村私塾,聪颖好学,勤奋过人,之后受廪贡生,在1890年,颜昌峣“补学官弟子于长沙”,[颜昌峣:《菊坡诗文集序》,《珍涟山馆文集》上卷,第16页。]1893年恩榜乡试。他在长沙岳麓书院求学时,跟着王先谦学习古文、经史, 1902年,清朝政府为挽救统治危机,推行“新政”,并对教育方面进行改革,经由各书院山长推荐,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颜昌峣遂以湘乡廪生的身份被王先谦推荐给湖广总督张之洞,在同年4月26日被选派至日本东京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班学习,成为湖南第一批官费留日生之一,[同行的湖南学生还有俞诰庆、龙纪官、仇毅、胡元倓、刘佐楫、陈润霖等11人,学习六个月,同年10月毕业。留学期间,每人发游学费400元。此外,当时在日本弘文学院学习的还有后来非常有名的鲁迅及作为旁听生的杨度等人。]“以期卒业归湘,藉端师范”。
应国内师范教育改革的需要,颜昌峣在日本六个月期间,详细记载课堂笔记,以作为湖南学界进行师范教育培养的范本或者教材。他与同学朱杞、龙纪官合作编译了《速成师范讲义丛录》,由东京湖南编译局印、上海广智书局发行,内容包括“教育与国家”、“教育学原理”、“小学校要则”、“中学校要则”、“师范学校要则”、“地理学”等方面,记载了在弘文学院日本老师所授课的讲义精要,“于教学之旨趣、立国之大原,盖有考焉”。还有法制和财政学两门,没有录入。这本《速成师范讲义丛录》被梁启超在日本横滨所办的《新民丛报》刊登介绍。留日期间,他在《寄弟畏庵书》里谈论到他在日本学习的感受,“今日吾中国之国势至此、屈辱至此、困难至此,亦是此弊皆因自三代以后,专以科名、辞章埋没人材,锢蔽性灵,全然不讲教育实践之故”,批评中国不讲教育实践、科举制度又误国误民。同当时很多年轻的留日中国学生一样,颜昌峣在这期间与黄兴、蔡锷等爱国志士有所交往,并经常阅读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还曾经把《新民丛报》寄回国内湘乡老家,使其弟颜畏庵、外甥谭戒甫都受到启发,曾在长沙加入黄兴、刘揆一等组织的华兴会,[颜珍、颜长珂:《先父颜昌峣先生事略》,《管子校释》,长沙:岳麓书社出版,1996年,第10页。]并受到民主革命的熏陶。
1902年10月,颜昌峣和同期毕业的湖南学生回国,回国后辗转于各个师范学校之间,从事教育工作,力图用教育振兴中国,他曾对人说:“日人胜吾,归功于小学,我今欲强我中华,教育岂可外哉?”[颜珍、颜长珂:《先父颜昌峣先生事略》,《管子校释》,第11页。]1903年正月,湖南巡抚俞廉三创办湖南师范馆,馆址设在城南书院,由颜昌峣担任历史教员。当时,学校选举新生的入学资格以举人、贡生优先,任命前国子监祭酒王先谦为馆长,其实多由学生颜昌峣代行其职责。[方克刚:《湖南中路师范史略》,《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编,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3页。]1904年11月,湖南全省师范学堂(由湖南师范馆改名)改为中路师范学堂,颜昌峣仍在中路师范学堂担任历史教员。1906年,颜昌峣被刚成立的南路优级师范学堂聘为历史兼伦理学教员,应当时学校之请,颜昌峣着手编写的《世界历史学》讲义的“上古”、“中古”卷仓促刊行。但是,颜氏不久被学校辞退。何镛、李大梁在《湖南优级师范学堂建设及其演变》一文中回忆说,颜昌峣在“讲论理学时,引严复云,谓孔子宗法伦理学说,不合于现代生活,思有以易之,而新吾民之耳目。又引李贽云,自汉武帝表章六经,尊崇孔子以来,天下无真是非,而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取便于帝王之专制,阻碍吾族之进化。同学闻之,更加异常兴奋。事闻于提学,大为不满。示意曾监督,令其引退。全体同学,悲愤交集,排队送别,师生递泪交流,痛恨言论不能自由。”[何镛、李大梁:《湖南优级师范学堂建设及其演变》,《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第90页。]大概是颜昌峣讲课时用了“新民”、“专制”、“进化”等激进、新鲜的言语,又对孔子的思想有所评判,导致学校监督不满。1908年湖南优级师范开办,8月份在长沙组织招生考试,9月份正式开学,颜昌峣作为当时的第一流名教授之一,被聘为历史老师。1912年,湖南优级师范学堂改名为湖南高等师范学校,迁入岳麓书院办学,颜昌峣继续任教于高师。
1910年,颜昌峣在任教于岳麓高等学堂之时,他的《世界历史学》讲义最终付梓。颜昌峣从1906年(始于南路师范学堂)至1910年任教期间,用了近四年时间将《世界历史学》讲义“上古史”卷、“中古史”卷、“近世史”卷和“最近世史”卷最终编写完毕。1908年至1910年,湖南法政学堂开办官、绅两校,颜昌峣曾被法政官校聘为伦理学教员,曾编有《湖南法政官校人伦道德讲义》。[此书现藏于湖南省图书馆。]
1911年9月19日,颜昌峣被补选为湖南咨议局的议员,“湘省咨议局因长沙府属议员粟戡时等六人辞职,特移由该府城戚太守召集初选,各当选人就府署投票补选,已于十七日上午十时开票……颜昌峣补湘乡十五票”。[《申报》(上海版),辛亥年七月二十七日,第13871号。]然而,不久武昌首、湖南反正,在长沙光复后,作为清朝统治机构的湖南咨议局也寿终正寝,政局更替、机构变换,议员们也纷纷去他处谋就。
辛亥革命后不久,湖南军政府任命颜昌峣来接办《长沙日报》,颜昌峣延聘其学生任凯南、黎锦熙、颜锡畲、朱让枬、李晋康等分别担任编辑、庶务等职,“尽虑谋改良,内容大易旧观,销路亦激增”,[李抱一:《长沙报纸史略》,《李抱一文史杂著》,长沙:湖南人民出版,2009年,第5页。]但他不久被辞退,改由同盟会的成员文斐接管,傅熊湘担任总编辑。一说是“旋因颜不是同盟会成员,有时拒绝发表同盟会的文稿,遂被撤换,改委文斐主持,以傅熊湘为总编辑”;[张平子:《从清末到北伐军入湘前的湖南报界》,《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编,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106页。]一说是“因为站在立宪派立场,拒登同盟会的文件”。[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026页。]不管这两说如何,大概侧面反映了湖南反正后初期革命党人与非革命党人权力上的争夺。随后,颜昌峣还曾与李抱一、贝元澂、黎锦熙、任凯南、朱矫、李嵩岳、唐吉俊等参与创立“湖南编译社”、“湖南公报社”、“湖南通讯社”等。
1914年,颜昌峣曾在省立一中担任习字老师,教授学生书法学习。[雷啸岑:《忧患余生之自述》,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17页。]1915年,他再度担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历史教员。[孙海林主编:《湖南第一师范名人谱(1903—1949)》,长沙:湖南第一师范学校,2003年,第19—20页。]在一师教学期间,也曾担任过毛泽东的老师,并与毛泽东等学生也常有往来。
1916年7月,谭延闿再次督湘,任命颜昌峣为《通俗教育报》(由《演说报》改名而成)的馆长。此前汤芗铭主湘时,《通俗教育报》倍受摧残,其主持人也被汤替换,并渐渐沦为袁世凯鼓吹帝制的工具。颜昌峣接办《通俗教育报》之后,使报纸有恢复了汤主湘之前的活跃精神,“亦足以张其绪”。1918年3月后,张敬尧取代谭延闿主湘,《通俗教育报》随之改由韦启俊接办,颜昌峣随即离开。[李抱一:《长沙报纸史略》,《李抱一文史杂著》,第14页。]从1918年至1920年张敬尧主政湖南期间,颜昌峣在衡阳担任湖南第三师范学校的校长。[屈子健:《衡阳五四运动的片断回忆》,《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编,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1979年,第40页。]这一时期的衡阳是继长沙之后全省学生运动最为活跃的地方,背后参杂着各个党派力量的推动、纷争,而第三师范正是其活动的重要阵地。1920年初,在湖南省学生联合会的领导下,驱张代表团前去衡阳进行活动,“衡阳学生积极投入了这一活动,特别是第三师范和女子职业学校给了我们大力的支援”。[丑伦杰:《驱张运动在衡阳》,《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第102页。]在1920年6月中旬,谭延闿和赵恒惕由衡阳进逼长沙,张敬尧仓皇逃走。湖南驱张胜利后,颜昌峣也离开第三师范,回到了长沙。1927年,北伐战争时期,武汉成立武昌中山大学,颜昌峣被聘为文学院教授,前去武昌。第二年,又被当时的湖南大学校长任凯南聘为湖南大学教授,从那以后直到1937年抗战之前,颜昌峣一直担任湖南大学教授。他的《中国最近百年史》正是1928年在湖南大学授课之际编写的讲义,先由湖南大学刊印,后在1929年由上海太平洋书店出版。
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后,长沙很快随之受到战乱牵连,颜昌峣携家眷回到湘乡故里的珍涟山馆避乱。他晚年在故里自筑书室,名曰“校管楼”;自书楹联 “翻书风入座,开门月满楼”,每天读书、习字,并间至蓝田(今涟源市)授课于国立师范学院。这期间,他曾指导过其子女及颜家龙的书法和经史学习。1944年去世,享年七十六岁。[颜珍、颜长珂:《先父颜昌峣先生事略》,《管子校释》,第12页。]
二、颜昌峣的著作及学问
颜昌峣虽然接办过报纸,从事过新闻事业,还当过《湖南学报》的主要撰稿人,[《湖南学报》于1903年4月创刊于长沙,主要汇集归国留日学生所开师范馆的讲义,并附有其他论著。主要撰稿人有皮锡瑞、单启鹏、许兆魁、颜可铸(颜昌峣)等。内容涉及学务统编、经学讲义、伦理讲义、理化讲义、数学讲义、地理学辑要、东文辑要和附录十编等。]但总结其一生,主要以教书为谋生之道,辗转于湖南各中学、高等学校。据易洛祖回忆,他在长郡中学念书时,颜昌峣也曾做过长郡中学的老师。[颜家龙:《回忆叔祖父颜昌峣》,《得德楼文稿》,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10页。]
颜昌峣的学识通晓古今中外,在教书之时,他必定自编讲义,王先谦曾对他所编的经史讲义进行了高度评价:“古泽今情,东手西眼,树三古教育之主义,发四极愿学之思想”。[颜珍、颜长珂:《先父颜昌峣先生事略》,《管子校释》,第11页。]至今我们可以看到的讲义有《湖南法政官校人伦道德讲义》一卷(清光绪间刻本)、《伦理学史讲义》四卷(民国刻本)、《经学讲义》一卷(民国刻本)、《世界历史学》5卷(1912年许荣华堂木活字本)、《中国最近百年史》(1929年太平洋书店出版)。此外,他还有《珍涟山馆续集》六卷、《欧波诗草》二卷(清末民国)、《日本兴国史》、《新三字经》等著作未能得见。
颜昌峣一生酷爱《管子》研究。他曾说,“余尝爱管子之书多精言,而可施之于治道,其文辞粲然可观”,[颜昌峣:《管子校释·自序》。]曾题所居书室为“校管楼”。但是,他深感古来关于《管子》的记述或研究漏误较多,于是潜心学术,集前人之大成,穷毕生心血于民国十三年(1924年)完成更详备的学术著作《管子校释》,由郭大痴作序。他在《自序》里说,“非敢自谓于管氏有所发明,要亦集近代近代校订之大成,于读者不无裨助”。事实上,颜昌峣正是这本《管子校释》奠定了其研究《管子》的学术地位,成为《管子》学的集大成者,在《管子》研究领域占得一席之地,以至于后世很多从事《管子》研究的学人都绕不过他的这本著作。
颜昌峣工古文,传承了自曾国藩、王先谦以来所创立的桐城古文学派的湖南一脉,文章造诣极高。他自己曾说,“尝以文见赏于王葵园、吴挚甫、阎季蓉诸先生”。[颜昌峣:《桐城派古文之建立及其流别》,《船山学报》,第四编,第二卷第三期,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998页。]他的古文代表著作是《珍涟山馆文集》。起初,在1919年夏,颜昌峣的《珍涟山馆文辑》两卷已经刊行,由谭戒甫先生做跋,《跋》中概括并且简单评价了中内容:“于上卷言学言史,既服其学之雄而见之远;于下卷言地方自治,复叹其才之大而虑之深。末乃附以经义数首,于举国人人所唾弃之余,独浩然不争一日之得失,而暴露于海吞潮沸之前。是其所思者定、所持者坚,其平生卓尔不群、特立独行之概,有以使之然也”。《文辑》只一册,包括两卷,谭戒甫先生既概述了《文辑》的主要内容,又赞扬了颜昌峣先生在那个经学衰颓的年代仍然坚持治经的“卓尔不群、特立独行”精神。随后,他的《文辑》中有关“序文”、“札记”、“书信”、“碑铭”、“寿序”等文章都收入民国十九年(1930年)振华印刷局出版的《珍涟山馆文集》里,分类更加明确,包括“序”、“论说”、“书”、“赠序”、“杂记”、“传状”、“墓表碑志”、“寿文”、“赞颂”、“哀祭”、“辞赋”、“诗歌”等十二类。在此《文集》出版前,罗庶丹、李肖聃等人给予高度评价:“此于桐城派之外另树一帜,其湘乡派也欤!”[颜珍、颜长珂:《先父颜昌峣先生事略》,《管子校释》,第11页。]高度评价了颜昌峣的古文造诣足以另立一派,在湖湘古文水平倒退之际,颜昌峣的文章恰恰能够“为湘中传绝业”。[罗庶丹:《和息庵自述原韵即题珍涟集后》,《珍涟山馆文集》下卷,第65页。]李肖聃先生也在《珍涟山馆文集·序》中说“季蓉叹其文为近代所未有,挚甫则谓文章之衰久矣,息庵殆将起而振之也”,都对他的古文水平做了高度的评价。其中,《珍涟山馆文集》里收集的《颜氏世典诸序》在当时评价颇高,石门阎镇珩说:“当与王临川《许氏世谱》并传”,桐城吴汝纶评价道:“谱牒书雅洁如此,近代所未有也”。[颜昌峣:《颜氏世典各序》,《珍涟山馆文集》上卷,第11页。]
颜昌峣所做文章的典型特点是主于经世,这大概与经学大师王先谦的教导及近百年来湖南文人主张“经世致用”的风气是分不开的。他自己曾说:“窃以为通经在乎致用、立言期补于世,文苟无关乎治道人心而掉弄风姿、藻饰字句,特末技耳。”[颜昌峣:《桐城派古文之建立及其流别》《船山学报》,第四编,第二卷第三期,第1998页。]他认为“文章当以学识为主”,不能做无病呻吟。因此,他的教学讲义必定亲自编订,针砭时弊,才能方便发挥自己的观点和心得;他的学术著作《管子校释》也是希望能够“施之于治道”;他的散文、地方自治的文章更是观点议论随处体现。李肖聃先生说“其学主于经世,深诋文士华靡之习,不欲以曼词自显,非关政理尤不苟作,博大之气充于篇章,远以承韩欧大家之风,近以绍曾刘诸公之业,经纬于事变,发皇乎神思”,[李肖聃:《珍涟山馆文集·序》,或见《李肖聃集》,长沙:岳麓书社,2008年,第151页]确是事实。
概而言之,颜昌峣一生的治学经历,可以用罗庶丹的话概括:“公系出子渊,好学绍其祖。少日东京游,归为教师主。历史通中西,华文串今古。一册珍涟集,上与史公伍。旁採百家言,叙成齐仲父。”[罗庶丹:《罗焌庶丹先生题赠二首》,《管子校释•跋》。]
颜昌峣除擅长经、文、史外,还工书法。他的隶书、楷书、行书、草书都有很高的成就,而尤精于行、草书,字体劲拔雄强,是当时有名的书法大家。他留下的有行书手卷《曾文正公忮求诗》、《曾文正公格言数则》等作为字范传之后嗣,还有在长沙岳麓山所书的《岳王碑》、《禹君墓碑》(即禹之谟)等,至今还矗立于山上。有书法集《珍涟山馆法书》两卷,收集有颜昌峣自己的临帖之作和他为子女学习临帖而书写的范本。著名书法家颜家龙也曾说,“我之嗜好书画,源于先生之影响”。[颜家龙:《回忆叔祖父颜昌峣》,《得德楼文稿》,第110页。]
三、颜昌峣的社会活动
近百年来的湖南文人秉承着“匡时济世、经世致用”的风气,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以更好地实现人生追求,颜昌峣沿袭经学大师王先谦的教诲,一生坚持“通经致用”。
颜昌峣一生积极参与政事。1910年,颜昌峣在《世界历史学》的《后序》中说:“今也,益数十万争荣尚利之人以困农工商,而儒者所为仁民爱物之学,尤复荡然无入于其耳。吾惧数十年后,外之不足与白人争雄,而内之转以滋黄民之困,将不止学行邯郸者之葡伏而归也。然则将如何?曰必也废科甲、兴工厂、奖实业、励农商、汰冗员、制气禄,使民自竞于生计,而无慕乎势位,其可耳。”这体现他编写此讲义的目的不仅仅在于教学知识的传播,更希望透过中西古今历史的对比,针砭国内时弊,探究中国黄种民族落后于白种民族的根本原因,并寻找切实可行的实业救国对策。1911年辛亥革命风行全国之际,湖南很多地方很快也随之反正,只有辰、沅、永、靖地区的官员朱益濬仍旧负隅顽抗,欲据湘西独立。因颜昌峣与朱益濬私交较好,湖南都督谭延闿请他写给朱益濬一封《致朱益濬书》的信札,内容分析当前形势,“今者人心思汉,清运既终,十八行省之中,所未下者,仅京师、河南、荆襄数郡之地耳,而直隶已有保定之变,山东已有德州之告,河南卫辉、彰德亦皆同举义旗”,分心当时人心所向,希望朱益濬能够顺应时势。进一步又从历史事实和匡复汉业方面来分析,“今先生之于清朝可方刘基、宋濂之于元耳,非王猛、许衡之比也,正可翻然改图,匡复汉业,小之则湖南一省学务之司、民政之寄,非先生其谁属?大之则中华光复之戎勋、民国鼎新之元老,垂名万世,杨烈千秋,亦在先生一反掌间耳,先生又何疑焉”[颜昌峣:《致朱益濬书》,《珍涟山馆文集》上卷,第36页。]来劝说朱益濬义举合情合理。1917年,颜昌峣发表的“丁巳阅大公报天籁君论有感而作”的《谷贱论》上、下篇,详细阐述了我国以农立国的历史和状况,并由此深入探讨谷贱、灾荒带来的流民问题将给社会社会的稳定造成后患,“我国向来以农立国,统一之代重农抑商勿论已”、“物贵谷贱,农夫终弃,所获不足回复,借贷之资本则出入筹划而决弃耒耜奔走都市,成为流荡”、“民穷国乱,政府岂能独存一旦?凶悍相乘,天下大扰”。因此,建议政府“重农贵粟,丰敛歉散,杜绝遏抑,宏奖输出,补助耕敛,整理泉布,使游荡之民转缘南亩,庶几盗贼息、危机弭矣”。[颜昌峣:《谷贱论》上下篇,《珍涟山馆文集》上卷,第23—24页。]1920年左右,谭延闿和赵恒惕在湖南大力推行地方自治的运动,湖南各界都有关于地方自治的热烈讨论,颜昌峣也时常发表关于地方自治的政见及其评论。例如,他直接上书的《发起地方自治期成会启》、《上参政院论地方自治书》、《上黎大总统段国务总理论地方自治书》等文章,表达他对地方自治建设的建议。[详见颜昌峣:《珍涟山馆文辑》下卷,民国八年铅印本,现藏于湖南省图书馆。]此外,他还在《大公报》上发表一系列关于湖南自治的文章,例如,《讨论城镇乡自治》、《我之自治意见》、《市乡自治制意见书》[分别详见《大公报》(长沙版)1920年10月8日、10月9日、10月12日、10月13日,1921年9月1日,1922年6月28日、6月29日、7月1日、7月3日、7月4日。]等。当时,毛泽东也在湖南推行湖南省的自治运动,颜昌峣在《湖南自治的商榷》一文中对毛泽东的自治运动也有所评论:“一如毛君所说的,暂时只要努力造邦,不要说联,以德美两国为例。先有了邦,自然会相联合。我不懂毛君痛恨中国的总组,却喜欢这个分立的邦,又将德美两国截然不同的国情,来混作一例看待了。据我看,德美的联邦,完全是个遗传的政体,正与我国春秋时代的诸侯相同,普鲁士国王威廉第一,战胜奥地利,夺得盟主权,而自执联邦国的牛耳,与春秋时代晋楚争霸相同。难道我们小百姓就不要天子,不要霸王,却都去要那些世袭的贵族鲁卫之政和唐朝的节度使小国么?想必毛君不是这样说的哩!若说美利坚,却不是联邦国,名叫美利坚众合国。合众不是合邦,也不是合州。国字表示其地域,合众表示人民自治的国体,美利坚的各州。是中级自治区,那各州也不过是各市乡自治区的联合体罢了。把个完全人民自治的国家引来为例,原是可以,但我的主张,起码的要求,自要筹办湖南的下级地方自治,不管什么国、不管什么省、什么县,先把下级地方自治弄好了再说”。[颜昌峣:《湖南自治的商榷》,《大公报》(长沙),第1610号,1920年10月7日。]显然表达了对毛泽东自治主张的不同看法。1933年,颜昌峣对邵元冲的地方自治论述发表了《读邵元冲论地方自治与建国基础》一文,“今者民国改建廿余年,吾民犹是出粟米麻丝以事其上之民族,有义务而无权利 (此权利指预算、决算、表决、选举等权而言)。国难临前则惊,相号召标语宣传,若揭竿而求亡,子吾民熟视若无睹焉。甚者窃笑其侧,安所得全国一致之民族同心御侮、毁家纾难也哉?乃者吾湘筹办自治,乃不注意于乡镇而专注中级之区治,其划乡也亦等于区,甚且等于古子男之国。吾以为此乃发展绅权之机会,且将变绅权为官权。数年之后,官愈多而民愈少,土豪劣绅专制而良民尽驱为寇盗。国欲不亡,不可得已。以此言自治,则自乱之道,速亡之兆也”。[颜昌峣:《读邵元冲论地方自治与建国基础》,《船山学报》第四编,第二卷第四期,湖南师范大学出版,2009年,第2289页。]颜昌峣认为,民国虽已成立二十来年,但中国民情没有改变,不注重乡镇之治而只是单一的划乡、划区,容易造成绅权的扩张。1927年,许克祥发动马日政变后,颜昌峣对于此事,作《马日靖乱功德碑》,简略叙述了马日政变的过程,对此事加以歌颂,“马日政变,声震八荒,许君之名与日月光。自有马日,湘人始苏,父得有子,妻得有夫,老得扶杖,幼得嬉娱,动有职业,止有室庐,衣食乐育”[颜昌峣:《马日靖乱纪功碑》,《珍涟山馆文集》下卷,第38页。]等。对于马日事变,他称作“靖乱”,显然是以国民党当局为正统,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认为许克祥是在维持当时的社会治安和秩序的稳定。
在教书和治学之余,颜昌峣曾积极参与船山学社的组织和宣讲工作。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船山学社社友上书《呈湖南省政府改组湖南船山学社学社文(二十年八月十二日)》,来倡议对船山学社进行改组。“呈请鉴核准予令行教育厅严令改组船山学社、整理讲学机关以崇先贤而重文化事。”[参见:《呈湖南省政府改组湖南船山学社学社文(二十年八月十二日)》,《船山学报》第二编,第二卷第一期,第1646页;或易孟醇点校:《赵启霖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23页。]公举社长为赵启霖,副社长为陶思曾,颜昌峣为船山学社研究部主任,在之后经过选举,颜昌峣一直作为船山学社的董事之一,直至抗战爆发。1932年至1937年的船山学社在赵启霖社长的带领下和湖南军政主席何健的支持下,活动频繁、成果颇多。在此期间,学社经常收到来自各地、各界订购《船山学报》的费用和赞扬船山学社“推崇圣教”、“卫道救国”之类的书信。颜昌峣作为其中的积极分子,与社员定期开会讨论、组织船山学社的一系列工作,包括每届重新选举新董事、每年发展吸收一批新社员、购买书籍、举办季课考试、出版《船山学报》等活动。作为学社重要的成员之一,颜昌峣经常应邀主讲,内容主要涉及经史、序说、传文等,基本发表在《船山学报》的里。可以说,他积极参与船山学社的学术讲演和日常活动,为三十年代船山学社的改组、运作、学术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湖南近代名流颜昌峣生平钩沉】王亚婷2014年1期总95
2015-01-03 21:47:19 来源: 评论:0 点击:
一、颜昌峣的生平履历颜昌峣(1868—1944),原名颜可铸,字仙岩,号息庵,湖南湘乡县神童镇(即今涟源市石狗乡人)。为了躲避元兵之难,颜昌峣的祖先千伯府君自庐陵避地来湘,侨居珍涟山下高溪桥头湾,[颜昌峣:
分享到:
相关热词搜索:湖南 名流 生平 颜昌峣
上一篇:【白石山麓拾芥尘——纪念齐白石诞生150周年】许康2014年1期总95
下一篇:【赵一曼丈夫陈达邦的传奇人生】黄禹康2014年1期总95
分享到:
频道总排行
频道本月排行
- 34【张一尊艺术年表——纪念张一尊先生诞辰120周年】贺建秋...
- 32【肝胆相照 荣辱与共——记戴岳与肖劲光合作交往情谊】...
- 14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专刊【抗战时期的邓为仁将军】史明20...
- 13【花明楼贺家圫杨氏人物琐记】陶子林2019年1期总115
- 9【吴溉之轶闻】许康2016年4期总106
- 9【邓仁堃名镌“金墉堤”】黄三畅2015年1期总99
- 7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专刊【阙汉骞在腾冲战役】周九宜2015...
- 7【王东原主政湖南述略】李长林 黎天宇2016年3期总105
- 7【齐白石和他的学生(四则)】聂鑫森2017年3期总109
- 6【梁焕奎——湘商之魂】谭静江2018年1期总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