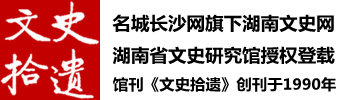三、长沙旧巢:工作地
1951年,史学大家陈寅恪寄诗一首给好友瞿兑之,在“独乐园花入梦秋”一句下,他自注“丁巳秋(1917年)客长沙,寄寿星街雅礼学会,即文慎公旧第也”。此处的“文慎公”,是指晚清军机大臣瞿鸿禨(1850-1918)。文慎公旧宅,即其位于长沙潮宗街和寿星街交界的瞿鸿禨宅第。瞿鸿禨(1850-1918),字子玖,号止庵。湖南善化(今长沙)人。同治十年进士,点翰林,授编修。官至内阁学士、军机大臣。光绪三十三年因与奕劻有矛盾,被袁世凯用计参劾,又忤慈禧旨意,被劾开缺回籍。宣统三年(1911年)迁居上海,1918年逝。


图5-6 瞿鸿禨故宅今貌(拍摄于2021年6月27日)
在晚清政局中,瞿鸿禨在腐败的官场颇能廉洁奉公,故颇受到当时的尊重。他在与庆亲王奕劻和袁世凯的斗争中下台。罢官之后的瞿鸿禨回到自己在长沙潮宗街的住宅(图5-6)。据《止庵年谱》:
光绪三十三年,丁末,瞿鸿禨58岁。5月20日,自京乘京汉车转轮船抵长沙,旋于朝宗街住宅之东营家庙,为本房奉祀之所。复于宅后余地筑楼三重以望岳麓,颜曰超览,种花树其旁。[1]
可知在开缺回省后,瞿鸿禨给其住宅加盖了一栋三重楼,名之为“超览楼”。而自从此楼建成后,就成为本地文人雅士、名流要人聚会、宴请的场所[2]。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超览楼、瞿鸿禨故宅和雅礼会的关系。根据前所引文,可知瞿鸿禨故宅位于潮宗街与寿星街交界的一带,“超览楼”是瞿开缺回省后所建。而当时在长沙的雅礼会(Yale in China)则暂时租用瞿住宅,办雅礼医院。也只有弄清了这个关系,才能完全理解寅恪先生那一句简短却不简单的“寄寿星街雅礼学会,即文慎公旧第也”的回忆。湘雅的美国方创始人胡美(1876-1957)对瞿鸿禨故居有如下回忆:
1914年秋天,在医学院开学之前就在这些城市举行了入学考试。应试的人非常多,九月,我们开办了一个二十人的班,在潮宗街租了一栋过去一个老参议长的宽大公馆开学。医院病房和教学用的实验室都安排在这栋公馆里的一部分房屋内。房子的后面和雷公庙的围墙搭界,那里是一个围墙围着的美丽的花园。月洞门和格子窗户朝水塘开着,假石山点缀其中。珍奇的树木和芍药花、山茶花花坛,把这个由高墙与外界隔绝的花园装点成一个神仙境界。[3]
这里必须指出翻译上的一个小错误。胡美回忆中所谓的“老参议长”,英文用的是“old grand councilor”。grand councilor是英文中对清朝“军机大臣”的固定称谓,因此其实应该是“年迈的军机大臣”之英译,而这位军机大臣即瞿鸿禨。胡美的这个回忆正好可为陈寅恪之回忆作一注脚。
瞿鸿禨被目为是晚清清流的代表人物。而清流与浊流的问题,是晚清重要议题,也是陈寅恪晚年念兹在兹而所不能忘的。这就是为什么在其晚年的残稿《寒柳堂记梦未定稿》中,专门设立篇章进行讨论,并列出如下人员名单:
简要言之,自同治至光绪末年,京官以恭亲王奕䜣李鸿藻陈宝箴张佩纶等,外官以沈葆桢张之洞等为清流。京官以醇亲王奕譞孙毓汶等,外官以李鸿章张树声等为浊流。至光绪迄清之亡,京官以瞿鸿禨张之洞等,外官以陶模岑春煊为清流。京官以庆亲王奕劻袁世凯徐世昌等,外官以周馥杨士骧等为浊流。[4]
在这个清流浊流的名单中,最耐人寻味的除开陈宝箴、张之洞外[5],笔者认为就是瞿鸿禨了,而陈寅恪恰恰就曾在其故宅寄居过一段[6]。
也正是因为有这些草蛇灰线,在陈文集中是否有和瞿鸿禨有关的文章,成为笔者一直思考的问题。而思考的前提是,以陈寅恪之心思细腻,对于他所希望纪念的事情,总会有某种方式的纪念,颇类他儿时拍照时为自己做的握桃花之“暗号”。早年翻遍《陈寅恪集》,笔者未能找到线索。直到最近笔者意识到,瞿鸿禨当时的地位、面临的处境,与晚唐重臣李德裕(787-850)颇有类似之处,而在陈文集中,恰恰就有一篇题为《李德裕贬死年月及归葬传说考辨》的专文,文章写于1935年,这篇文章很可能就和瞿鸿禨有关。之所以有这个推测,也和笔者读到瞿兑之记载的一条王闿运轶事有关,根据瞿氏的记录:
先生(即王闿运)所选八代诗及唐诗均有自批之本。批唐诗多作谐语。余记其批李德裕“内官传诏问戎机”一首云,“军机大臣自命不凡”。[7]
李德裕这首诗名《长安秋夜》,全文是“内宫传诏问戎机,载笔金銮夜始归。万户千门皆寂寞,月中清露点朝衣”。这首诗能看出李德裕当时与皇帝的亲密关系(“内宫传诏问戎机”),同时也可看出李德裕对自己加班(“载笔金銮夜始归”)结果还是非常满意的(万户千门皆寂寞,月中清露点朝衣)。而王闿运“军机大臣自命不凡”的评价又尤其让人回味,因为武宗朝的李德裕属于宰相,而非军机大臣。军机大臣是清代官衔,而瞿鸿禨的恰恰就是军机大臣,因此瞿兑之在回忆王闿运批注唐诗时,才特别记得这一条。当然,陈寅恪写《李德裕贬死年月及归葬传说考辨》一文,主要是实践宋贤年谱长编编排之研究方法,但这还不足以说明,在众多人物中,为何陈寅恪要选择李德裕贬死年月及归葬传说的问题。笔者推测,一方面陈是想用宋贤之方法与钱大昕等人对话,同时,也因其自身经历而受到晚清人物瞿鸿禨的启发,寻找类似的晚唐人物。如果此说成立,大概可以找到陈先生在此文中留下的一线索,比如他在此文特别对李德裕的归葬问题进行讨论,而如果翻看他在瞿鸿禨故宅居住的那一年的报纸和相关史料,就会发现湖南省政府当时处理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归葬”问题[8]。
李德裕与瞿鸿禨相关,还有另外一个间接的证据,即在陈寅恪撰写《李德裕贬死年月及归葬传说考辨》的同一年,他还写了一首《吴氏园海棠》的诗:“此生遗恨塞乾坤,照眼西园更断魂。蜀道移根销绛颊,吴妆留眄伴黄昏。寻春只博来迟悔,望海难温往梦痕。欲折繁枝倍惆怅,天涯心赏几人存”。陈氏自己给此诗加注言:“凡花以海名者,皆从海外来,如海棠之类是也”。关于这首诗同陈父陈三立的海棠诗之间的互文关系,以及陈寅恪自己之后四首海棠诗的含义,胡晓明教授已经做了非常出色的笺注,本文不复赘述[9]。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的张雨教授特别指出,此诗“与其说是作者为自身或时局而感叹,不如说是在为李德裕一生而感叹”,并拈出李德裕《平泉草木记》。“平泉庄”乃李德裕别业,在洛阳外三十里。其《平泉草木记》中提及所种“木之奇者”,有“天台之金松、琪树,嵇山之海棠、榧桧”,由此可知“海棠”对李德裕有特殊意义[10]。在张雨一文的基础上,笔者想进一步指出,其实陈寅恪曾寄居的瞿鸿禨故居也以有两株高大的海棠树而著名。著名的湖南画家齐白石就曾有一幅《超览楼禊集图》(局部,见图7)[11]。他在此画的题跋中写道:
前壬子春,湘绮师居长沙,予客谭五家。一日,湘绮师笺曰:明日约文人二三借瞿超览宴饮,不妨翩然而来。明日饮后,瞿相国与湘绮师引诸客看海棠,且索予画禊集图。予因事还家乡,未及报命。后二十七年,兑之公子晤予于古燕京,出示相国及湘绮师览超楼禊集诗,委予补此图予复题三绝句。[12]
齐氏还自题诗三首,其二有句“一日楼头文酒宴,海棠开上第三层。”齐自注为“相国自谓海棠树高花盛,长沙无二”;其三有句云“清门公子最风流”[13]。从齐白石的绘画和诗文,可见当时瞿鸿禨故宅的海棠花也颇让人流连,所谓“树高花盛,长沙无二”,引得王闿运等名流前来观赏。而第三首诗的“清门公子”自然指在1938年请求齐白石补画《超览楼禊集图》的瞿兑之(1894-1973)了。使用“清门公子”一词也表明身处晚清民国的齐白石非常清楚瞿鸿禨的“清流”身份。有了这些背景,应给陈寅恪1935年所作的李德裕文及《吴氏园海棠》之诗带来更为丰富的内涵。

图7 《超览楼禊集图》局部图
1917年客居于长沙瞿鸿禨故宅的陈寅恪是有机会看到其花园里两株海棠树的。而陈家也有种植海棠以寄托的传统[14],来到瞿鸿禨住宅看到海棠,一定令陈寅恪有不同的感慨。陈寅恪之所以在1917年客居长沙,是因为从1916年10月到1917年9月,他就一直在长沙工作。据《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略云:
七月,谭延闿任湖南省长兼督军,延聘先生至湘,任职湖南交涉使署。[15]
陈来长沙的具体职务是湖南省交涉使署交涉股长,这一年他27岁。其办公地点就是陈祖父和父亲曾经的工作地——湖南巡抚署。这个地方对陈寅恪来说是非常熟悉的。卞僧慧在《年谱长编》中回忆,“谭延闿为散原老人旧识,是年阳历八月谭任湖南省长兼督军,故先生任事”[16]。卞先生的这个判断是不错的。根据新出的《谭延闿日记》,可知陈父陈三立的名字在1916年谭日记中出现次数颇为频繁。据日记,是年9月24日谭曾接到陈三立的信,而12月23日陈寅恪的名字首次出现在该年的日记中,“晚饭,张润农来,胡兆鹏来,程颂云来,左霖苍来,张继良来,陈寅恪,伯严子也”[17]。虽然无法看到陈三立给谭延闿信件的内容,但从时间上看,这封信很可能涉及为陈寅恪求职事。陈寅恪先生来长沙工作的具体时间,囿于材料所限,已不可确知。据当时陈寅恪日本宏文书院的同学、同在湖南省署工作的林伯渠的日记,他的名字出现在1916年10月25日:
午前九时,上公署。……晚,赴何仲韩召饮于枣(园),同座陶叔惠、范秉钧、刘树焘、宾楷南、熊知白、陈子辉、朱后烈、陈寅恪。[18]
何仲韩,为当时湖南省署内务科长何国琦,本次饭局其为主要召集人。熊知白,是公务署教育科长熊崇煦;范秉钧,为政务厅长范治焕,林伯渠为任省公署秘书兼总务科长。吃饭的地点枣园位于府后街的顺星桥,离湖南省署及又一村,仅一箭之遥。根据饭局的组局人员(内务科长何国琦)、时间(陈寅恪刚到任)及地点(离政府办公处不远)看,则此次饭局,主要为宴请新任政府各个署的相关负责人员、相互见面熟悉,则可知矣。从林伯渠这条日记推测,陈寅恪应该刚到长沙不久。谭政府各机关职员的人员名单出现在10月7日的《大公报》上。另外,赵灿鹏在阅读1916年10月17日北京《民苏报》时,发现第七版“文苑”栏目有陈寅恪《寄王郎》诗一首:“泪尽鰤鱼苦不辞,王朗天壤竟成痴。只今蓬堁无孤托,坐恼桃花感旧姿。轻重鸿毛曰一死,兴亡蚁穴此何时。苍茫我亦迷归路,西海听潮改鬓丝”[19]。可见在10月上中旬左右,陈寅恪或许还在北京。
虽不能确知陈何时抵达长沙,然排比已知材料之时间顺序,似可整理出如下时间线:1916年8月确定谭延闿任命湖南省长兼督军,9月24日陈三立给谭延闿写信涉及陈寅恪求职方面内容,10月6日,长沙《大公报》刊登出相关省政府公职人员名单,10月中下旬左右陈寅恪抵长沙任职,10月25日赴新组省政府公务人员饭局,12月23日首次出现在谭延闿此年日记中。
又据卞僧慧的回忆,约1935-1937年,陈寅恪在课堂上谈及档案重要性时说,“昔年在长沙,初任职交涉使署,终日翻阅档案,看交涉案例。涉外交涉,不仅须熟悉条约,且须知过去交涉案例,临时不致仓促应付,贻误事机”[20]。可见陈很早就因为工作之关系接触过第一手的档案资料。对于一位史学家来说,这种经历是难能可贵的,那种快乐估计非常类似德国著名史学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在档案馆翻看档案时的感受[21],与之不同的是,陈的工作更需要与实际挂钩,更加讲求时效性,要对条约、交涉案例烂熟于心,才能“临时不致仓促应付,贻误时机”。陈的这种工作经验即前文所提及的“历验世务”的经历[22]。加上1930年代,陈寅恪曾兼任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主任、故宫博物院理事、清代档案委员会委员等职,让他得以遍阅故宫满文老档。这些经历越来越让陈寅恪感受到近现代史史料过于繁多,无法遍读[23]。
两广总督劳崇光的后人、学者劳幹(1907-2003)曾在1939年在昆明有与陈先生朝夕晤对。他回忆道:他曾经和我谈到民国初年长沙的事,并说看到过和我父亲同曾祖的两位伯父,神情和我还多少有些像。可惜我生长在陕西,对于湖南的情形相当隔膜,因而接触的问题也就不多,不然这也是近代史上很有用的资料。[24]
劳幹虽祖籍长沙,亦是长沙的世家子弟,但因为生长在陕西,对民国初年的情况反倒不如陈先生熟悉,这是情有可原的。这里劳幹提及的“民国初年长沙的事”自然是指陈寅恪先生在长沙工作的这一段经历。可惜的是由于听者对这一段的情形并不熟悉,因此没有记录下陈寅恪难得的回忆。
陈寅恪任交涉股长时的具体工作,也可从《谭延闿日记》中略知一二。如:1917年3月6日条,“至省长办公厅办公毕,同秉均谈近事,乃往会食。归,见李纯生、张韵农及俄领事,陈寅恪来,为译人”[25]。可见陈任职期间曾发挥其外语特长。李纯生是湖南岳阳人李锜(1883-1968,字纯生),同盟会员,清末毕业于湖南时务学堂、求实书院,建国后曾任江苏省文史馆馆员。张韵农是湖南长沙人张孝怀(1882-1925,字韵农)。
1917年3月30日条,“至政厅办公,得陈寅恪书,言预算极有理”[26]。可见陈寅恪曾经就省政府或交涉署的预算对上级有所报告,且得到领导谭延闿的首肯。
陈寅恪早年在工作中这些表现,如重视文档、熟悉交涉案例、外语的纯熟以及重视经济工作,都体现在了他日后的史学研究当中,如他用丰富的外语知识对《蒙古源流》的研究、对佛经翻译的研究等等;在经济方面,他曾撰写《元白诗中俸料钱问题》等专文,而他的读书札记中对中古社会中的相关经济问题也非常关注[27]。
在长沙的这段工作经历,陈寅恪不但自己向瞿兑之有所坦露,而且还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影像资料,收在雅礼协会及湘雅会相关的校史书刊内。虽然照片并不罕见,但由于是集体照,陈寅恪坐在中间容易被人忽视,因此特意发表于此。

图8 1917年谭延闿、陈寅恪及雅礼协会人员留影
根据雅礼协会的档案记录,此照片(图8)拍摄于1917年,正是陈寅恪在长沙工作的时间。照片中前排右二的年轻人就是当时不到30岁的陈寅恪。坐在照片中间、身穿西服者便是当时的湖南都督谭延闿,谭延闿身边的两位军人,右边可能是赵恒惕,左边可能是张鹏翼,而张鹏翼身边、头戴瓜皮帽者则可能是曹典球。照片第二排右一是湘雅医院的美方创办者之一胡美(Edward Hume,1876-1957)医生。
1917年8月,陈寅恪与湖南省公署的林伯渠、熊崇煦一起辞去政府公职,得湖南省教育经费之余款游学美国。经过漫长的手续办理和准备之后,在1919年初,陈寅恪踏上北美的土地,进入世界顶级的哈佛大学学习[28]。
四、长沙旧巢:工作逃难地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7月29日,北平沦陷。在混乱中,陈寅恪离开清华园,乘人力三轮车回到北平城内西四牌楼姚家胡同四号父亲陈三立寓所,与家人团聚。8月8日,日军大批部队开进北平。北平沦陷后,国民政府命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在湖南长沙组建临时大学。清华校长梅贻琦(1889-1962)当年8月底到长沙着手筹备,9月初在长沙成立清华办事处。10月25日长沙临时大学开学,11月1日上课。学校紧急召集留在北平的教师赶往长沙上课,陈寅恪与家人也决定赶往长沙。根据陈寅恪妻子唐筼的“避寇拾零”回忆,1937年11月20日夜,陈寅恪一家从汉口乘坐粤汉车抵达长沙,“天仍在下雨,幸先发电,有人来接,得以住在亲戚家张宅,到时已在深夜了”[29]。
陈寅恪三个女儿回忆抵达长沙时的情形:“进站时已是夜晚,又逢细雨,幸得二嫂张梦庄的哥哥张景福兄嫂来接,在他们家暂住了几天”[30]。张梦庄(1909-1978),乃陈寅恪的哥哥陈衡恪(师曾)儿子陈封怀的妻子,清华外文系毕业,擅外语,谙绘画,且曾任清华篮球队队长(图9)[31]。

图9 张梦庄任清华篮球队队长时照片[32]
张梦庄的妈妈黄国厚(1883-1967),湖南长沙人,1905年与妹妹黄国巽同为湖南首批留日女学生,入日本东京青山实践女校师范学习,与秋瑾同学。回国后曾任衡粹女校校长等职[33]。根据《长沙市志》,黄国厚还是著名外交家郭嵩焘(1818-1891)的外孙女[34]。张梦庄的哥哥张景福(1901—?),清华大学毕业,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化学工程硕士,曾任湖南大学化工系主任,又名张光。
在张光家借住了几天后,陈家又搬到了著名语言学家黎锦熙(1890-1978)家的楼上。1937年12月1日,同样南下到长沙的吴宓拜访陈寅恪,其日记写道:“上午10:00,至黎宅,兼访陈寅恪夫妇(现寓黎宅楼上)”[35]。当时同样在长沙的陈之迈曾回忆道:
有一天我去探望我素所景仰的陈寅恪先生,地址是长沙麻园岭北大路王家巷四号。我到了之后才发现这是黎劭西先生的寓所,因此我又再度见到(黎)宪初,真可谓有缘。[36]
大王家巷距湘雅医院、雅礼中学(当时还在麻园岭)及周南中学(刘蜕故居)、湖南巡抚旧址及瞿鸿禨故宅等处都不算远,住在此地的陈寅恪尚有机会一访这些与他关系密切的地方。但抵达长沙的陈寅恪似乎忙于工作,他的三个女儿如是回忆道:父亲和他的兄弟姐妹都在长沙度过一段童年时光,所以他们之间一直用长沙话交流,把湖南看做第二故乡。这次重回故地,父亲没有闲心带领我们寻访旧居,却频繁外出,多是去清华大学长沙办事处、长沙临时大学,及由南京迁至长沙的中央研究院等处。当时临时大学因长沙圣经学院校舍不敷,将文学院设在南岳的圣经学院分校。临大文科师生1937年11月中旬相继抵达南岳,而12月15日校方即奉令迁出,于是师生们纷纷于1938年1月下旬再至长沙。但父亲一直留在长沙,曾在临时大学短期授课,并未去南岳。[37]
这一段回忆有两点非常重要,第一是陈寅恪常年与其兄弟姐妹用长沙话交流。第二是来到长沙的陈寅恪没有选择去南岳,而在临时大学短期授课。就陈寅恪而言,他对长沙有感情,能在此继续任教,不去南岳,是非常自然的选择。在这里简单涉及一下陈寅恪先生“恪”字发音的问题。近年杨逢彬先生曾撰文,认为陈寅恪“恪”(确音)的读音是长沙方言转换的结果。从陈家三个女儿的回忆看是非常可能的,因为陈家不但兄弟姐妹长期用长沙话交流,他们的亲戚中间也有长沙人[38]。
在长沙临时大学授课的陈寅恪当时开设两门课程,“魏晋南北朝史”和“隋唐史”。其中“隋唐史”一课是与郑天挺(1899-1981)共同担任。他当时的学生陈述(1911-1992)如是回忆:“寅恪先生每周来授课,让我先把用的书准备好,届时就拿到课堂去,历史组的同仁也跟着听。陈先生讲南方民族巴、蜀、蛮、獠、溪、俚、楚、越,就是在那里讲的。”
王永兴也是在长沙第一次听到陈先生的授课后,改变了其一生之志向。他在晚年回忆道: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日本侵略军占领华北,清华大学南迁长沙,我选修了陈寅恪先生讲授的魏晋南北朝史,这时候我第一次听他讲课。先生讲课有股巨大的力量,我的思想感情完全被吸引;并由此决定:我要学习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我一生要像先生那样为人治学。一个23岁的青年,坐在长沙圣经学院(临时备用)教堂中,苦思冥想,为自己找到了一生要走的道路。[39]
南下避难的陈寅恪在这之后喜欢把自己比为宋代诗人陈与义(1090-1139),如他在1939年《夜读简斋集潭州诸诗感赋》一诗中有句云“我行都在简斋诗,今古相望转多疑”。据胡文辉的《陈寅恪诗笺释》:北宋靖康元年(1126),京师开封为金兵攻陷,陈与义南下避乱经过湖南,故有所谓潭州诸诗;而此时民国政府首都南京亦早为日军攻陷,陈氏由滇赴港,亦径取湖南,旅程及心事都颇与八百年前的陈与义切合,故此处有“我行都在简斋诗”及“古今相望”之语[40]。
笔者还想补充陈寅恪自比陈与义,除开如胡文辉先生提及的旅程与心境相似之外,两人又皆为陈姓。另外,因为陈寅恪祖籍江西义宁,而陈与义则被认为是“江西诗派”的诗人之一,也存在某种暗合[41]。这次南迁对陈来说还有一个非常惨痛的损失。他离开北平之前,曾托友人将一批对他很紧要的教学用书寄送长沙。但他抵达长沙时,书尚未到。不久陈寅恪一家就离开长沙,书才陆续邮寄送达,只好寄送于亲戚家中。这一批书全部在1938年11月12日的“长沙大火”中付之一炬。陈在1939年7月6日写给傅斯年的信中特别提到:
弟读陈简斋诗,即用其语而和其诗,中有两句列于下,可明弟之情况也,“还家梦破恹恹病,去国魂消故故迟”。[42]
需要注意的是,陈寅恪发关于刘蜕文章的年份正是1939年[43],即长沙经历文夕大火(1938年11月13日)的后一年,而当时他的出生地、已是周南中学的刘蜕故居已基本被烧毁[44]。因此可以推测,关于刘蜕的问题,在陈寅恪心中已经思考多年,但正是“长沙大火”的刺激,才让陈寅恪在1939年发表此文。不但他的出生地,整个长沙城都陷入一片火海,使长沙这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化为一片废墟,当时30万居民无家可归。而就在长沙大火的前一年冬天,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1853-1937)先生就因憎恨日本侵略,以近八十五岁的高龄,绝食死于北京。如陈寅恪自己所言,长沙不但是他本人的“旧巢”,其实亦是其三世的梦痕所在,如其祖父就曾仿杜子美做《长沙秋兴八首》。张求会先生对此诗评价:
《长沙秋兴八首用杜韵》是陈氏七律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组,诗用少陵韵,沉郁深挚也直逼少陵。……正可看出陈宝箴以屈、贾自况,身系家国、心念兴亡的孤介情怀。[45]
在《长沙秋兴八首》中,陈宝箴还提及不少长沙的名所,表现了他对长沙各地的熟悉,如“岳麓有情还绕廓,湘源何处可乘槎?”“贾傅祠边吊夕晖,萧萧落叶晚风微”“定王台下路逶迤,秋草湖边万顷陂”诸句中,出现的“岳麓山”“贾傅祠”“定王台”等地,到今天都是长沙本地的名所。而陈三立则在长沙期间创作有大量诗文,对了解晚清长沙社会风貌有很高的研究价值。陈寅恪自己也在长沙大火前,再次与这座历史文化名城近距离接触。而随着长沙大火,这些他曾经留恋徘徊的故迹都付诸丙丁,只能在回忆中存在了。也难怪他在1939年会黯然神伤地写下“还家梦破恹恹病,去国魂消故故迟”。
注释:
[1] 见瞿鸿禨:《止庵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81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第424页。
[2] 关于瞿鸿禨“超览楼”在长沙本地的相关情况,笔者准备另外撰文介绍。
[3] 见胡美:《道一风同》第二十一章,长沙:岳麓书社,第143页。
[4] 见《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入《陈寅恪集·寒柳堂集》,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第191页。
[5] 张之洞之名在同治至光绪末年,及至光绪迄清之亡时间段内两次出现。而陈寅恪自己也曾说自己“议论在曾湘乡(曾国藩)、张南皮(张之洞)之间”。关于晚清的清流派,学界多有关注,如赵丽雅《晚清京师南城政治文化研究》(凤凰出版社,2011年)一书,以同光时期的清流派为中心,结合北京南城的社会环境,对晚清政治进行探讨,尤其是本书第二、三编,讨论尤为细腻。王维江对晚清的清流也做了出色的研究,见王氏:《“清流”研究》,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
[6] 陈寅恪本人也在其研究中使用“清流”这一概念。对中晚唐清流文化颇有研究的唐史专家陆扬教授就曾特别指出陈寅恪曾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里,用“清流”一词来描述中晚唐的精英群体。见陆扬:《唐代的清流文化:一个现象的概述》,收入其《清流文化与唐帝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14页。
[7] 见瞿兑之:“王闿运轶事”条,收入瞿氏《杶庐所闻录·养和室随笔》,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6页。
[8] 1916年10月31日,黄兴在上海逝世,终年43岁。11月8日,蔡锷病逝于日本。当时湖南省一个关心的问题就是两位革命烈士的归葬问题。1917年4月10日到11日,蔡锷国葬典礼在长沙岳麓山举行。4月13日到14日,黄兴国葬在长沙岳麓山举行。翻看1917年当月前后的长沙《大公报》,常有这方面的新闻和进展。而这一段时间陈寅恪恰好在长沙工作。另外,谭延闿的母亲也于1916年11月6日去世,谭将之葬长沙南门外雨花亭故宁福寺之原。。
[9] 见胡晓明《陈三立陈寅恪海棠诗笺证》,收入吴盛青、高嘉谦主编《抒情传统与维新时代》,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432-452页。另见胡文辉《陈寅恪诗笺释》中的相关注解。
[10]见张雨《史学大师陈寅恪与挂甲屯吴家花园的海棠》,收入北京联合大学三山五园研究院,北京市海淀区文化发展促进中心编;《旧园与故人》,北京: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2018年,第22页。
[11]此图目前藏北京故宫博物院,这幅画最引人注目的地方除开瞿鸿禨三层高的超览楼外,就是楼边两株高高的海棠树了。需要指出的是,齐白石赴王闿运超览楼宴饮的年份是1911年,他错记成了1912年,即壬子年,此事已为胡适的《齐白石年谱》指出。又1911年,长沙朝宗街边尚有城墙未拆,这也是超览楼需建三楼,以观湘江对岸的岳麓山,否则视野会被城墙阻挡。而齐白石的画则“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完全将离超览楼不远的城墙给忽略了。
[12] 见故宫博物院编:《翰墨华光:故宫博物院藏现代名家绘画》,北京:紫禁城出版社,第184页。
[13] 同注12。
[14] 见胡晓明:《陈三立陈寅恪海棠诗笺证》文,同注9。
[15] 卞僧慧:《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63页。
[16] 卞僧慧:《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63页。
[17] 谭延闿:《谭延闿日记》第四册,中华书局,2019年,第318页。
[18] 湖南省档案馆:《林伯渠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30页。
[19] 赵灿鹏:《陈寅恪佚诗一首》,见《读书》,2011年第2期,第17页。
[20]卞僧慧:《年谱长编》,第64页,他同注15。
[21] 见安东尼·格拉夫顿著、张弢和王春华译:《脚注趣史》第三章,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关于此书的书评见陆扬《把正文给我,别管脚注》,见《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9卷第5期,第96-103页。
[22] 如陈清华弟子陈守实回忆,陈寅恪特别重视内阁档案中,清初明清交涉档案以及海通以还的各国外教档案。见陈守实:《记梁启超、陈寅恪诸师事》,收入张杰、杨燕丽选编:《追忆陈寅恪》,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42页。
[23] 如杨联陞记录陈寅恪曾言“近代史不难在搜辑材料,事之确定者多,但难在得其全”,见杨联陞:《陈寅恪先生隋唐史第一讲笔记》,收入《陈寅恪集·讲义及杂稿》,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486页;王钟翰回忆陈曾言“至于近现代史,文献档册,汗牛充栋,虽皓首穷经,迄今无终了之一日,加以地下地面历史遗物,日有新发现,史料过于繁多,几无所措手足”,见王钟翰:《陈寅恪先生杂忆》。收入张杰、杨燕丽选编:《追忆陈寅恪》,第253页,他同注22。
[24] 见劳幹:《忆陈寅恪先生》,收入 张杰,杨燕丽选编:《追忆陈寅恪》,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95页。
[25] 谭延闿:《谭延闿日记》第五册,中华书局,2019年,第64页。
[26] 同注25,第88页。
[27] 见王永兴:《关于唐代财政札记疏证》,收入王氏:《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1998年,北京大学出版社第319-336页。
[28]陈寅恪经上海赴美入哈佛大学的官费来源,见卞僧慧《年谱长编》引1917年8月27日、29日、9月8日长沙《大公报》及刘少雄《陈寅恪纪念室陈列说明》的文字,第64-65页,他同注15。
[29] 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14页。
[30] 陈琉球、陈小彭、陈美延:《也同欢乐也同愁》,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第135页。
[31] 1926年第五期《辟才杂志》录有张梦庄写的《春水》词一首:“芳草天涯,纤茵沿净一流沙。何处春泉?微波泛碧净无暇,更窥见好花掩映,花外谁家。也拟泛轻舟,只恐载不动许多愁。清沦一曲,难涤我心头;只在我泪河里,隐隐飘飘流,南望野花瑟瑟;更花外晚钟一声声送,增我离忧”。1926年第五期,第88-89页。可见张是德、智、体、美非常全面的才女。
[32] 照片见1930年上海《图画时报》第657期第三张。
[33] 黄国厚与衡粹女校的关系,见黄曾甫:《衡粹女校与黄国厚》一文,收入《长沙文史资料》第五辑,1987年,第162-164页。
[34] 见长沙市地方志办公室编:《长沙市志》第16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62页。
[35] 《吴宓日记》第三册,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265页。
[36] 转引自蔡登山《名士风流》,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1月,第241页。
[37] 陈琉球、陈小彭、陈美延:《也同欢乐也同愁》,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第136页。
[38] 见杨逢彬:《杨树达之后的杨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41-243页。又李恭的《陇右方言发微》有“窃虫”条,言:《续博物志》:“人家有小虫,至微而响甚,寻之卒不可见,号窃虫”。陇右人以家有“窃虫”为吉兆,故里谚曰:“家有廓廓虫,一生不受窘。”“廓廓”者,“窃”之重言也。北音“窃”“怯”同读,“窃”之读“廓”,犹“怯”之读“克”也。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四云:“明天启间,客氏、魏忠贤用事,当时有‘茄花’‘委鬼’之谣,盖京都语‘客’如‘茄’也。《元史》‘怯烈氏’,或作‘克烈’。英宗国语谥曰‘格坚皇帝’,石刻有作‘怯坚’者(见《泰安府东岳庙圣旨碑》),盖亦读‘格’为‘客’,因与‘怯’相近也”。见《陇上学人文存·李恭卷》,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18页。可见“窃”转读为“廓”,或“怯”转读为“克”是其来有自的,与“恪”转读为“确”音有类似处。但具体到陈寅恪的“恪”字读音,应是长沙方言保持的古音使然。这也能解释1917年陈寅恪在拿到湖南省官费留学哈佛后,到哈佛使用的名字拼法为Tschen Yinkoh,这个Koh,即类似“廓”,用长沙话亦可读为“que”。目前由于湖南卫视而流行的长沙方言“那确实”就有“那koh实”和“那quo实”两种读音。王钟翰也曾回忆陈寅恪讲课,稍带长沙口音。见其《陈寅恪先生杂忆》,第250页,同注59。
[39] 王永兴:《八十述怀》,收入王氏:《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1998年,北京大学出版社,第460页。
[40] 见胡文辉:《陈寅恪诗笺释》上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36页。
[41] 有趣的是,在钱锺书的《宋诗选注》关于陈与义条目的介绍中,他就特别提出陈与义其实不算“江西诗派”的诗人,形成一个有趣的反差对比。见钱氏《宋史选注》,北京:三联书店,第213页。另外,陈、钱之间的差别,可见胡晓明《陈寅恪与钱锺书:一个隐含的诗学范式之争》,发表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第67-73页。
[42] 陈寅恪:《陈寅恪集·书信集》,三联书店,2009年9月2印,第56页。
[43] 据“陈寅恪先生论著编年目录”,收入蒋天枢:《编年事辑(增订本)》,第198页,他同注9。
[44] 周南校友肖志彻回忆:“1938年11月12日晚长沙大火,周南校舍,原有十九栋,烧毁十三栋,幸存六栋”。见肖氏文:《解放前的周南》,收入《长沙文史资料》,1986年第3辑,第81页。
[45] 见张求会:《陈寅恪家史》,北京:东方出版社,2019年,第2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