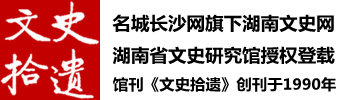清道光初年,有两只带有铭文的青铜鼎很偶然地从陕西省岐山县礼村出土,后世以其铭文的大小来命名,分别称大、小盂鼎。大盂鼎通高101.9厘米,口径77.8厘米,重达153.5千克,为西周时期的炊器。折沿,敛口,双耳立于口沿上。深腹中空,内壁有铭文,足上有扉棱。整体造型庄重大方,纹饰简洁质朴。小盂鼎则不幸毁于战乱,仅有拓片存世。
作为已知西周最大的青铜器,大盂鼎被列为“晚清四大宝”之一,并与毛公鼎、大克鼎一起被誉为“海内三宝”。
大盂鼎最有名的当属它的铭文,291字的铭文有证经补史的重要作用。内容主要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追溯文王受天命和武王灭商的功德,周康王强调自己要秉承先王美德;第二部分追溯盂早年学习的经历,盂深受周王恩泽,周王告诫盂要效仿他的祖父南公;第三部分是周王册命盂辅佐上司荣氏,要勤于奉公、恪尽职守。命盂继承祖父南公的官职,掌管军队、负责诉讼,辅佐周王治理天下。

西周大盂鼎
大盂鼎出土后几经流离,直到被晚清重臣左宗棠买下,作为礼物送给潘祖荫后才真正为世所知,成为无价之宝。
潘祖荫,字在钟,号伯寅,江苏吴县人(今苏州市)。他是大学士潘世恩之孙,内阁侍读潘曾绶之子。咸丰二年(1852)一甲三名进士,探花,授编修,长期当值南书房,陪侍咸丰皇帝,光绪间官至工部尚书。通经史,精楷法,藏金石甚富。
左宗棠买下来之后转送给潘祖荫的目的,是表达对他当年最先在咸丰皇帝面前举荐自己的感激之意。要知道,当时两人并不相识。
一
咸丰九年(1859)六月,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幕府的左宗棠,为政敌所忌,卷入了著名的“樊燮案”。
湖北恩施人樊燮本是湖南永州镇总兵,秩列二品武官。他恃有湖广总督官文为后台,即便在永州的官声很差,上年十一月初,仍被官文奏保代理湖南提督,这是一个统辖湖南全省绿营部队的从一品武职。
时任湖南巡抚骆秉章闻讯后,就以“违例乘舆、私役弁兵”为由上奏弹劾樊燮,在湖南防剿形势吃紧的大背景之下,十二月十一日,樊燮被就地免职,由骆秉章保奏湘军将领周宽世任永州镇总兵。既而,他又于咸丰九年二月二十八日再次上奏,指控樊燮贪污、挪用军饷。两周后,咸丰皇帝下旨逮问樊燮,由骆秉章查办。由于随后太平军石达开部围攻湖南宝庆,对樊燮的查办没有及时进行,因此樊燮安排了家人反诉骆秉章,语涉他的幕僚左宗棠。咸丰皇帝十分重视,认为事关镇将大员侵占军饷,又有官员挟嫌陷害、滥邀保举,故委派钦差大臣钱宝青专程查办。
因为很能干,当时幕僚左宗棠有“左都御史”之誉,而各种逸闻野史也流传他有“劣幕”之名,再因当众辱骂甚至掌掴樊燮才遭控告和查办。但无论是樊燮本人还是上司官文,都没有在相关文本中涉及这些细节,樊燮拉左宗棠下水的真实原因很可能是因为左宗棠作为巡抚的幕僚,不仅是两次弹劾奏稿的起草者,甚至还是“通知”者,意思是永州那边有人先向左师爷告密,左师爷再怂恿巡抚发起弹劾。
左宗棠觉得自己很委屈,八月二十五日,他在酒后给姻亲好友胡林翼写信,详谈了被樊燮控告一事,通篇不仅没有谈及掌掴和辱骂等情节,还在信末以“书中一字涉虚,必为鬼神所不佑”来证明自己绝非虚言。九月十四日,他又在信中再次确认,樊燮给自己安的罪名是“通知”,他让胡林翼放心,这完全是诬告,没有任何实据。
至于咸丰皇帝密令官文“左某如有不法情事,即行就地正法”之说,迄今也未发现确切的依据。根据清宫档案,自咸丰八年(1858)十一月初二日官文奏请樊燮署理湖南提督起,至咸丰十年(1860)四月二十日咸丰皇帝下旨让左宗棠以四品京堂襄办曾国藩军务止,在此期间,咸丰为樊燮案先后有过12次批示,其中咸丰九年九月十六日的一道“寄官文钱宝青旨”可视为密谕,内容是将骆秉章的奏折、樊燮的亲供一并封印以五百里的速度交给官文审阅,其中并没有如被查实就地正法的交代。至于不少逸闻野史中提及郭嵩焘出二千金说服潘祖荫与权臣肃顺出手相救之说,理论上也有可能,但肃顺所说的“如查实即就地正法”的廷寄(密谕)也未查到,故难以采信。
从《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及当时查办劣幕的类似案子来看,如果左宗棠的“通知”罪名坐实,巡抚骆秉章将被革职或降调,幕僚左宗棠则革职永不叙用,这样他虽无性命之虞,但势必会遭遇“社会性死亡”,从而失去施展抱负的一切机会。
二
基于这样的预判,曾国藩、胡林翼、郭嵩焘等人必然要设法为左宗棠斡旋脱困。左宗棠的同乡、曾国藩的挚友郭嵩焘正在南书房任职,当时他因僧格林沁的参劾倍感失意,不便直接出面,只好亲述原委,托请同事潘祖荫上奏举荐左宗棠,潘祖荫当仁不让地答应了。
他在咸丰十年闰三月二十三日上疏,先直接点名湖广总督官文“惑于浮言”,既而大力举荐左宗棠,指出湘军攻势得力是由于骆秉章调度有方,实则是左宗棠的运筹决胜,因此“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也。”
二十八日,潘祖荫跟郭嵩焘再面谈了一次后,于三十日推荐左宗棠“帮办湖南军务”。
四月初一日,咸丰看到潘祖荫的奏折后,专门就左宗棠的任用问题征询曾国藩的意见。十三日,曾国藩在答复中先夸赞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再给咸丰提出了几个任用选项,最后希望能明降谕旨,以便他能名正言顺地出来任事。以曾国藩的地位和影响力,他的意见具有一锤定音的效果。
胡林翼由于需要避嫌,就积极向官文、钱宝青做外围的沟通,再于五月初三日开单向咸丰推荐包括左宗棠、李元度、沈葆桢在内的十六位人材,内有左宗棠“名满天下,谤亦随之”之语。
应当说,众人帮助左宗棠都只持有着一个最朴素的看法:人材难得。而且适逢一个很重要的关头,那就是自咸丰四年春曾国藩率湘军东征以来,塔齐布、罗泽南、王錱、刘腾鸿等著名湘军将帅先后凋谢,李续宾及其所部五千余更是在安徽三河镇覆亡不久,湘军亟缺将才、帅才,众人为左宗棠转圜正适逢其时。
作为局外人的潘祖荫与湘系诸帅没有任何利益纠葛,咸丰不会疑心。他作为世家子随侍左右,也自信咸丰会采纳建言。
樊燮案,以左宗棠襄办两江总督曾国藩的军务、樊燮以流配五年发往军台效力、部分中下级官员被降调而结束。后来,樊燮的长子樊增裪中了举人,次子樊增祥,号樊山,光绪三年中进士,点翰林,官至江苏布政使,是著名的同光诗人之一,与湘军后裔交游频密。
左宗棠在众人的帮助下成功渡劫,藉此开启了新的非凡人生历程。他从四品京堂起步,十余年间东征西讨,官至陕甘总督,获封恪靖侯,可谓功成名就。林则徐当年的收复新疆重托,曾国藩、胡林翼的未竟事业,也都由他继续完成。
左宗棠事后在同治元年(1862)十月二十三日给儿子孝威的信中回顾了这个案子,说咸丰皇帝本来就因为多人推荐而留意到他,凡是见到从湖广觐见的官员,总会打听自己,实在是太抬举了,可谓“袭世奇遇”。此言确实不虚,最早向咸丰推荐左宗棠的是浙江会稽籍御史宗稷辰,他说湖南的左宗棠不求荣利,地位不高但是作用很大,如果能让他独挡一面,一定干得不比胡林翼差。
左宗棠也清楚,骆、曾、胡之保举,都是在咸丰做出决断之后,因为官文利用樊燮一案构陷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敢出面为他鸣冤,只有无一面之缘、无一字之交的潘祖荫敢点官文之名,敢说湖南不可一日无左某人。至于郭嵩焘,本来交情就深,早年还曾保举过他应孝廉方正科。这两位虽然帮着在皇帝面前推荐,却从来没有向他道及具体,想必也知道他不以私情而感之。所以他也觉得郭、潘二人的“留意正人”“见义之勇”,是非比寻常的。
左宗棠是道光十二年(1832)的湖南“搜遗”举人,在戎马倥偬之余,曾在陕西访得当年湖南乡试主考官徐法绩,至他的坟上拜谒以示缅怀,为他写了神道碑铭,为家书作序,并将其孙徐韦佩招入幕府。他显然没有忘记自己生命中的贵人,因此一直在留心一个感谢潘祖荫的机会。
三
大盂鼎出土后,首先被当地的富户宋金鉴收藏,他还针对铭文写了上千字的释文,不久,大盂鼎被岐山知县周赓盛所强夺,流入京城琉璃厂。
事有凑巧,宋金鉴于道光三十年(1850)考中进士,时来运转,旋即在琉璃厂邂逅了这件流失的宝贝,就用三千两银子买了回来。
宋金鉴善书画,爱收藏,中进士后,历官贵阳知府、刑部郎中、内阁中书等职。同治二年(1863)去世后,家道中落,子孙不得不再次变卖家藏,大盂鼎因此将再度流失,这个消息被左宗棠于同治十二年(1873)获知,他立即委托在西安督办西征粮台的属官袁保恒,于以银700两买下。
袁保恒是袁世凯的堂叔,交游广泛,官运亨通。他的父亲袁甲三,则是曾国藩、李文安(李鸿章之父)的进士同年。
左宗棠起意买下的目的只有一个:送给金石行家潘祖荫。潘氏为世宦之族,家境丰裕,潘祖荫酷爱收藏青铜器,藏品多达五百余件,其考据铜器、铭文的能力也闻名遐迩。
为慎重起见,左宗棠把大鼎及铭文的拓片送交潘祖荫审察,潘祖荫起先有些疑虑,倾向于此鼎有假。左宗棠无奈之下,拟转卖给关中书院,价钱由袁保恒酌定。
同治十二年(1873)十二月二十日,左宗棠致信潘祖荫,再次表达了诚心相赠之意。此时的潘祖荫颇为失意,由于户部行印遗失,他于三月十一日被部议革职留任,十一月又遭降二级留任。而此时左宗棠是西征军的总指挥,正位高权重,赠礼自然不是出于主动巴结之意。潘祖荫此时就改变了主意,愿意接受这个馈赠。
同治十三年(1874)五月二十三日,左宗棠复信,一方面表示敬佩潘祖荫的宠辱不惊,二方面表示时值多雨季节,为安全起见,只好安排袁保恒在秋后将大鼎车运至京。尽管后来秋季时仍有所耽搁,但大盂鼎终于顺利交接。
光绪十五年(1889),大克鼎在陕西宝鸡县渭水南岸出土,潘祖荫又以650两银子购得,可谓好事成双,高兴之余,他刻了一枚“天下三宝有其两”的印章以示纪念。
四
左宗棠后来与郭嵩焘结为姻亲,但是由于性格与政见的差异,两人于同治五年(1866)前后关系失和,以致多年不通音问。
光绪七年(1881)十一月,刚调任两江总督的左宗棠回湘省墓,与郭嵩焘在长沙相见,时间是十一月二十八日。左宗棠是否当面感谢过当年的相助,郭嵩焘并没有在日记中透露。此时左宗棠已经出将入相,与郭嵩焘的地位相差悬殊,他能登门相见,也是一个难得的姿态。
光绪八年(1882),郭嵩焘就湘阴县志定名之事致信左宗棠,左宗棠在回信时邀请郭嵩焘到南京做客,称“四十年同心至契也”。光绪九年(1883),又再次邀请郭嵩焘前往南京主持钟山书院,但郭嵩焘均未应约。
不难看出,郭嵩焘对左宗棠仍存芥蒂,尤其此前左宗棠在此前一信中还回忆起当年能从樊燮案脱身,是由于自己确实清白的缘故,这显然更不能让郭嵩焘释怀。
直到晚年,郭嵩焘才袒露了帮这个忙的初衷,那就是他担心左宗棠的去职将使得东南大局失去支撑。在左宗棠去世后,他先后写了挽诗和挽联,世所周知的挽联是:
平生自许武乡侯,比绩量公,拓地为多,扫荡廓清一万里;
交谊宁忘孤愤子,乘车戴笠,相逢如旧,契阔死生五十年。
对他的事功总体上是持正面评价。但据说他还有另一副联则是:世需才,才亦须世;公负我,我不负公。存于吴恭亨的《对联话》。
潘祖荫于光绪十六年(1890)去世后,因无子嗣,藏品由小了整整四十岁的弟弟潘祖年掌管,直隶总督端方闻讯后,以多种手段威逼出让两只大鼎,都被他断然拒绝,并在嫂子去世后不久,将大部分藏品秘密运回苏州,安置在南石子街的旧宅内,谨遵家规,绝不轻易示人,连至亲好友也不例外。
抗战期间,潘祖年去世。为确保国宝不落入敌手,他的两个孙子花了两天两夜,将大盂鼎、大克鼎藏于二进院一间久无人居住的堂屋地下,又将室内恢复原状,整个过程极度保密。当日寇侵占苏州的次日,就冲进潘家搜查,前后七次,始终未能发现潘家的宝藏。
1951年,潘祖荫的侄孙媳潘达于女士致函上海市政府,将家藏大盂鼎、大克鼎捐献给国家。1959年,大盂鼎转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今国家博物馆)。
大盂鼎不但铭刻了遥远的历史过往,还见证了一段空前绝后的感恩故事。很显然,它无与伦比的厚重和珍贵,只是后世之人的结论。当时左宗棠虽然是捡了一个大漏,并不真正了解它的内在价值,他甚至没有过手看一眼,显然不是以金钱来衡量,而是作为一份雅礼感谢知遇之恩,此举符合当时的世俗,同时也让这个珍贵文物不再颠沛流离,客观上来说使它得到了更好的保护。
(作者单位: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区域文化研究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