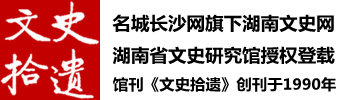一

城南书院船山祠
一个共识,即对船山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历史地位的认识完全一致。郭氏在《船山先生祠安位告文》中指出:“盖濂溪周子与吾夫子,相去七百载,屹立相望。揽道学之始终,亘湖湘而有光。”周子,指周敦颐,湖南道县人。周氏生于1017年,船山生于1619年,二者在时间上相去七百个年头。揽,指包揽、总揽。亘,空间和时间上延续不断。这句话是说,周敦颐和王船山在历史上相距七百个年头,魏然屹立,遥遥相望。他们包揽了宋明理学的开始与终结,一个以其著作为宋明理学奠定了理论基础,是其开山祖;一个则从理论上对宋明理学进行了总结,是其终结者,他们在湖湘文化的历史上也是光芒万丈的。这句话是这篇告文中最关键、最重要的一句话,它准确地评价了周敦颐和王船山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崇高地位。
郭嵩焘的这一观点与中国当代学术界对周敦颐和王船山的认识是完全契合的。例如,杨东莼在其1932年出版的《中国学术史讲话》中,就说周敦颐“为理学开山祖师”。侯外庐等主编的《宋明理学史》第二章的标题即为《理学开山周敦颐》;又说:“从形式看,王夫之哲学表现为对张载思想的继承和发扬,而从其实质看,则已越出了理学思想的樊篱。”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则称周敦颐为“道学的前驱”,王夫之为“后期道学的高峰”。张岱年在《宋元明清哲学史纲》中说:“朱熹、张栻等以二程的哲学观点解释周(敦颐)的学说,认为周、程一脉相承,于是周敦颐的太极被解释为理,而周敦颐就成为宋代理学的开山祖师了。”又说,“王船山自觉地继承了宋明理学的唯物主义传统……对宋明理学作了批判的总结。”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说,周敦颐“是宋明理学唯心主义的奠基人”。而王夫之“通过对宋、明以来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的清算批判,把唯物主义的元气论发展到更加完备”。萧萐父、李锦全主编之《中国哲学史》说周敦颐“是宋明道学的开创者”,而其第五编第四章的标题则为“总结和终结宋明道学的王夫之哲学”。这些学者的表述语言虽不尽相同,但在肯定周敦颐、王船山在宋明理学发展史上的地位的认识却是一致的,并且与郭嵩焘形成了共识。
就这一共识来说,今天我们公祭船山,就是要纪念他在中国思想史所做出的历史性贡献,推戴他崇高的学术地位。
二
一个超越,即当代在对船山政治思想的认识与评价上大大超越了郭嵩焘。郭氏《船山先生祠安位告文》说:“其立身大节,皭然不滓,与河汾、叠山以颉颃。”河汾,指隋末思想家王通(503—574),字公达,南朝大臣。他开创之河汾之学的主要贡献,是重新发现和发展了先秦儒家关于道高于君的道统思想,开启了唐代中叶形成到宋代充分发展了的新儒学。叠山,指谢枋得(1226—1289),字君直,号叠山,信州弋阳(今江西省上饶市弋阳县)人。南宋末年著名的爱国诗人,学通六经,淹贯百家。曾任六部侍郎,后带领义军在江东抗元,失败后隐居卖卜;被人强荐仕元,至元大都(北京)绝食而死。郭氏这句话是说,船山的的志节高尚,纯净洁白不受任何污染,与王通和谢枋得不相上下。这说明,郭嵩焘虽然还是从一般的道德意义上表彰船山的“立身大节”,但将他与谢枋得相比,则已经接触到船山的民族气节;因郭氏身为清代朝廷重臣,所以还不敢公开宣传船山的民族主义思想。
郭氏逝世不久,随着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兴起,船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得到了空前的彰扬,船山被近代中国许多先进人物推崇为精神领袖。谭嗣同继承了王船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在近代最早批评满洲贵族的民族压迫。他在《兴算学议》中曾指责清朝当局“满、汉之气,至今未化”。在《仁学》中则说:“彼起于游牧部落,直以中国为其牧场耳,苟见水草肥美,将尽驱其禽兽,横来呑噬。……《明季稗史》中之《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略》,不过略举一二事。当时既纵焚掠之军,又严薙发之令,所至屠杀虏掠,莫不如是。”章太炎是辛亥革命中宣传王船山的“夷夏之辨”思想最卖力者。除章太炎之外,章士钊、杨毓麟、陈天华、禹之谟、易白沙、杨度等人,均曾在辛亥革命前反复宣传过王船山的“夷夏之辨”以反清排满。例如,易白沙“早岁读郑思肖《心史》,及梨洲、船山、亭林、密之遗书,恍然种族之痛,亟思摈满”。毕永年“少读《王船山遗书》,隐然有兴汉灭满之志”。杨度在《湖南少年歌》中写道:“惟有船山一片心,哀号匍匐向空林。林中痛哭悲遗族,林外杀人闻血腥。”形象地刻画了船山反对异民族统治的心态。而洪门则将船山与黄宗羲、顾炎武、傅山等人尊崇为始祖。
辛亥革命胜利之后,“排满”的任务完成了,船山“夷夏之辨”的思想在国内成了明日黄花,但其中包含的“三义”说,却具有永恒的、普遍的价值:“有一人之正义,有一时之大义,有古今之通义。”“不以一时之君臣,废古今夷夏之通义。”即强调不要对某个地方割据者效忠,不要对一朝一代的君主效忠,而要对整个中华民族效忠。“夷”和“夏”这两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是随时代变化而变化的。只要人类社会还是按照地域划分为国家,人们在从事社会政治活动时,总会遇到这个“三义”的问题。所以杨昌济在船山学社成立时指出,船山一生卓绝之处,在于主张民族主义,以汉族之受制于外来民族为深耻极痛,此是船山之大节,吾辈所当知也。面对东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仍需发扬船山的民族主义思想。杨昌济的这个论断,把船山的狭隘民族主义转换成了现代爱国主义。而1983年7月2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联合发布《关于加强爱国主义宣传教育的意见》,将船山列为中国历史上13位爱国主义者之一。这实际上是由官方出面,将王船山确定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近代由于船山的《黄书》深刻影响而形成的一次尊黄运动。在《黄书·宰制》中,船山宣称:“中国财足自亿也,兵足自强也,智足自名也。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休养励精,士佻粟积,取威万方,濯秦愚,刷宋耻……足以固其族而无忧矣。”充分体现了他对中华民族复兴的高度自信。这个思潮兴起最鲜明的标志是《黄帝魂》一书的出版。此书实际上是由长沙人章士钊和黄藻合编,出版于1903年十二月六日。黄藻所写《黄帝魂例言》宣称:“是编所取,皆吾黄帝子孙痛极思呻之言,哀弦激楚,绝无忌避,而又言之井然,读之可泣可歌,可兴可发。意者黄帝在天之灵,实式凭之,故以《黄帝魂》名篇。”在此书所收的文章中,有的在论述中还引用了《黄书》的内容。在《黄帝魂》的影响下所形成的尊黄思潮,极大地提高了黄帝的历史地位,并对海内外中华民族同胞在“炎黄子孙”的伟大旗帜下的融合,起了不可估量的促进作用。
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船山学的重要进展之一,是王船山伟大爱国者地位的牢固确立,很多学者根据船山对近现代中国的深远影响,将其尊为中国近现代的精神领袖。将这认识推而广之,正是我们今天公祭船山的现实意义之所在。
三
一个不及,即当代学者对船山学术成就评价的标准,不及郭嵩焘的客观。郭氏《请以王夫之从祀文庙疏》说:“我朝经学昌明,远胜前代,而暗然自修,精深博大,罕有能及衡阳王夫之者。夫之为明举人,笃守程朱,任道甚勇。……所著经说,言必征实,义必切理,持论明通,确有据依。亦可想见其学之深邃。……其尤精者《周易内传》《读四书大全》,实能窥见圣贤之用心而发明其精蕴,足补朱子之义所未备。”这清楚地表明,郭嵩焘是以研治儒家原始经典为依据,衡量船山学术成就的。这一标准虽然是郭氏所处时代所决定的,但就是在今天,对一个研治儒学的学者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客观的衡量标准。郭氏在《船山先生祠安位告文》又说:“斟酌道要,讨论典礼,兼有汉、宋诸儒之长。”这是讲船山治经的基本立场和方法。“至于析理之渊微,论事之广大,千载一室,抵掌谈论,惟吾朱子庶几仿佛,而固不逮其精详。”朱子指朱熹。这句话是说,船山分析理论的渊博和精微,论述史事和时事的广阔和博大,犹如隐居一室,眼观千载,击掌而谈,这种水平只有朱熹差不多相似,但朱氏的析理不及船山之精确和详尽。这说明在郭嵩焘看来,船山在对儒家经典的理论分析上,是超过了朱熹的。
可是,自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学术界往往从意识形态出发,把王船山对待宋明理学的态度作为衡量其学术成就或地位的标准之一。因为长期以来,宋明理学被视为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评判一位宋明以来的思想家是否进步,就要看他对待宋明理学的态度。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船山研究中,将船山说成新兴市民阶级的观点,曾经比较流行。主张此说者将船山说成是启蒙思想家,说他在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上,表现出比较明显的反理学性质,因此是一位进步的思想家。这个观点提出之后,始终有人不赞同。他们认为船山是属于中小地主阶级思想家,他的哲学是以维护封建统治为最终目的,他没有脱出传统儒家哲学,特别是宋明理学的樊篱。在船山研究中,这两种观点长期尖锐对立,双方争论不休,谁也说服不了谁。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从意识形态出发,以对待宋明理学的态度作为衡量或划分学术派别的标准,往往带有很大的主观色彩。列宁说过:“因为社会现象极端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一种意见。”这种极端复杂性,既表现为研究对象身份的复杂性、著作内容的复杂性,还与研究主体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密切相关,乃至包括其对研究对象的感情好恶。所以,要做到学术观点上的统一是非常困难的。
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人们不再讨论船山是否反理学的问题,但是仍然十分纠结于船山对朱熹的态度,而对于这种态度的分析又不尽相同。例如,陈来先生在其《诠释与重建——王船山的哲学精神》中说:“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船山对朱子的态度前后有所变化。《读四书大全说》中对于朱子学的《四书》诠释,在大关节上予以肯定的同时,往往有苛评之处,盖与其当时心境有关,虽然主要针对于朱门后学者。但在船山后期,对朱子的态度渐就平实。在《礼记章句》和《四书训义》中对于朱子的推崇明显加重。”而邓辉先生则认为:“船山早年几未有直接针对朱子的批评,多批之于朱门后学,而晚年在《四书笺解》《周易内传发例》《张子正蒙注》《思问录》等重要作品中多有直接对朱子的批评。”这种分析的不同,反映了作者对船山理学立场看法的不同。按照陈来先生的意见,船山早年对朱子的批评,是一种正学内部的理论差异。而按照邓辉先生的意见,船山晚年对朱子的批评反映船山从朱熹移向张载,回归他所说的“正学”。两者的结论虽然不同,但是其立足点却还是以对朱熹的态度作为衡量船山学术倾向的根据。
如果我们采用郭嵩焘的标准,即以研治儒家原始经典的成就来衡量船山的学术水平,我们就不会再斤斤计较船山是否批评了朱熹,以及这种批评是多还是少。就以郭嵩焘盛赞、也是前面两位学者都提到的《读四书大全说》来说,其实船山不止是批评了朱熹的后学,而且也有很多直接批评朱熹本人之处。例如在《读四书大全说·中庸》中,船山直接批评朱熹之处就有十多处。船山不赞成朱熹将“中庸”的“庸”字解释为“平常”,他说:“自朱子以前,无有将此字作平常解者。……盖以庸为日用则可,而于日用之下加‘寻常’二字,则赘矣。”其评语中还有“断章取义”“自相矛盾”“捕风捉影”“窒碍”“微有病”“于义却疏”“无当大义”等文字,都是针对朱熹集注的。这些评语既不是苛责,也不是误解,而是摆事实、讲道理的分析。这种批评并不是出于某种学派对立的立场,而是为了准确把握儒家经典的真义,以“补朱子之义所未备”,也就是为了实践王船山自已所说的“六经责我开生面”。所谓“六经责我开生面”,就是要对儒家经典的原义做出超越前人的最准确的解释,可见郭嵩焘的标准与船山自已所说的治学宗旨也是完全一致的。只要我们认真研读船山有关经学的著作,就会发现他不仅从训诂、笺解方面,而且从训义、义理分析等方面对儒家经典进行了深入研究,从而开出了新的生面。
公祭船山也是对船山学的研究成果进行检阅,通过这种检阅找出差距,正是为了今后更好的进步。(作者系本馆馆员)
注释:
杨东莼:《中国学术史讲话》,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56页。
侯外庐等主编:《宋明理学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6页。
侯外庐等主编:《宋明理学史》下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09页。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1、258页。
张岱年:《求真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4—125、274页。
《船山思想的启蒙性质问题》,《船山学报》1984年第1期。
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第3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79页。
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第4册,第74页。
萧萐父、李锦全主编:《中国哲学史》下册,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228页。
《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增订本,第153页。
《谭嗣同全集》,第341—342页。
易培基:《亡弟白沙事状》,《易白沙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13页。
《杨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92—93页。
《船山全书》第10册,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535—536页。
《船山全书》第12册,岳麓书社1992年版,第509页。
《郭嵩焘全集》第4册,岳麓书社2013年版,第798—799页。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7卷,第326页。
陈来:《诠释与重建—王船山的哲学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
邓辉:《船山经典语录·前言》,岳麓书社2019年版,第004页。
《船山全书》第6册,岳麓书社1991年版,第4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