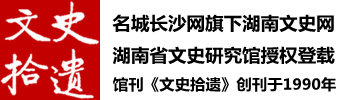湖南省历史上瘟疫频发,对社会的破坏和影响仅次于水旱自然灾害。据统计,宋代全国发生有明确地点的瘟疫48次,其中湖南4次,占十二分之一,与四川并列第五名,属多发地区。再如1939-1946年湖南省法定传染病患者发现及死亡人数占全国的百分比为:霍乱7.99、8.41;天花9.25、8.90;伤寒6.49、7.33;斑疹伤寒1.72、3.61;痢疾11.81、11.25;疟疾10.93、10.91;流行性脑脊髓膜炎3.16、1.82;鼠疫0.30、0.42;白喉2.45、1.95;猩红热1.17、2.0;回归热4.69、5.18。其中霍乱、天花、伤寒、痢疾、疟疾的患、死比例都名列各省前茅。
一、民国以前湖南瘟疫流行简况
湖南瘟疫流行最早见诸文献资料的为汉代。吕后七年(前181),赵佗“乃自尊号为南越武帝,发兵攻长沙边邑,败数县而去焉。高后遣将军隆虑侯晁往击之。会暑湿,士卒大疫,兵不能逾岭。” 据文献记载统计,从建武二十五年(49)至崇祯十六年(1643)长达1600年湖南发生过44次疫灾,平均约40年才发生一次。而年代较晩的明朝多达29次,几近这1600年的四分之三,平均约10年发生一次。清朝入关至鸦片战争前196年湖南有50年发生过疫灾,平均约4年发生一次,频率几近清朝以前年代的10倍。显然由于年代越久远资料散佚越严重,可能有许多次疫灾凐没在历史的滚滚红尘之中。由于明清时期编纂方志蔚然成风,对区域性疫灾均有所记载,而明清以前的国史不可能对一州一县的事务详加纪录,尤其是湖南这种远离政治文化中心甚至古代认为是蛮夷之区的省份,往往被历史的记忆忽略遗忘。当然,明清时期商品经济更为发达、社会交往增多而促使传染病流入也是原因之一。
清道光十二年(1832)湖南“岁饥大疫,死者无算”。武陵“道殣相望,殍毙者以上万计,民户多绝。”诗人阎其相以所见所闻作《悯疫吟》四首,其一《数若主》写一家八口死亡七口,买棺材时未点清亡者人数与棺材铺发生争执:“市城死人如乱麻,十室九空鬼大哗。三寸棺具价为昂, 况乃无钱直须赊。一室八口活者一,前负棺债算未毕。算误曰六贾曰七,呶呶不已贾人怒:“若去若室数若主”,仰天大哭不能语。”其二《益一人》写某家染疫死亡仅剩一老翁,只好请乞丐代为收殓。不料老翁半夜死去,代为收尸的乞丐也染病死亡:“一家短垣周荆棘,无何疾疫死纷纷。初犹买棺营新坟,后乃尸多構火焚。从染疫时未经旬,岿然病剩老翁存。谁与吊唁青蝇宾,薄暮乞儿乃至门。翁呼乞儿自为飱,汝毋我去我一身。我死汝葬刻汝恩,汝赀我赀谁与论。夜半翁死尸犹温,乞儿乃走告诸邻。迟明乞儿呻吟闻, 越日亦死尸横陈。一家已尽益一人,呜呼!一家已尽益一人!”
清季湖南爆发过三次严重的疫灾。第一次发生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号称“己酉大饥”的年份。据《湖南通志》记载:“全省大疫至明年四月乃止,死者无算。方疫之作也,死者或相枕籍,同善堂及各好善之家施棺以数万计。夜行不以烛者,多触横街死人,以致倾跌。盖其时饥者元气已尽,又加以疫,人人自分必死。尝见有扶杖提筐咨且于道,忽焉掷筐倒地而死者。有方解裤遗矢蹲而死者。有叩门呼乞,倏焉无声而死者。人命至此,天惨地愁矣。”读来使人毛骨悚然,不禁令人联想起14世纪席卷欧洲的那场黑死病的恐怖景象。
第二次发生在光绪十四年(1888):“疫气自郴、衡及于长沙、岳州,遂至苏、扬间。皆俄顷僵仆,士大夫家间亦传染”,贫苦民众更不问可知。这一则史料尽管不足30字,却为我们勾画了瘟疫的来龙去脉,提供了重要信息:其一,是年湖南瘟疫由郴州、衡阳肇始,实则可能来自广东。是年广东18府县发生鼠疫和霍乱,广州及与郴州毘连的乐昌均为疫区,而郴州正是湘粤商路的入口地,可以推断疫源地为广东,郴州为输入孔通。其二,瘟疫传播路线为广东—郴州—衡阳—长沙—岳阳,而这正是传统湘粤商路的走向,也是后来粤汉铁路的线路,瘟疫借助奔波活跃于湘粤之间的商人得以传播。其三,瘟疫的输出方向。瘟疫传播至岳阳,也许受洞庭湖和长江阻隔,没有继续北上,而是借助于另一条商路——水运向长江中下游的苏、扬地区蔓延。这次疫灾遍及湘南、湘中、湘北广大地区,仅湘潭就死亡数千人。湘西亦有少数县发生,如麻阳霍乱流行,“断炊绝户,阖门尽亡者多。”
第三次发生在光绪十九年(1893),主要在湘东、湘南地区流行。据湖南巡抚吴大澂奏报:“(醴陵县)本年入春以来天气亢旱,瘟疫流行,死亡相继。隔岁存储早已食尽,值此青黄不接之时,饥民无以糊口,至有掘取草根树皮煮食者。扶老携幼,流离道路,惨不忍言……茶陵州与醴陵相距不远,情形大略相同。该州属茶乡一隅,尤为困苦。”这场瘟疫旷日持久,一直延续到年底。吴大澂复奏:“茶陵之茶乡、西乡,瘟疫缠染数月之久,情形尤为可悯……不意衡州府属之安仁县,与茶陵毗连之处,疾疫流行,仍由茶陵一带转入安仁各乡。始患疟疾,继而转痢,日甚一日。合邑四十八村,其甚者一村死至数百人之多,医药俱穷,棺木亦无从措办。该绅民等以为数十年来从无此之奇灾……本年夏间雨多晴少,秋后淫霖伤稼,通计收成虽系四分有余,而成熟之日,或全家俱病,收获无人,禾芽渍腐,民不聊生,实非寻常偏灾可比。”
二、北洋政府时期湖南瘟疫流行简况
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湖南几乎年年都有瘟疫发生,比较严重的有1918-1920、1922-1924及1926等年份,尤以1919年和1920年为最。就地区而言,长沙发生瘟疫灾次数最多(11年次),其次为平江(9年次)、岳阳(8年次),沅陵(6年次)、常德(5年次)、衡阳(5年次),4年次有益阳、溆浦、新宁、桂阳、慈利,3年次有华容、湘潭、湘阴、会同、湘乡。长沙和这些地区发生瘟疫灾次数最多,究其原因主要有:
(1)长沙地区人口密度较大,人口越密集,发生疫灾的几率相对越大。作为湖南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交通中心的省会城市,一直以来人口流动性大,尤其是1904年开埠以后,长沙直接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商品倾销和原材料供应市场,一方面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吸引周边地区民众聚集长沙就业谋生。另一方面全国各地与长沙地区的人员往来更为频繁,商店旅馆林立,表明商品经济繁盛,人员交往频繁,但也往往把外地的传染病带入,在促进湖南近代化的同时也容易导致瘟疫的流行和传播。
(2)交通、邮政、商贸事业的逐步近代化。长沙是湖南的交通枢纽,粤汉铁路北可直达武汉,南抵韶关(1936年粤汉铁路才全线贯通),同时又是水运航线的重要港口,经湘江、洞庭湖可到达长江沿岸甚至沿海各城市,交通相对便利,客运货运繁忙。另外,湖南的邮政事业起步于1898年冬,长沙、岳州、常德、湘潭设立邮局。湖南的商务机构也随着长沙的开埠逐渐增多,至1916年,“外人之(在湖南)设行通商者,计四十余埠”,以长沙为中心向四周辐射。交通、邮政的发展在促进湖南商贸发展的同时,客观上又加速了瘟疫的传播。病菌很大程度上是附着在旅客、货物和交通工具上沿着交通运输线路传入其他地区的。
(3)由于长沙是省政府所在地,大小事务更容易被省府知悉,也与报纸等传媒的发展(如长沙《大公报》)、记录相对详细有很大关系。偏远之地即使发生瘟疫信息也往往难以外传。
(4)湖南传统商路有一纵几橫,纵线为岳阳(含平江)—长沙—湘潭—衡阳—郴州,北接武汉、长江,南通粤桂,既是传统商路,也是近代交通要道和南北战争的军事命脉。橫线之一为长沙—益阳—常德—沅陵,通湘西、湘西北接鄂、川、黔,也是传统商路和川、黔军队北上的要道。沿线城市和地区受外来影响较大,往往成为瘟疫频繁肆虐之地。
以下重点介绍1919年至1920年的湖南瘟疫流行简况,恰好距这次新冠肺炎发整整100年。
1919年夏季 “瘟疫流行渐广,上海、福州一带死亡枕籍,波及长江上游、武汉三镇”。8月上旬湖南首先在岳阳西乡发现“剧烈喉症,脑昏脚麻,染者不及半日而死”,县城内外亦发现有传染吐泄等症医药无效者。旋又发生赤痢流行,“每日死者约十数人、五六人不等。至疟疾热症触目皆是,患病之家十居八九。”继之“长沙、湘潭各处果发生疠疫,然一现即灭,死亡甚少。以为此后或可荷天庥,疫症不致再发。及长江各省虎疫(霍乱)盛行,常德、岳阳遂后先传染,近则省城内外亦有疫症发生,且传染日多。平均计之,每日死者约有七、八人。”《大公报》(长沙)10月9日报道“数日间疫死三十余人。”
是年先后发生疫灾的还有衡阳、武冈、辰州等地。衡阳霍乱流行,“疫势极险”,“传染者多而救治方少,数刻间即行毙命,城厢内外死者不知其数。”“中秋节前数日之间,死者病者到处皆有,棺木铺几无棺木可卖。” 疾疫流行最严重的是省会长沙,8月20日前后为“疫氛最盛时期,日毙在百三十人以上”。《大公报》(长沙)自9月25日逐日公布疫情,
| 分类 | 霍乱 | 赤痢 | 痢疾 | 伤寒 | 白喉 | 说 明 | 总数 |
| 死亡 | 100 | 47 | 43 | 36 | 1 | 不详2人 | 229 |
| 住院 | 152 | 215 | 7 | 59 | 4 | 治愈出院21人 | 458 |
| 门诊 | 195 | 549 | 949 | 142 | 8 | 不详8人伤寒4人 | 1855 |
| 总计 | 447 | 811 | 999 | 237 | 13 | 35 | 2542 |
| 死亡率% | 22.3 | 5.8 | 4.3 | 15.2 | 7.7 | 9.0 |
1920年春季有明确统计的疫死人数计长沙40人,平江鼠疫死3000多人,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死2000多人,通道、永州不详。夏、秋季计长沙50人,辰州20多人,溆浦120多人,共计近200人。湘潭、溆浦、岳阳、醴陵、辰溪、常德人数不详,估算全省死亡人数为6000—7000人左右。
关于疫病种类,从报纸公布的数据而言,1919年9月17日-10月31日长沙患霍乱死亡人数居首位(100人),其次为痢症(含赤痢与痢疾90人),均为消化系统疫疾。其次为伤寒(36人)和白喉(1人)。感染人数(即死亡、住院及门诊人数之和)依次为痢症(含赤痢与痢疾1810人)、霍乱(447人)、伤寒(241人)、白喉(13人)。死亡率依次为霍乱、伤寒、白喉和痢症。
应该说明的是,以上统计材料大多为城市及城郊,广大农村尤其是远离城市中心的穷乡僻壤偏远山区很少有人关注,那里的农民生活困苦,缺医少药,是各种瘟疫的主要受害者。一旦感染疾疫,他们束手无策,只能坐以待毙。事实上,从发病率而言,真正威胁民众健康的主要是疟疾,从死亡率而言威胁儿童生命的杀手是天花和麻疹。由于前者发病率高但死亡率并不高,后者死亡率虽高但被认为是人人必过的铁门槛,生死关,司空见惯,发生死亡事件不足为怪。1920年8月岳阳“瘟疫发生城乡内外,因患疟疾转痢疾以殒命者固多,而四乡因此病亡者更复不少”。可见当时疟疾患者相当普遍,患者众多,湘省城乡广泛流传“谷子黄,人上床,摆子如狼,呼天喊娘;千亩良田,一片荒凉”的民谣。
瘟疫传染的对象首先是亲密接触的家庭成员。无论是呼吸道传染还是消化道传染家庭、家族成员都首当其冲。如长沙“北门外苏家、楚家湖地方,有袁桂林者,耕田为业,家道小康,合计男女大小有二十二人。一时春瘟症暴发,传染甚速。闻数日之间染春瘟病者十八人。七日之间一连死去九人,竟备办棺材不及。其余九人尚在垂危。” “有高姓者一家老幼八口,因时疫传染,于日前毕命七口,只遗一女,年十八岁。先死之人尚有人操持营葬,其父后死,乡人恐受传染,均裹足不前。女以无法掩埋,颇形忧虑,适有邻村某货郎前来售货,女以早曾相识,出外商议,如能营葬其父,愿侍枕席。货郎贪恋产业,毅然许之。营葬之后,始成夫妇礼,住于女家。兹据城南来人云于本月七八两日,该夫妇亦先后染疫身故。”
此外,亲友近邻来往密切,或空气传播,或接触感染,也属易感人群,“有一人受疫,传染一家一村者。”
从职业上看,下列属易感人群:
(1)军警: 1919年9月30日陆军第七师补充第四团5名士兵感染霍乱。商埠巡士谢某、四团二营五连护兵连胜均患霍乱死亡。1920年霍乱首先从军队中暴发,8月18日从武昌至长沙的火车开至汩罗站,检疫人员上车检查,“车上人众拥挤,军人尤多”,查出染杂病军人6名,染霍乱士兵周玉龙、周毕陶2人,均送往隔疫所防治。常德“各该营连兵士,病者甚多,而因病致死者,日以数人计。”9月报载:湘潭“近日由城陵矶开来之二区守备队各营,其兵士染虎列拉病者甚多。该区谢副司令来潭,特以十一总临丰宾馆为病兵休养所,以示隔离而免传染。闻该所病兵约有二三百之谱云”。
(2)囚犯
1920年辰溪的疫病系从监狱发生。9月17日“典狱署囚犯有四人同时染病,经一昼夜同时而逝,闻多系未决犯,覊押待质。”
“军队为多人群居场合”,旧时军营和监狱人员密集,空间狭小,空气混浊,环境龌龊,大小便均在室内置一粪桶,臭气熏天,极易感染和互相传染疾病。“长沙旧监署内容腐败已极,越狱之事屡见,一年间三易典狱官。”甚至还多次发生过囚犯因饥饿而越狱的事件:长沙看守所“已押囚犯二百余人。去腊中有数犯因日食半薪,屡次冲出逃生,旋被捉获加镣,幸告无事。但该所经费向无酌款,纯恃财司每月摊发三成经费挹注。惟因日食昂贵,囚粮无着,每日食米二石有奇,实难支持。闻该所傅所长四处挪借,亏累二千余元。所有员役薪饷尚积欠一千余元。及至昨日,竟至断炊,被押人犯因饥饿难堪,遂于昨午相率冲监,势甚凶猛。”士兵和囚犯待遇低下,饮食恶劣,或病或伤,体质羸弱。士兵流动性大,与敌军频繁接触,均属易感人群。
(3)学生:住楚盛旅馆的湘雅医院英算专修科学生谭方岳、北区留学达才法政学校刘如愚、女子师范生黄某均患霍乱抢救无效死亡。学校也是人员密集之地,感染性较大。连法政学校校长戴真铨也患霍乱死亡。1918年新化“大同镇地方自八月以来忽发见一种瘟症,传染甚速”,“闻该镇小学校学生数十名现已病十余人。”一位记者“到某著名中学校区看一个亲戚某君的病。某君住在调养室内,一进门去,奇气刺鼻,锐不可当。房门窗门关得铁桶一般,房内共有三人,一为淋病者,一为肺痨病者,肺病者奄奄一息,痰唾满地。某君患伤风,卧于肺病者之对面,呼气互通,登时记者吓得汗出如雨。”“著名中学”卫生状况尚且如此,其他学校可想而知。
(4)旅客:旅客主要为经商、谋事、出差、调遣和探亲外出,他们乘车乘船,在人员麇集的环境中易于感染。如旅客傅士元由常德乘轮至长沙感染霍乱,送医院诊治。湘乡人、商埠区旅客谭晓初在普济小轮患痢症。长沙邹福由常德乘轮返省感染霍乱死亡。淑安轮船旅客、江西人袁汉章在船染疫;在吉安轮船染疾的旅客有湘阴人卢春华、衡州人王春元。1919年9月有人发现长沙“火车道旁患疫一人,惟已不省人事,不知姓名,询及左右住户,云系今晨欲搭株萍铁路车旅客在此得病。”
(5)船民 :1919年,家住湘潭十总的船户蒋之植、十三总的船户冯鸣龙、十总永走码头的船户谢志茂均患痢症死亡。船民以船为家,四处游走,容易接触病源体,又多使用不洁之水,易于感染。湘潭死亡的14人中有13人住在临河的繁华区总街,11人死于痢症,可能与水源被污染和人口密集有关。
(6)其他:如1919年9月20日医院出诊,发现伤寒患者4人,其中1人为布店工人,1人为算命者,一人为伙夫。长沙县中学校工陈伯林患肠窒扶斯死亡。1920年8月皮匠姜得佑霍乱致死。常德 “虎疫流传”,“船工河街苦力流者最多,日数人至20余人不等”,“据常德广德医院云,旬日来染虎疫赴院请诊者,计247起,已死多人。”
报纸公布的染疾病员及死者,除以上少数特别说明其职业与身份之外,大多只有家庭住址。有的身份虽然不明,但从其家庭住址可以推知其生活环境和家庭经济状况。如住东区篾棚内王友乾、住盐边坡茅棚内的赵杨氏均患霍乱致死,住铁路旁篾棚内的马瑞祥患痢疾身故,这些都是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生活极其艰难的下层民众,有的甚至可能是无家可归的难民或流民。又如1924年7月30日至8月5日长沙防疫医院共死3人,“一为长沙地方雇工人郭兴贵,患脑出血病,入院即死。一为牛渚洲苦力杨子林,患痢症。一为潮宗门茶馆巷任厚坤,患热肠症,因住院后又回家误食硬饭,病剧,复入院时已无救矣”。这些人居住环境拥挤龌龊,工作繁重,生活质量低劣,身体素质不佳,均属易感人群。患病之后往往也因家境拮据无法及时就诊用药,导致病情恶化乃至死亡。
三、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湖南瘟疫流行简况
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湖南水旱自然灾害和战争的破坏烈度都大大超过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 瘟疫肆虐亦较前期有过之而无不及。几乎每年都有瘟疫发生,有的年份几乎殃及全省。以1938年为界,后期疫情更猛,危害更烈。10种疾疫之中,尤以具有高传染性的疟疾、痢疾、霍乱、伤寒发生频率较高。这个时期呈现出多种疫病在同一年度内并发的状态。1938年后有5个年份同时遭受到10种疫病的袭击,1942年有9种疫病流行,最低的1939年、1940年和1944年也有7种疫病流行。据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统计,1938年日军入侵后湖南每年疫灾都在40个县次以上,1946年更是达到380个县次,平均每县达4次多,即同时受到4种以上瘟疫侵袭。
瘟疫流行与自然地理条件有一定关系。长沙、岳阳、衡阳、常德等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瘟疫易于传播,这在上文已作论述。此外,如平江是疟疾流行的高发区,该县地处山地丘陵地带,属湿润性大陆季风气候。境内森林茂密,竹类丛生,溪渠纵横,有利于蚊虫的孳生繁殖。清末至民国时期,境内80%的人口先后患过疟疾。
1930-1932年,平江全县患疟疾病近30万人。虹桥、长庆、天岳部分村庄屋场出现死人未埋、活人待毙而同睡一床的惨状。平江旅省人士方克刚、李积琨等募购大批药丸,亲带湘雅医院医生,赴乡施诊。1933年是平江疟疾发病率最高的一年,仅长寿地区6万多人口中,疟疾患者竟达5万余人,死亡万余人(含痢疾死亡人数)。据旅省平江同乡会为救援家乡疫灾呈报湖南赈务会请求给予赈济的调查报告中记载:“窃属县不幸,浩劫之后,继以瘟疫、疟疾流行,传播甚速,现已遍及东、南、北三乡,居民染病者达百分之九十。秋稼登场,竟萎田间,无人收割。户、村相继病倒,死亡枕籍,收殓已乏棺材,草葬苦无人抬。炊烟断绝,行旅戒途,姻戚禁相通问,哭泣痛不成声。贫病交加,父母兄弟姐妹妻儿面面相觑,共约同赴黄泉,各以先死为快。”1934年春全县疟疾、痢疾患者达20万人,嘉义地区发病18000人,死亡2000余人。1936年夏秋两季疟疾大流行,嘉义、安定、献钟、瓮江、三联一带发病1万余人,死亡数千人。1938年省卫生实验处派员到芦洞等地调查,体检490人,有疟疾明显症状者383人。
根据统计,1939—1946年湖南12种法定传染病中患者人数从高到低排序依次为:疟疾、痢疾、霍乱、伤寒、天花、回归热、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斑疹伤寒、白喉、鼠疫、猩红热、黑热病。
死亡人数从高到低排序依次为:霍乱、痢疾、疟疾、天花、伤寒、回归热、流行性脑脊髓膜炎、鼠疫、斑疹伤寒、白喉、猩红热、黑热病。
病死率从高到低排序依次排序为:鼠疫、霍乱、天花、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斑疹伤寒、猩红热、白喉、伤寒、痢疾、回归热、疟疾、黑热病。
患病人数在全国所占比例从高到低排序依次为:痢疾、疟疾、天花、霍乱、伤寒、回归热、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白喉、斑疹伤寒、猩红热、鼠疫、黑热病、
死亡人数在全国所占比例从高到低排序依次为:痢疾、疟疾、天花、霍乱、伤寒、回归热、斑疹伤寒、猩红热、白喉、流行性脑脊髓膜炎、鼠疫、黑热病。
综合考虑,对湖南影响最大的疫病为霍乱、痢疾、疟疾、天花、伤寒,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白喉、回归热次之,猩红热、斑疹伤寒、鼠疫又次之,黑热病仅发现患者一例。
(作者单位:湖南科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