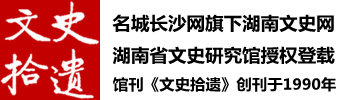长沙基督教女青年会的斯堪的纳维亚女人(1917-1927)
作者:玛琳·格雷格森Malin Gregersen 译者:陈娟
(注:本文译自《斯堪的纳维亚历史期刊》,2015年第3期(Scandinavian Journal of History,2015 Vol.40.No.3,382-404)。内容有删节。)
背景:长沙和基督教女青年会
长沙当时是一个繁忙的工业城镇,因拥有湘江这一重要港口,使之成为湖南地区的中心。这是几个基督教会组织的运作领域。1902年,湖南第一次允许外国人建立自己的布道组织时,挪威布道团(NMS)是这座城镇建立的第一个布道场所。十年后,两位挪威传教士在长沙建立基督教青年会;1910年代晚期,斯堪的纳维亚基督教女青年会加入,而20世纪20年代初,瑞典教会(CSM)也带着路德大学的长远计划加入进来。
基督教女青年会19世纪中期就已经存在,与基督教(男)青年会同行,是全球性的各基督教派系间的运动。基督教女青年会在长沙的工作于19世纪晚期开始,第一个中国总会形成于1899年,且于1903年任命了第一任会长。中国的基督教女青年会的主要工作是在贫穷的妇女和儿童之间开展不同的“社会改良项目”以及对上层社会儿童和妇女的教育。瑞典会长英格堡·韦康德,1917年来到长沙,启动基督教女青年会工作。1919年,长沙基督教女青年会成为中国第五个基督教女青年会,有中国会员10人。通过长沙妇女间的联系,韦康德设法为她的新组织在长沙市中心的左家大院寻求到安全场所。有着五代人的左氏家族,是曾平定太平天国起义的著名的左宗棠的后代。他们的新主人,左太太(或左家五小姐)是这一大家族的一脉。1923年,因布道场地太小,女青年会搬迁到城郊宽敞的左家祠堂。
长沙基督教女青年会前期很活跃。紧密团结的斯堪的纳维亚传教士小组有几个瑞典和挪威布道组织的积极支持,也有全球组织和网络的国际支持。虽然基督教女青年会本身就涉及不同教派,但四位斯堪的纳维亚传教士和挪威、瑞典的路德宗密切相连。怀着对未来的高期望,1910年代后期的暴力事件只是被看作长期积极发展过程中短暂的障碍。1910年代后期以及1920年代初期,基督教女青年会处于能给他人提供保护的地位:传教士们有来自国际布道组织和全球布道网络从道义、经济和基础设施上给予支持。1920年代末,形势改变。纳特霍尔斯特和斯腾费尔特都离开基督教女青年会工作站,分别加入NMS和CSM的工作,传教士们被分散。从1920年代中期开始,她们经历了一个新的时期:暴乱、社会动荡、反外情绪增长。1920年代出现的反基督教运动、北伐战争以及国民党在这一地区的发展,政治格局转变,导致一场更直言不讳的民族主义运动。在此期间,很多外国人以及他们的财产都需要保护,以免遭责难和攻击,中国基督徒以及与传教相关的人们也一样。资产被没收,物质资源遭破坏,布道工作的长期投资受到威胁。1927年春,来自不同教会的大多数传教士迫于政治形势离开湖南,长沙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工作被迫中止。
框架:性别、保护和女传教士
和当时大多数其他女传教士一样,长沙斯堪地纳维亚基督教女青年会的传教士(后来瑞典教会的传教士)特别关心妇女和儿童的生活。她们想通过教育和社会活动“提高”妇女地位,且为未来基督社会奠定基础。在女子学校和孤儿院的工作表明了她们的志向:引导女孩和成年女性走向一个由谦逊和虔诚的基督教价值观塑造的女性时代。这种价值观以她们路德宗的认知为特征——女性的天职在家庭、且只有在家庭女性才得以发挥其潜能。理想如此,然而,矛盾的是:很多在儿童和妇女中工作最积极的女传教士们是强势、权威、独立的单身女性。
通过大量、一系列的原始资料——来自瑞典、挪威,以及中国基督教女青年会组织,也有挪威布道团(NMS)和瑞典教会(CSM)的私人及供传阅的信件、报告、文章以及书籍等,资料中对在中国的工作的叙述,我们了解到四位斯堪的那维亚基督教女青年会的传教士:英格堡·韦康德,露丝·纳特霍尔斯特,维丽·斯腾费尔特,以及埃斯特·霍尔英,她们对保护的看法。
首先,是保护标志的使用,如白人的脸和外国国旗;第二,作为保护空间的布道场所。这两个部分都集中在该时期的第一个阶段的暴力和暴乱,特别是从1918年3月军队的势力从南部转移到北部,至1920年6月从北部转移至南部的暴乱(1918年3月至1920年6月是北洋直系军阀张敬尧统治湖南时期)。第三部分,重心转移到了结束期,这一时期随着北伐战争发生政治动乱和暴力斗争,军阀时代结束。本文特别关注的焦点是女传教士作为监护人以及在1926年城市周边的战斗期间遭受威胁的布道场所。最后分析部分着重于紧接着发生于1927年传教士大规模的撤离,包括1918年事件的简要回顾。
使用保护标志:旗帜和面孔
1917年,英格堡·韦康德开始她在长沙的工作时,许多的左家成员已搬出了祠堂,离开这个不安全的城市,去了更安全的地方。1918年,当军队威胁要接管这些空房子时,左太太——左家五小姐,邀请英格堡·韦康德带着她在长沙精英中开展基督教工作的计划,搬进这个城市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建筑之一:左家祠堂。虽然我们不太了解左女士的个人动机,她自己不是基督徒,却卷入基督教女青年会工作的妇女和儿童工作中(在很大程度上,她确实做了),但我们明确知道这是为这所房子提供保护的一个战略转移。一面外国国旗是阻止士兵进入和抢劫的保障,很快瑞典国旗就在标明外国人居住在内的大门旁边飘荡。利用外国国旗保护财产是传教士们是常见的做法,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传教和帝国主义之间是紧密联系的。
瑞典人不仅利用他们的国旗作为保护伞,他们的脸也有相似的用法。英格堡·韦康德讲述她和莫尔顿小姐(长老会传教士),怎样帮助中国红十字会在外面守卫战争监狱:“我们只是笑,坐在一中国梧桐树下的长凳上,两名女性保护着几千犯人——只有我们的‘白人面孔’——对抗武装部队的士兵”。外国旗帜和欧洲面孔充当了对抗入侵者的保护伞。作为女性,在安全的情况下,她们习惯于服从男人,但在这里,他们的种族被认为优于他们的性别;即使他们嘲笑这点,她们作为白人妇女的象征价值在这种情况下还是把他们放在一个平等的,甚至优越于自己教友卫士——中国男人的地位。
然而,他们的外国面孔和旗帜的保护价值只是象征性的。对外国人的不平等待遇有法律根据。该条约规定起源于19世纪的一些国家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协定,保证这些外国侨民的治外法权。这些条约导致中国人与外国人的不平等待遇,并在20世纪上半年成为冲突和不满的根源。瑞典的女士搬进左家时,当地报纸即刊登政府颁布的法令,声称这所房子现在处于当局的保护之下,就是这种条约的一种体现。
保护场所:不安全城市中的安全避难所
1918年3月,长沙市被骚乱所震撼。3月25日,隶属于南方军的省长离开了这个城市。当晚,退役士兵和当地居民洗劫了这座城市。第二天,两个瑞典女传教士,韦康德和纳特霍尔斯特与她们的中文老师霍先生一起前往挪威传教站。他们以观察员身份穿过暴乱的城市,看到昨晚抢劫的结果:商店和商行被摧毁,人们受伤和被杀。在他们行走过程中,他们的男老师变得越来越紧张;当他们接近市中心的时候,暴乱变得更加强烈。瑞典人说,由于两个女人在他的保护下,他们安全到达了传教站的大门时,他显然松了口气。而之后她们独自返回时,街上的情况恶化了,两位妇女很快选择返回挪威传教站,等待有人陪他们回去。纳特霍尔斯特强调,她们穿过城市并不害怕,但她们返回是考虑到信任她们的人。正如引文所叙的纳特霍尔斯特和斯腾费尔特的事例,纳特霍尔斯特和韦康德在此坚持对男性监护人的普遍看法,同时在她们的叙述中与他们保持着清晰的距离。
当两位女士抵达挪威传教站时,他们看到的是一个充满难民和受伤民众的传教站,但它在被毁坏的邻里间完整无损。传教士J. A. O. Gotteberg一直整晚守在传教站外面,以防火灾和抢劫。两年后,1920年,在随着权力的转移而发生的暴乱中,韦康德不再是一个观察者,而是一个左家大院的守卫者。它与左先生及一些仆人一起,巡查大门。她充当了一个守护者的角色,以此超越了女性职能领域的界限。传教站的大墙成了里面人与外部威胁者之间的界限,一个标有外国旗帜和武装护卫者建立的空间分隔。然而,标志的保护价值是相对的,到20世纪20年代末,界限被超越了。
受威胁的空间:社会母亲和监护人
由于1920年的暴力事件,左家大院和其他布道场所一样,在中国红十字会的组织下改为难民营。左家祠堂的人卷入城市的安全保卫事宜中,英格堡·韦康德和左家五小姐的继子一样,成为红十字会的一员。韦康德负责左家大院,而莫德罗素(Maud Russel)(莫德罗素,美国社会工作者、教育家和作家,1917-1943年在中国基督教女青年会工作,1971年成为美中人民友好协会——译者注。)和露丝·纳特霍尔斯特负责市内其他难民营。
1926年,在洗劫城市周边的战斗中受伤的士兵要占用布道场所。排外情绪是这次冲突的重要部分,而布道场所的安全更不明朗。长沙基督教女青年会已在旧左家大院成长壮大,搬迁到位于城市另一处的左家祠堂。由于大多数祠堂是公有财产,左家私人祠堂也被很多官员“惦记”,试图为他们的士兵和伤员获取这一资产。韦康德不得不多次为自己和女青年会向来访者辩护,解释为什么她们——基督教徒和外国人——“占有”了国家财产。她特别讲述了一些官员和一个讲德语的中国男人想进入大院、祈祷室和教室:“当我们强调不可能在我们附近驻扎官兵时,那男人相当暗示地表示:‘喔,你完全不必担心你的女孩们,我们有自己的女人’”。他的这些说法,间接的道出了士兵的威胁,也确认女孩们被作为性目标;但当他暗示大院内有不合适性关系时,也为她们提出了道德上的威胁。然而,就在第二天,当他们准备进入大院——祠堂和祠堂内部不属于基督教女青年会租赁合同的部分——从市议会的官方信息传来:他们不得占用祠堂,已另安排别处。左家亲戚为了保护祠堂幕后操纵了此事。
过了一段时间,又制定了在祠堂大院内为前线的伤病员提供住处的计划。一千名伤病员将到达长沙城,由于其他所有可能的地方都已占用,他们将来到大院。韦康德担心如此近距离驻扎易感染的病人有危险,而当该计划未实施时她明显地如释重负。中国干事认识部队医院的主管,(主管)代表他们进行了交涉。正如前面的事例一样,这表明:对左家大院的保护是依赖于中国妇女的关系网及行动。韦康德强调传教士之间合作的价值,他们对形势的共同掌控以及友谊和信任的增长。传教士们在自己的故事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同样清晰的是,她们的同事在与政府官员以及街道上的人民代表进行谈判时,也发挥了同等重要的作用。当韦康德抵挡入侵者时,她在他人的帮助下做到了。中国干事和左家人利用他们的关系网也使占用左家大院的计划得以改变。
第三次,一名带有大约100个男人的官员终于进入了大院。在她的述说中,韦康德描述了自己保卫她们生活和工作空间界限以及维护女孩们在接近士兵时的安全的行动。她写道:在基督教女青年会中有一个军营感觉是相当奇怪的,并描述了士兵们怎样在做体操时企图去看那些女孩们。她也描述了他们如何超越约定界限,以及他们的不敬如何成为她和士兵们争吵和冲突的根源,但也描述了她如何与那位官员保持良好的关系,以及他如何使其他人尊重他们的界限。这些士兵在五天之内就离开去了前线,女青年会赶紧和左家一起安排一所儿童学校搬进祠堂大院内,以保证大院将来不再有类似的造访者。
营救救助者?被男人保护,被上帝保护
在韦康德保护大院内女孩们的安全使她们免受伤害的斗争的事例中,外国面孔和旗帜的标志性价值在1926年已下降。到1927年,传教士的情形更是戏剧性地恶化。上半年,几乎所有在长沙的传教士以及在中国内地的大多数传教士都被疏散。3月,局势稳定,但是3月下旬和4月,动荡重现,大多数仍在此地的传教士不得不突然离开,英格堡·韦康德已经在2月离开,而曾决定留在长沙的埃斯特·霍尔英接到全国委员会撤离的命令,于3月12日离开。到4月初,只有两个斯堪的纳维亚人仍然在长沙城—维丽·斯腾费尔特和露丝·纳特霍尔斯特作为瑞典教会的传教士在工作。4月和5月,许多传教站遭掠夺或被他人接管;基督教女青年会大院被关闭,其建筑及库存资产被没收。
起义和内战迫使斯堪的纳维亚女传教士,积极地将自身的安全与当局及国家赋予她们的对自己和其他人的安全需求紧密联系在一起。1927年的情况可以与九年前即1918年的类似事件进行对比:1918年,一份书面命令说,由于政治局势原因,所有的美国妇女和儿童—更恰当地说是所有的西方妇女和儿童,都应撤离长沙。当时在长沙的两位瑞典人,露丝·纳特霍尔斯特和英格堡·韦康德都很高兴她们是“瑞典公民,在两种情况下都不会被迫离开这个地方。在那里,我们感到比其他任何地方更安全,那里也是我们的职责所在”。她们认为,这一呼吁违反了她们各自的使命,并批评它对在难民中所造成的恐慌缺乏考虑。“有成百上千的人在她们的大院内寻求保护,女子学校的所有女孩被托付给她们照顾,其中很多人在长沙没有家或亲戚—离开这些人在我心中是一种犯罪。”最后,只有美国妇女和儿童服从号令,其余的留在原地。1927年,当纳特霍尔斯特和斯腾费尔特选择留在长沙时,并没有任何技能或使她们特别适合的任务激发她们。她们认为她们的命运由上帝决定,而她们自己实际上并没有选择。纳特霍尔斯特自己写道,她相信让女人留在后面的原则是错误的。
斯腾费尔特还谈到露丝·纳特霍尔斯特和她一起留在长沙的决定:“她的意思是正确地行动,并意味着她有权留在这里,保护我,既然她这样做是出于对我的爱,那么我必须尽力接受这个爱的提议”。
结论
对1917至1927年间在长沙参与基督教女青年会及其他传教工作的四位斯堪的纳维亚路德宗妇女来说,不同的性别保护观念经常发生碰撞,在话语结构中同时制造了矛盾及谈判的可能性。一方面,传教士妇女充当了她们同事和学生的监护人;另一方面,她们作为传教团体中的女性以及她们的家乡背景,被认为是需要守卫的。
(作者单位:开福区教科所)
【长沙基督教女青年会的斯堪的纳维亚女人】玛琳·格雷格森 陈娟2018年3期总113
2018-12-07 19:20:38 来源: 评论:0 点击:
长沙基督教女青年会的斯堪的纳维亚女人(1917-1927)作者:玛琳·格雷格森Malin Gregersen 译者:陈娟(注:本文译自《斯堪的纳维亚历史期刊》,2015年第3期(Scandinavian Journal of History,2015 Vol 4
分享到:
相关热词搜索:
上一篇:【先伯父罗正纬致毛主席信中的往事】罗奇玉2018年3期总113
下一篇:【剪不断的“飞虎情”——陈香梅芷江纪事】龚卫国2018年3期总113
分享到:
频道总排行
频道本月排行
- 41【铁血铸丰碑——浏阳党史人物简述】邓继团2021年3期总125
- 36【元代名人邓谦亨及其浏阳后裔族群考】邓继团2022年4期总130
- 20【烽火间隙的酬唱和风雅】王金华2022年4期总130
- 11【革命情深两世家——陈、黄两家的交往】陈崇孝[黄兴诞辰...
- 11【文强非毛泽东表弟考】邓继团2018年2期总112
- 9【近现代长沙旅馆业史略】乐兵2023年1期总131
- 8【白果园33号:一座名宅与一位名医的往事】彭坚2022年4期...
- 7【芋园、芋园主人与芋园文化】李崧峻2011年2期总84
- 6【长沙设市前后的城市建设】任理2024年1期总135
- 6【湖南传统国术“八拳”】羊定国2014年1期总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