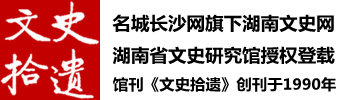“精神气质”是一种主体化的精神文化。湖湘文化的历史建构,首先是湖南人的精神气质的建构;湖湘文化的区域特质,特别体现为湖南人在精神气质上的特质。湖湘文化的重要标志,就是一种地域化精神气质的形成。
在历史文献中,存在大量关于湘人精神气质的描述。在引述这些史料展开讨论之前,我们首先需要界定,什么是“精神气质”?
“精神气质”是一个我们运用得较多,但又有待深究的概念。在西方文化人类学界,学者们将某一民族、部族、社会群体的精神风貌、性格气质用“ethes”表述,中文译著将其译成“精神气质”。用“精神气质”来说明一个部族、民族或者社会群体的“文化——心理”特征,确实是一个具有很强综合性、概括性与表达力的概念。作为一个体现为主体化文化一心理的概念,“精神气质”其实包含着“精神”与“气质”的两层涵义。其一,“精神”层面的文化意义,这个“精神”主要又是指道德、审美的文化意义,如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兹[C.Geertz]说:“特定文化的道德(和审美)方面,评价性元素被称为‘精神气质’。”他认为,“精神气质”不包括文化中的知识学问,这只是一个与知识学问的“世界观”相对应的价值观方面的概念。其二,“气质”层面的生理心理意义,在心理学意义上,“气质”通常是指个体以生理为基础的心理特征与个性风格。由于精神文化与生理气质是紧密联系、相互渗透的。所以,人类学家用“精神气质”来表达某些社会群体、民族部族的人们在“文化——心理”方面的特质、风格、品性,描述他们在道德、审美的文化精神影响下的心理方面的特征。因此,“精神气质”的概念是结合精神文化与心理文化,以表达某些特定的社会群体(部族、民族、国家、地域等 )的文化心理的结构、功能与特征。
一、民性:湘人的气质之性
由于精神气质是由“精神”与“气质”两层涵义构成的,所以我们首先考察湘人的“生理--心理”意义的“气质”层面。历史文献对此有较多的描述,史书上往往称之为“民风”、“民性”。
本土“湘人”的来源如果往上追溯,是所谓的“南蛮”。在古代经史文献中,中国分为东、西、南、北、中等不同地域,并有不同部族和不同的气质、性情与风俗,对于南方的部族,包括《礼记》在内的各种经史文献统称之为“蛮”或“南蛮”。其实,“蛮”不是某一个部族的专称,而是南方非华夏民族的各种部族的泛称。在不同历史时期,“蛮”往往与不同部族、地名连用。如在尧舜时代,“蛮”与“三苗”部族连用,称“苗蛮”;春秋战国时期,“蛮”与楚族连用,称“楚蛮”;秦汉以后,“蛮”又与湖南各地名连用,分为“长沙蛮”、“零陵蛮”、“武陵蛮”,即指这些地区非汉族的少数民族人,人们将其通称为“诸蛮”。讨论湖南地区的蛮族群体十分重要,因为历史文献所记载的湖南人的精神气质、文化性格等等,均与湖南地区的蛮族血统及文化传统有关。
如果沿着历史长河往前追溯,湖南地区的土著部族可追溯到“三苗”部族。在距今四、五千年前,即尧、舜、禹时期,湖南地区的土著部族称之为“三苗”。在先秦至秦汉的历史文献中,均有大量关于南方地区的三苗部族与中原地区尧、舜、禹的部族之间的军事冲突。“三苗”本是一个由诸多部族结合的部落集团,活跃于长江中下游地区,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后来学者认为这里所说的“崇山”现在湘西大庸。地方志记载:“驩兜墓在崇山,舜放驩兜于此,死后遂葬于山上。”这就是所谓“苗蛮”的来源。人们称尧舜禹时期湖南的土著部族为“有苗”、“苗蛮”等。
苗蛮部族的性格、气质普遍表现得骁勇、刚强、自慠。人的气质、性格往往通过其社会交往的行为方式体现出来。各种历史文献中,均大量记载“苗蛮”、“有苗”或“三苗”与中原部族首领尧舜禹之间的长期而激烈的战争。为什么苗蛮与中原部族之间有这样长期的战争?《尚书·大禹谟》称:“有苗弗率”、“苗民逆命”;《竹书纪年》载:“有苗氏负固不服。”另,孔颖达疏《尚书·周书·吕刑》云:“三苗复九黎之恶,是异世同恶。”这些记载说明,苗蛮是一个刚强、坚勇、自慠的族群,他们不服强大的中原部族,长期与中原部族展开激烈、顽强的搏斗。正由于他们骁勇、倔强的性格气质,故而大禹与三苗的战争一直进行得残酷与激烈,据古本《竹书纪年》记载:“三苗将亡,天雨血,夏有冰,地折及泉,青龙生于庙,日夜出,昼日不出。”另外,其他历史文献均有关于大禹与三苗之间激烈战争的记载。这均反映出苗蛮部族是一个有着刚强气质的部族。
到了商周及春秋战国时代,湖南地区的居民主要是“荆蛮”与“楚蛮”。无疑,这个时期的荆蛮、楚蛮与尧舜时代的有苗、苗蛮有着历史渊源关系,有苗、苗蛮的后裔是荆蛮、楚蛮族群的主要来源。这也是楚武王熊渠为什么会自己声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他明确将自己的族群归之于南方的蛮夷族群,并鲜明地表达了其倨慢、狂傲、强悍的气质。无论是荆蛮,还是楚蛮,他们的气质、性情仍然与苗蛮有着相似性,即不像中原华夏部族形成了所谓的“文教”与“德性”的文化,而是更多地保留着其自然的性情和刚勇的气质。他们在和中原部族的抗争中进一步强化了这种骁勇、顽强的性格与气质。所以,上古的文献中常常有商、周王朝征讨“荆蛮”、“楚蛮”的诸多记载,诸如“方叔帅师伐荆蛮”, “蠢尔蛮荆,大邦为仇。方叔元老,克壮其犹。”正因为荆蛮、楚蛮具有骁勇的性格气质,不愿臣服中原王朝,才导致商、周时期诸多王朝的征讨、战争。
而且,史籍中还有关于楚蛮的性格、气质的具体描述。《礼记·王制》谈到“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并具体说到这种气质、质性体现为“刚柔、轻重、迟速异齐”。如果说中原人因受到“文教”、“德教”的熏陶而在气质上变得柔和、凝重、迟慢的话,那么这些楚蛮、南蛮的气质则更多表现出原始野性的刚烈、轻剽、快速。《史记》记载:“楚人鲛革犀兕,所以为甲,坚如金石;宛之钜铁,施钻如蜂虿,轻利剽遫,卒如熛风。”这里所说的“轻利剽遫,卒如熛风”就是楚蛮在气质上的轻剽、敏捷。西汉时期,人们对楚蛮的气质、习俗有进一步的描述。如张良对刘邦说:“楚人剽疾,愿上无与楚人争锋。”又如“荆楚僄勇轻悍,如作乱,乃自古记之矣。”可见,到了汉代,楚蛮仍然保留着他们的“剽疾”“剽勇”“轻悍”的气质特性,并认为这是他们喜好并能够与中原王朝对抗的原因。
两汉以来,向以蛮族为原著民的湖南开始“汉化”,依据谭其骧先生的《湖南人由来考》,汉末王莽之乱,中原人士开始大举移殖荆湘,从而开始蛮、汉杂居,历经两晋、唐宋、明清等历史时期的不断移民,湖南才逐步形成一个以汉族人为主、包括多民族聚居的地区。但是,一方面,因蛮汉通婚而使湖南的汉人中本就有着大量蛮族血缘;另一方面,那些长期定居于湖南的汉人,有大量又是由蛮族转化而来,谭其骧所著《近代湖南人中之蛮族血统》,考证了近代湖南大量汉人家族其实是秉有蛮族血统的。他还认为清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与“蛮族血统活力之加入”,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当然,清代湖南人材辈出是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但是湘人的生理--心理方面特质应是与蛮族血统有一定联系的。
所以晋唐、宋元、明清以来的大量历史文献,在描述湖南人的气质、性格、风俗时,更明确地肯定他们所具有的特质。《隋书》说:“其人率多劲悍决烈,天性然也。”即认为其蛮族的“天性”,具有“劲悍决烈”的气质、性格,与先秦、秦汉的苗蛮、楚蛮具有相以的气质。这一说法不断得到后人的赞同、响应。宋朝祝穆著《方舆胜览》讲到“湖南路”时亦说:“长沙卑湿,其人劲悍决烈”。在明清时期的诸多文献中,除了认同《隋书》关于湘人的“劲悍决烈、天性然也”的描述外,还增加了许多意思相近、内涵更丰富的论述。明代有人说:“长沙故大郡,地广物众,统属邑十有二,其人劲悍决烈,尚勇而好争,非得疏通练达介特廉明之士不足以治之。”除继续保留“劲悍决烈”外,还增加了“尚勇而好争”。在明清时期湖南各地州府县邑的方志中,到处都可以看到“人性悍直”“劲直任气”“其俗慓悍”“任性刚直”“其俗好勇”“劲悍尚讼”“尤尚力气”等方面的记载。可见,湘人的尚勇、好斗、任气、悍直等特征,确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特征。
由上可见,从苗蛮、楚蛮到诸蛮、湘人,他们的气质似乎有着前后相承、内在相似的特质,均表现出剽疾、勇悍、任性、劲直、尚气等主要特质。这种“气质”是如何形成的呢?学者们有多种解释。一种认为与蛮族血缘有关,前述谭其骧是这种观点的代表;另外一种认为是地理环境,中国古代历史文献能找到相关的论述,强调由于地理环境的不同,各个地域会有不同的气质的差异。在中国传统典籍中,早已经对不同自然地理下的不同生理气质特点作过论述。《礼记·王制》论述说:
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修其教,不异其俗。齐其政,不异其宜。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
《礼记》作者认为,由于人们生活在不同的自然环境,故而形成了不同的风俗民情、气质之性。这里所说的“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方之民,皆有性也”,所说的正是不同的地理环境而导致不同的地域性气质或性格的差异。而湖南的民性之所以倔强、剽疾、尚气,亦与湖南的地理环境有关。历史上曾有不少学者提倡这种观点,民国时期著名学者钱基博认为:“湖南之为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四塞之国。其地水少而山多,重山叠岭,滩河峻激,而舟车不易为交通。顽石赭土,地质刚坚,而民性多流于倔强。”他明确将湖南人的气质、“民性”归之于地理环境。
上述从蛮族血统、地理环境方面的解释,均属于从自然条件来说明民性与气质的来源。另外还有一种社会条件的解释,即从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来说明湘人气质的形成。有学者强调,要考察民风的历史演变过程,关键在于人文环境的变迁。张伟然认为,“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文环境出现衍化。人地关系趋于紧张,生存竞争渐次加剧,故民风逐步得以嬗递。”应该说,从人文环境的变化来说明湖南的民性、气质的形成,亦有着相当的说服力。但是,考虑到人的气质的形成是一种生理与心理、自然文化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的过程,所以,我们仍然主张从自然条件(血缘与地理)与社会条件的结合,来考察湘人气质、湖南民性的形成。
二、士气:湖湘士人的精神气质
在讨论了湖湘的民性、民风,再来进一步探讨湖湘士气、士风。事实上,讲民性、民风,更多的是体现湖南人的生理--心理层面的“气质”方面的特质;而所谓士气、士风,则是指一种“精神气质”,即文化精神与文化心理的结合,而且特别体现出“道德与审美”方面的精神文化意义。
近代以来,湖南人以十分鲜明的精神气质而受到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特别关注和敬仰,被称之为“湖南人之性质”或“湖南人底精神”。近代著名政治家杨毓麟作有《湖南人之性质及其责任》,强调湖南人“有特别独立之根性”,其中列举“濂溪周氏,师心独往”“船山王氏以坚贞刻苦之身,进退宋儒,自立宗主”,王闿运“独树一帜”,郭嵩焘“能发人之所未见,冒不韪而勿惜”,谭嗣同“无所依傍,浩然独立”等等。而陈独秀则著有《欢迎湖南人底精神》,并由衷地赞扬说:“二百几十年前底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几十年前底曾国藩、罗泽南等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战’的书生!……”他还继续列举了黄兴、蔡锷等人。在这里,我们要注意两点:其一,杨毓麟、陈独秀所说的“湖南人”,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而是指那些特别优秀并体现为“士人”身份的湖南人,周敦颐、王船山、魏源、曾国藩、罗泽南、郭嵩焘、谭嗣同等均是传统士人;其二,他们所说的“湖南人的性质”、“湖南人底精神”,是一种“气质”与“精神”的渗透,尤其体现出“道德和审美”的精神文化的特质,这和“民性”“民风”中的刚烈、任气等 “气质”意义有所不同。
当然,在人们的一般观念中,民性、民风与士气、士习往往对举而言,人们容易将民性与士气看成是两种并列的文化心理现象。其实,“士”是“民”的组成部分,即所谓“士为四民之首”;同时,“士”也是来之于“民”,一般的民均可通过进入学校而成为“士子”,通过科举考试而成为“士大夫”。所以士人往往既具有民性、民风的心理文化即“气质”特性,又由于他们接受文化知识教育而具有“士气”“士风”的“道德、审美”等精神文化的特质,这就是我们在研究湖湘文化时,特别重视探讨湖湘士人精神气质的原因。因为湖湘士人的精神气质,不仅能体现湖湘文化中道德、审美方面的精神文化,同时也能反映出民性、民风等方面的社会心理文化。
正由于士风与民性密切关联,所以,在这个有着“悍直”“慓急”“尚气”“好勇”等民风民性的区域,其士气、士风也就具有许多相关的特点。杨毓麟概括的“湖南人的性质”与“特别独立之根性”,陈独秀所说的“湖南人底精神”,除了具有士人的精神追求外,还特别表现出上述民性、民风的特点。这样,虽然湖湘士人所接受的仍是那作为统一意识形态的儒家文化,但由于他们所具有的民性、民风的心理文化底色,对他们的精神气质形成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另外,他们长期积淀而成的教育传统、学术传统和精神传统,也对他们形成鲜明的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精神气质起了重要作用。譬如,那一直对湖湘士人有深远影响的屈原,其崇高理念与刚烈气质合为一体的精神气质成为历代湖湘士人的乡贤典范,以至明代王船山还由衷地赞扬他“唯极于死以为志,故可任性孤行,无所疑惧也。”无疑,这些具有楚蛮气质的乡贤,进一步强化了民性、民风对士气、士习的影响。
虽然,从总体上比较,湖南在整个古代历史时期的文化教育相对落后,与文化教育直接相关的士人群体也并不庞大。最著名的例子是唐代发达的科举取仕制度,湖南士人能够举进士者极为罕见,以至于刘蜕中进士后,人们惊呼是“破天荒”。但是不可忽视的是,自唐宋以后,湖南的文化教育不断发展,与之相关的士人群体不断拓展规模,到晚清达到极盛,成为近代中国最有文化创造力、政治影响力的士人群体之一。然而,最引人注目的是,湖湘士人群体所长期形成的具有地域特色的士风、士气,就是那种既具有楚蛮遗风、又具有斯文关怀的精神气质。
史书上关于湖湘士人的记载是从魏晋开始的。如果翻阅史料,就可以看到,这个时期的湖湘士人普遍具有“志气”“义勇”“高洁”“推诚”“质直”“言行笃信”等方面的精神气质,现例举几位:
周该,天门人也,性果烈以义勇称,虽不好学而率由名教。叔父级为宣都内史,亦忠节士也。
韩阶,长沙人也。性廉谨笃慎,为闾里所敬爱。……桓雄被害之后,二人执志愈固。
虞悝,长沙人也。弟望,字子都。并有士操,孝弟廉信,为乡党所称,而俱好臧否,以人伦为已任。
《晋书》中所列的这几位湖湘士人,一方面,他们身上均有着楚蛮遗风的民性,其气质体现出果烈、坚勇、悍直、尚气的心理文化特质;另一方面,他们作为受过儒家文化熏陶的读书人,表现出一种道德品性、精神价值的追求,故而有孝兼廉信、人伦为已任的精神特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悍直气质与德性精神是融为一体的,故而能够体现出“义勇”“忠节”“廉谨笃慎”“士操”等精神气质的特质。
唐宋以后,特别是两宋时期书院大兴,湖南成为书院教育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并产生了岳麓、石鼓等全国闻名的书院。故而两宋时期湖湘士人群体发展很快,列入《宋史》及各学案史传的人物大大增加。值得注意的是,这段时期湖湘士人的精神气质表现特别鲜明,从这些史传中可以发现,湖湘士人的精神气质鲜明地表现出那种强悍气质与精神情操的融合。这一点,在与抗金、抗元的斗争中体现得特别突出。现例举几位:
“赵方,字彦直,衡山人,父棠,少从胡宏学,慷慨有大志。……自言吾性太刚,每见刘公使人更和缓,尝请光祖书“勤谨和缓”四字揭坐隅以为戒。”他在抗金战场英勇杀敌,受到高度赞扬。
胡颖,字叔献,潭州湘潭人。他“感励苦学,尤长于《春秋》。”“性不喜邪佞,尤恶言神异。”“为人正直刚果,博学强记。”
李芾,衡阳人,“为人刚介,不畏强御”,“且强力过人。”他在官知潭州兼湖南安抚使时,指挥官兵抵御元兵,失败后,全家死于节义。
尹谷,字耕叟,长沙人,“性刚直壮厉,初处郡学,士友皆严惮之。”参加抗元的残酷激战,兵败而举家自焚。尹谷死后,岳麓书院诸生数百人去悼念,“城破,多感激死义者。”
与上述李芾、尹谷抗元死节相关,湖湘士人“忠节”“义勇”的精神气质,在岳麓书院的士子中表现得十分突出。据《宋元学案》记载,元兵攻取潭州时,岳麓诸生均参加守城战斗:
长沙之陷,岳麓诸生荷戈登陴,死者什九!惜乎姓名多无考。
从例举的这些案例来看,湖湘士人确有异常鲜明的精神气质。他们的突出特点是,一方面继承了南方的苗蛮、楚蛮的悍直、刚勇、任气的民性,故而才有“刚介”“刚直”“不畏强御”的气质;另一方面继承了儒家忠义、德性修养的德教传统,并且将这种道德精神与悍直气质结合起来,从而表现出特别突出的忠节、义勇的精神气质。
明清两朝,湖湘士人群体不仅仅是规模大大拓展,达到历史上的最盛,而且在学术上、政治上的地位达到空前的高度,已经成为全国士人群体集中的重要区域。与魏晋、唐宋时期相比,湖湘士人的精神气质一脉相承,并且表现得更为突出。明清时期湖湘士人精神气质表现在数百年的历史长河之中,这里首先例举明清之际以王夫之为代表的士人群体。王夫之是一位典型的将儒生的道德情操、精神信仰与南蛮的劲直任气、慓疾尚勇结合的湖湘士人。其儿子王敔在《大行府吾君行述》中描述其精神气质时,说他“天性肫挚,见机明快”“忠义激烈,而接人温恭”,其“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的自撰联语,更是将儒生的文化使命、精神追求与南蛮的劲悍血气、刚强意志表达得淋漓尽致。其实,与王夫之交往的一大批湖湘士人均具有这种精神气质。现从罗正钧的《船山师友记》例举一些与他交往密切的湖湘士人,诸如:
管嗣裘,字冶仲,衡阳人。其“少英爽,有文名”。“广西陷,匿临川山中,冬月负败絮,觅苦菜以食。与刘远生、刘湘客、朱昌时行吟溪峒中,以死自誓。”
夏汝弼,字叔直。“性倜傥,负劲气,与王夫子兄弟友善。”“明亡数十年,遗老旧臣,佯狂遨游,居衡湘者尤众。……其终隐九疑以饿死云。”
刘惟赞,字子参,祁阳人,崇祯已卯举人。“性刚介尚气。癸未之乱,与衡州同知郑逢元督义勇,歼贼魁。国变后,以中书屡征不就。”
陈五鼎,字耳臣,攸县人。崇祯朝贡生,官耒阳教谕。“耳臣性狷介,刻苦自励。无子。乱后隐居深山不出。”
李国桐,字敬公,衡阳人。“性醇挚,外和内刚。”
在这些与王夫子交往密切的湖湘士人群体中,他们的精神气质大多与王船山十分接近,一方面具有“劲气”“刚介尚气”“狷介”“刻苦自励”“内刚”的气质,另一方面又受到儒家道德义理熏陶而表现出对忠义德性、精神人格的追求。
从晚清到近代,是湖湘士人群体规模最大、成就最辉煌的时期,同时也是他们的精神气质表现得最为充分的时期。其最为典型的莫过于湘军将领。湘军是一支由“士人领山农”而建立起来的队伍,湘军的将领主要是一大批由进士、举人、秀才等出身的士人充当军队的各级将领。作为儒生、士人,他们均受过很好的儒家文化的教育,故而对儒家的道德价值、人格精神极为推崇,湘军的主要将领如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罗泽南、郭嵩焘等人,均是儒家道德及其精神人格的典范。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均有湖湘蛮族的气质,故而特别张扬一种“别于中原人物而独立”的气质与个性。曾国藩大力倡导的“刚气”“倔强之气”“刚直保真”“明强为本”“血性男人”等,郭嵩焘强调“气盛”“赖”“特立独行”等,其实均是这种南方蛮族气质的传承。湘军将领既是湖湘士人精神气质的典型代表,同时又对后来崛起的湖湘士人群体,起到很好的导范作用。在近代史上事功卓著、人格光彩的一大批湖湘士人,从维新运动的谭嗣同、唐才常、沈荩,到辛亥革命的黄兴、蔡锷、宋教仁、陈天华等,无不表现一种将道德观念、精神人格与刚直个性、蛮性气质的结合。所以,杨毓麟所说的“湖南人之性质”、陈独秀所说的“湖南人底精神”等,均是从这些湖湘士人的精神气质中概括出来的。
三、湖湘士人的二重文化基因及其组合
湖湘士人的精神气质与这个地区的“民性”与“士风”均有关联。“精神气质”是某一族群、地域等社会群体的“文化--心理”特质的概念,包括道德的、审美的、宗教的“精神”层面和生理、心理的、习俗的“气质”层面。而湖湘士人的“文化--心理”特质所体现出精神层面和气质层面,有着“民性”与“士风”方面的不同来源。
一方面,湖湘士人“气质”方面的心理文化,是以本土的“民性”为来源与基础。由于自然地理、血缘遗传、人文历史的综合原因,湖南地区形成一种特有的民性、民风。这就是历朝的历史典籍、地理方志等书上所描述的湘人的性格、气质,即所谓的民性、民风,即史志上所反复说到的“劲直任气”“人性劲悍”“任性刚直”“刚劲勇悍”“其俗慓悍”等。虽然由于移民、交通及文化教育等原因,湖南的民性、民风在一些局部地区有所改变,但从总体而言,即使到了近代,这一民性、民风的格局仍得以保存。民国初年湖南调查局曾作过一个湖南民情风俗的调查,其结论是:“湘人之特质,总之不离乎劲悍决烈,忍苦习劳者近是。”“西南之民刚而朴,其失也悍。”这种“劲悍决烈”“忍苦习劳”的民性、民风是源于湖湘本土的文化传统,可由明清时期湖湘民俗文化、心理文化,上溯到汉晋以来的“诸蛮”、战国时代的“楚蛮”与上古时期“苗蛮”。
另一方面,湖湘士人“精神”方面儒家道德文化。在古代中国,士人一直是中国传统精神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学术的承担者与传播者,儒学的价值信仰、道德观念、政治思想,主要是通过一代代士人的承担与传播而发挥其基本的社会功能。儒家文化本是起源于齐鲁的区域文化,经西汉时期的“独尊儒术”政策后成为统一中国的意识形态,但是直到晋唐之时,儒家文化在湖南的影响仍是十分有限。宋代以后,中国的文化重心南移,湖南的文化教育逐渐发展,儒家文化才有了进一步的推广、普及,最著名的例子是四大书院之一的岳麓书院的创办。唐末五代时期,因有人“念唐末五季湖南偏僻,风化陵夷,习俗暴恶,思见儒者之道,乃割地建屋,以居士类。”这是岳麓书院正式建院之前的状况。北宋初年,经过一些儒家士大夫的努力,岳麓书院已经成为一所闻名全国的著名书院,在儒家文化的传播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以至于著名学者王禹偁赞扬说:“使里人有必箿之志,学者无将落之忧。谁谓潇湘?兹为洙泗。谁谓荆蛮?兹为邹鲁。人存政举,岂系古今?导德齐礼,自知耻格。”这段话说明,岳麓书院的文化教育既是“潇湘”与“洙泗”的地域文化的交流融合,也是“荆蛮”的民性、民俗与“邹鲁”士风的文化结合。
其实,自两宋以来的儒家士大夫,无论是湖湘本土的学者,还是流寓湖湘的士大夫,他们一个重要文化使命是“化民成俗”,将儒家的礼义文化传播到这个“风化陵夷、习俗暴恶”的“潇湘”、“荆蛮”之地。但是,许多有见识的士大夫亦意识到,湖湘本土的“民性”与中原传入的儒家礼义并不完全是对立的,而是可以将两者融合起来的,如明代士大夫倪岳说:
“予闻长沙为郡,……其士习则好文而尚义,其民性则决烈而劲直。故习之相近,固多问学志节之风;而性之所染,亦多豪犷桀骜之态,往往健讼之日闻而逋赋之岁积。”
他和许多士大夫的理想一样,希望保持这一“士习”与“民性”的融合,即盼望将这种“士习”化入“民性”之中,即所谓“敦礼师儒使居其间,以教郡邑之俊秀,将见贤者汇兴,风俗必变,因以化导其乡之人,以复昔时所称,人多纯朴,俗耻不义。学者勤于礼,耕者勤于力……翕然湖湘文献节义之盛。”
经过这种“民性”与“士习”的渗透与融合,湖湘之地确是成长了一大批成功将劲悍的民性与礼义的士气结合的湖湘士人群体。从明清到近代,一批批湖湘士人的精神气质,总是将儒家的道德、审美等精神文化渗透到其“南蛮”的心理气质层面。儒学向来重视人格修炼,南下的理学强化了这一精神修炼的传统。湖湘理学的精神修炼与湘人气质性格的结合,产生了湖湘士人的“精神气质”。譬如,湘军是由“儒生领山农”构成,曾国藩对领军的儒生有一些完全属于“精神气质”方面的要求,即所谓“书生之血诚”“大抵有忠义血性”,“血性”是属于以生理心理为基础的气质性格,“诚”“忠义”则是以儒家道德修身为基础的精神文化,两者的渗透与结合,构成了湘军将领普遍追求表达的“忠义血性”的精神气质。曾国藩在总结民间武装的湘军最终能够取得国家军队八旗、绿营所不能完成的平定天下的成就时,认为与湘军将领普遍具有的独特精神气质有关。他说:“吾乡数君子所以鼓舞群伦,历九载而勘大乱,非拙且诚之效与?”所谓“拙诚”,是一个与“忠义血性”类似的概念,表达的正是湘军将领的精神气质,其“诚”源于中原儒家的道德理念,是精神方面的;而“拙”则源于南楚蛮族的血气民性,属于气质方面。曾国藩能够非常准确地使用这些概念来表达湖湘士人精神气质的二重组合。
如果我们深一层考察湖湘士人的精神气质,均可以发现其内在组合上的一些特点,就是他们的内在人格、精神气质中,往往具有一种两极现象,就是将两种十分不同、甚至是十分对立的心理的、精神的文化现象融为一体。譬如,人的道德理念与自然血气在内心世界总是十分对立的,根据儒家的修身理论,一切士君子的修身过程与目标,就是要用道德理念去压抑、克制自然血气。但是许多杰出的湖湘士人却能够将其德性修养与血气拓展统一起来,成就为一种“拙诚”“明强”“忠义血性”的精神气质。“狂”与“狷”亦是十分对立的人格与气质,但湖湘士人中偏偏产生较多的“狂狷型”精神气质,既有狂者精神,又有狷者特质,表现为一种既狂又狷的独特人格。其实,湖湘士人的这种相反相成的精神气质特征还表现在许多方面,包括既有“虎气”人格,又有“猴气”人格;既有浪漫理想,又重实际事务;既是正统的维护者,又是反对正统的叛逆者;既有悲情心理,又有豪迈激情;既是崇文的书生,又是尚武的将士;既有成就圣贤的精神追求,又有开拓豪杰事业的政治志向等等。这就使得湖湘士人的精神气质呈现出一种多姿的风貌和多彩的景象,尤其是在动荡的政治变局和痛苦的历史转型,更是将这种相反相成的精神气质特质表现得淋漓尽致。
湖湘士人的精神气质之所以会呈现出这种相反相成的两极现象,毫无疑问,这是不同文化基因组合的结果。如果对湖湘士人的“精神气质”作一解构,可以发现,其文化基因的组合是别有特点的。本来,“精神气质”的概念就是道德的、审美的精神文化与生理的、气质的心理文化的结合,是一种不同文化因素组合而成的人格现象。而“湖湘士人”的主体是“士人”,其精神气质则是将“民性”的社会心理文化与“士风”的人文精神文化结合起来,体现出这一社会群体的文化特质。又由于这种士人群体特指“湖湘”地域,湖湘士人的精神层面的文化,其主要文化基因来自中原的儒家学说,而其心理层面的文化基因主要又来自南蛮的民性民俗。这样,湖湘士人的精神气质就是一种多重文化基因的组合,即心理文化与精神文化、民俗文化与士人文化、楚蛮文化与中原文化等多重文化的组合。这些不同文化基因组合的直接结果,就是湖湘士人的精神气质呈现出德性与血气、狂傲与狷守、崇文与尚武、浪漫与实际、虎气与猴气等不同文化人格合于一身,体现出一种两极性文化特质既相反又相成的奇特文化景观和精神气质。
更加重要的是,这种不同文化基因的组合,强化了传统儒家文化的文化活力,使得晚清以后缺乏文化活力的儒家文化能够继续充分发挥其文化功能;同时也进一步激化了士大夫精神的文化活力,使得儒家士大夫的德性文化、理想人格仍成为清朝、民国时期社会变革的主体力量。晚清以来,儒家士大夫面临严重的文化困境,这既包括中国文化与西方文明的冲突,即儒家的德性文化、君子文化与西方列强的尚力文化、蛮性文化的较量;也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内在活力的损失,居于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理学文化呈现道德虚伪、思想空疏而不切实际的严重弊端。湖湘士人的精神气质中出现的将儒家德性修养与蛮族血性结合、文化理想追求与切实社会行为结合,故而从这种文化困境中走出一条生路。这种德性文化与蛮性文化的结合,从而可以与西方近代列强的尚力文化、蛮性文化相对抗,不仅是使原本走向空疏,虚伪的理学文化重新获得了精神活力,同时也培养了一大批改变历史、推动中华民族走向独立、富强的“圣贤豪杰”。 (作者系本馆馆员)
注释:
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纳日碧力戈等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8页。
明万历《慈利县志》卷十二。
《史记》卷四十,《楚世家第十》。
今本:《竹书纪年》卷下,《宣王》。
陈戍国:《诗经校注·采芑》,岳麓书社出版社,2004年版,第220页
《史记》卷二十三,《礼书第一》。
《史记》卷五十五,《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史记》卷一百十八,《淮南衡山列传》。“予闻长沙为郡,……其士习则好文而尚义,其民性则决烈而劲直。故习之相近,固多问学志节之风;而性之所染,亦多豪犷桀骜之态,往往健讼之日闻而逋赋之岁积。”
《隋书》卷三十一,《地理下》。
《方舆胜览》卷二十三,《湖南路》。
《金文靖集》卷七,《赠欧阳太守长沙序》
李学勤:《十三经注疏》第6册,《礼记注疏》卷十二,《王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98页,。
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张伟然:《湖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41页。
杨毓麟:《杨毓麟集》,岳麓书社,2001年版,第35页。
陈独秀:《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离骚经》,《船山全书》第14册,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220页。
均见《晋书》卷八十九,《列传第五十九》。
《宋史》卷四百零三,《赵方传》
《宋史》卷四百十六,《胡颖传》
《宋史》卷四百五十,《李芾传》
《宋史》卷四百五十,《尹谷传》
《宋元学案》卷七十三,《元城学案》。
罗正钧:《船山师友记》,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44页。
罗正钧:《船山师友记》,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68页。
罗正钧:《船山师友记》,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87页。
罗正钧:《船山师友记》,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118页。
罗正钧:《船山师友记》,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97页。
湖南调查局编:《湖南民情风俗报告书》(民国元年)湖南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
欧阳守道:《赠了敬序》,《巽斋文集》卷7。
王禹偁:《潭州岳麓山书院记》,《小畜集》卷17。
[明]倪岳:《清溪漫稿》卷十九,《赠长沙府知府王君赴官序》。
[明]倪岳:《清溪漫稿》卷十九,《赠长沙府知府王君赴官序》。
《书信一》,《曾国藩全集》 卷,第76页。
《书信一》,《曾国藩全集》 卷,第224页。
《诗文·湘兮昭忠祠记》,《曾国藩全集》第14册,第304页。
【湖湘士人的精神气质与文化基因】朱汉民2021年3期总125
2021-08-04 15:27:24 来源: 评论:0 点击:
分享到:
相关热词搜索:
上一篇:【探路时期社会主义思潮的译介与传播】梁颂成2021年2期总124
下一篇:【东汉时期长沙郡太守简述】潘淑萍 蒋波2021年3期总125
分享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