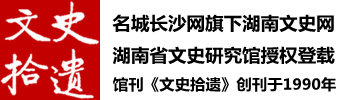时务学堂故址
19世纪末创办于长沙的湖南时务学堂在湖南维新运动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以教育改革为中心,促进了湖南的近代化。学界对湖南时务学堂的历史多有研究,曾经发表了专以时务学堂为主题的论文十余篇,在有关湖南维新运动著作中,又有评述时务学堂的章节。但尚无研究的专著问世,2015年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了由郑大华教授主编的《湖南时务学堂研究》一书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湖南时务学堂研究》一书(以下简称《研究》)系统的论述了时务学堂创办的背景,创办的经过,开展的教育改革,引起的纷争,作用与影响。执笔的作者对时务学堂素有研究,取得不少成果,《研究》一书重建了对时务学堂的完整的认识,堪称一部力作。
《研究》一书在学术史的回顾中地毯式的搜索了历来的有关研究成果,然后,将这些成果加以消化,整理,从而提出需要研究的重点问题和难点问题。《研究》一书充分占有了多种原始资料,有些是过往研究者,没有充分掌握的,这样便使研究有了深厚的基础。
《研究》一书作为一部取得新成果的学术著作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新的突破:
第一,将时务学堂的创办置于湘学发展的大背景中加以考察。《研究》一书对湘学发展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论述(见第一章),从中我们可以认识到时务学堂的创办渊源深远,它是湘学发展的必然结果。《研究》一书揭示了近代湘学有三个特征: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精神;求新、求变的变革精神;重实践的经世致用学风,这三个方面是湖南维新运动兴起的重要条件,也是时务学堂的兴办的三大思想支柱。正如作者指出的:“如果没有强烈的经世观用欢和浓厚的政治意识,就不可能出现被视为晚清维新派人才摇篮的时务学堂。”(《研究》一书第38页)
第二:人们在考察时务学堂时,必然对其校舍的情况有兴趣,希望了解。《研究》一书第二章附有“时务学堂校舍形制考”,满足了这一希望“形制考”是作者实地考察,访问有关人员和参考回忆录写成的,后来以此为根据写出《关于建立时务学堂纪念馆研究报告》,提交长沙政府,作为文化建设的参考,做到了历史研究为市政建设服务。
第三,全面准确地论述了时务学堂的教育改革,将改革分为教育宗旨,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学业评价六个方面。在具体论述前将有关概念进行了确切的界定,澄清了模糊的认识。指出“教育宗旨一直和教育方针,教育目的,教育目标等概念纠缠不清,取宗旨而舍其他,是因为‘方针’,只表明方向,‘目的’又偏重眼前,而目标又可拆分近期和远期,只有‘宗旨’既兼顾了上述内容又具有灵活性。”(《研究》第121页注①),关于课程设置《研究》论及的对象既指某一门学科,又指学生在校所学的学科和及其进程及安排。(第126-127页)关于教学方法,包括教学组织形式教师的教学方法和学生学习方法(第153页)。如此界定使有关记述清晰明了,并且全面。
在分述了时务学堂的教育改革内容之后,《研究》一书,概括指出其重大意义,是湖南维新派为了救亡图存,实行救国,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启蒙教育相结合的一次伟大实践。虽然时间短暂,但内容极为全面,涉及教育宗旨、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学业评价等方面,是一种不同于旧式官学和书院的新的教育机构,开启了湖南乃至全国教育由传统向近代全面转换的先河。(第175页)这样的结论精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四,关于时务学堂引起的纷争,《研究》一书写得十分精彩,颇具新意。这一纷争是一个复杂交错的问题,以往学者在研究时,往往加以简单化,只粗线条的进行分析。《研究》一书展开了多元化,深入细微地研究,摒弃了“新与旧”二元绝对对立的观点,明确提出不能将有关人物脸谱化,线形化,凝固化。
时务学堂引起的纷争主要在官绅阶层中展开的,因此对他们言行的细微的分析,有助于揭开纷争的内幕。在以往的研究中多把参与纷争的人物划分为左、中、右三派这种划分基本上符合历史实际,从有关人物的思想倾向,呈现为激进与保送中间三大派,但是有关人物的思想往往是复杂变化的,在研究中很难做出截然的划分,《研究》一书根据这一实际情况,细微将纷争中有关人物确定持六种态度(或称六种派别):
以梁启超、谭嗣同、熊希龄、樊锥和一些激进学生为代表的激进维新派
以叶德辉、苏舆和安于现状的绅士为代表的顽固保守派。
另有属于两大派之间的中间势力,他们后来发生了变化,形成了以王先谦,张祖国一批绅士,由原本支持新政,逐渐走向保守。
以陈宝箴、陈三立、欧阳中鹄等为代表的官绅,始终摇摆于维新与保守之间,他们倾向于温和改革,当保守势力甚嚣尘上时往往退让,妥协,进行调和的努力。
以黄遵宪、徐仁铸、江标、皮锡瑞为代表的官绅,比较偏向于维新改革。以邹代钧、李维格、李经羲为代表的官绅,偏向于保守派。
《研究》一书摒弃了“新与旧”二元绝对对立的观点,明确指出:维新派与守旧派在政治上虽然有所不同,但由于共同的区域文化的背景又表现出一些相同的学术特征:如推崇实学,崇尚经世致用。推崇理学的文化传统。(第38页)。
《研究》一书还发表了下面的一些中肯的见解:甲午战争以后,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朝野要求改革的呼声愈来愈高,维新变法基本达成国人的共识,真正纯粹的保守派几乎已不存在,然而,不同派别、不同背景、不同身份的人,对于变什么,怎么变等问题,并不是完全一致,毫无芥蒂之分的。(第207-208页)
在新旧关系上,(守旧派)叶德辉重拾经典教异的“温故知新”的原则,体现了对传统的尊重为延续,自有其合理性。他对康有为的批判也很有预见性。康有为为了尊孔而保教,为了保教而改教,而这种改教,最终又导致了儒学价值体系的崩溃。那么,究竟如何做到温故而知新建设一种新、旧两不误,有益于时代进步的新学,叶德辉没有提出具体而微的策略思路。(第242页-243页)
《研究》一书研究时务学堂引起的纷争是一大亮点,评述,引进了国内外学者有关新的研究成果,新的观点:①新旧两派不是截然对立;②不能将文化取向与政治取向混为一谈,③“圣化构想”与“悲观构想”互相冲突等观点,这些观点的引进,发人深思,有助于转换研究视角,为时务学堂研究提出了新问题,开辟了新领域。
由于《研究》是第一部研究时务学堂的专著,不可能十全十美,笔者大致通读这部著作之后,发现存在有以下三方面的问题,兹提出供参与。
一、 论述上的缺点
《研究》一书缺少时务学堂办学时借鉴万木草堂办学经验的论述。光绪十七年(1891)康有为在广州长兴里设立了万木草堂,它是一所培养维新变法人才的新型学校。梁启超曾就读于此校,后来梁启超在兴办湖南时务学堂时曾借鉴过万木草堂的教育宗旨和教学方法。
时务学堂十分注重“以政学为主义”的教育。为什么时务学堂十分注重“以政学为主义”的教育呢?这与任中文教习的梁启超的教育思想分不开。梁启超是“西政教育”的积极倡导者,他的老师康有为在广州万木草堂讲学时也非常重视“政学”教育,这对其弟子影响很大。梁启超既继承了万木草堂“政学”教育传统,又在其基础上有所发展。
梁启超认为“政学”乃治国大道,用途甚广,见效甚速。他是继康为之后最明确提出“以政学为主义”的教育思想家。他曾指出:
“今日学校,当以政学为主义,以艺学为附庸。政学之成较易,艺学之成较难,政学之用较广,艺学之用较狭。使其国有政材而无艺材也,则行政之人,振兴艺事,直易易耳。即不尔而借材异也,而客卿而操纵之,无所不可也。使其国有艺材而无政材也,则绝艺虽多,执政者不知所以用之,其终也,必为他人所用。今之中国,其习专门之业,稍有成就,散而处于欧、墨(美)各国者,固有乏人,独其讲求古今中外治天下之道,深知其意者,殆不多见,此所以虽有一二艺材,而卒无用也。”
在时务学堂,梁启超把康有为当年在万木草堂的教学方法加以运用并发扬光大,他把书籍分为专精和涉猎二类就是继承了康有为的方法。梁启超说:“学者每日不必专读书,康先生之教特标专精涉猎二条,无专精则不能成,无涉猎则不能通也。”《研究》一书对这些论述的情况,不知为何只字未提?看来,关于时务学堂办学时对万木草堂的借鉴,这一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二、 史料上的疏漏
《研究》一书广泛的挖掘与搜集了有关史料,但笔者发现仍有疏漏,现将疏漏的有关史料补充如下:
1.唐才质:《追忆蔡松坡先生》(节录)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冬,湖南时务学堂成立,余与松坡同时考入,始识松坡。当时同学中,在我脑中印象最深者,为虎村(李炳寰字虎村,庚子武汉起义殉国)、松坡二人。虎村年长于余,且同住一宿舍,意气投合,遂换帖为兄弟。松坡在同班年龄最小,体质亦复文弱,初不为人重视,然而言论见解,有独到之处,乃知年少好学,根柢甚为深厚也。
松坡原名艮寅(后来投考日本士官司学校,乃改名锷),湖南邵阳人,松坡其字也。生而颖异,年11,补弟子员。母舅樊锥,博学多能,在邑中有才名;松坡请之游,学业益有进步。丁酉冬,松坡应考时务学堂,名列第三;在堂每月月考,皆居前列。英气蓬勃,同学皆敬慕之。
松坡在堂,所居余辈斋舍接近。课余之暇,必过余言学论政。谈到当前政治败坏,声情激越,决心贡献自己一切力量,以挽救国难。
按察使黄公度(名遵宪)与时务学堂同学联系密切,常约吾辈往官舍谈话,娓娓不倦,态度和蔼,无官场习气。公度在湘仅一年,旋以戊戌政变去官,养疴海上。翌年即归嘉应故里。其己亥怀人诗即是时作,内有怀李炳寰、蔡艮寅、唐才质云:“谬种千年兔园册,此中埋没几英豪。国方年少吾将老,青眼高歌望尔曹。”其期望与勖勉吾辈为国致力,情意至为殷切。
戊戌8月政变,新政尽废,时务学堂亦有趋于解体之势,学生多愤而退学。余与松坡、静生(范源濂字)亦与焉。吾侪商榷之结果,决定继续求学,以求深造。顾是时国内研究实学之学校,寥若晨星。武昌虽有两湖书院,院内事务,多半为旧派掌握。政变之后,对于湖南时务学堂之退学生,拒不接纳,南京亦无学校。于是吾侪不得不以上海为目的地。已亥夏5月,松坡与余辈同考入上海南洋公学。时值暑假,幸前时务学堂英文总教习李维格先生,在该校任教,特许先入宿舍。7月,梁启超自日本来函相招,又得家兄才常先生资助,遂东渡。
松坡与余到日本后,其他时务学堂学生,继续冒危险经上海而抵东京者,并余等共为11人。梁在东京小石川久坚町,租赁三间房屋,让吾辈居住,为投考日校作准备。此是时务学堂解散以后,余与松坡在上海、东京二处,又得继续处求学,约为一年左右。物质生活方面,虽然甚苦;但精神方面,异常愉快。
庚子(1900年)春间,家兄才常先生决意在武汉起义,军事部署,略已就绪。当时时务学堂同学来到东京11人中,除松坡愿留日本学习陆军,静生愿研究学术,致身教育以外,余皆回国参与其事。同学既行之后,松坡心不自安,旋亦毅然变计,只身回沪转汉,参与武汉起义。才常先生以松坡在同学中年龄最幼,暂不欲其担任艰巨以误学业,即函介赴湘见黄忠浩,面商机要,要求在武汉发动之后,同时在湘起义,以相策应。黄原在湘训练新军,此时正奉令移鄂。黄认为才常先生所谋,目的虽对,方法不行。结果无数青年志士,白白牺牲,未免可惜。于是挽留松坡商论数日,未即遣行。未几自立军起义失败,松坡尚留黄寓,因而得免于难。黄仍送松坡赴日留学,以图上进。
唐才质系唐才常之弟,也是时务学堂学员,此文写于20世纪50年代,关于蔡松坡在时务学堂、唐才质在他写的《唐才常和时务学堂》一文中也有记述,但与此文有所不同。唐才质这篇追忆,引述了黄遵宪1899年所写的诗作中对李炳寰等人的赞颂,尤为珍贵)
2、曾是时务学堂一班学员的杨树达在时务学堂停办后写的《积微翁回忆录》一书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对时务学堂的人和事多有追忆见:1927年9月5日所记;1927年12月25日所记;1929年1月19日所记,1929年2月15日所记;1944年1月23日所记;1937年7月7日所记;1953年6月3日所记。其中1927年12月25日记有祭联|《挽范君静生》(即挽范源廉)败而死李君抚生,成而死有蔡君松松;吾党纵多才,非公谁与抗手?不令子为汉之孟博,而令子为宋之希文;造物岂无意,胡为天不假年?
1929年2月15日写有《时务学堂弟子祭任公师文》
文中开头部分记述了任公师从康有为的业绩,继之赞颂了开办时务学堂的成就:“惟我楚士,闻风激扬,乃兴黉舍,言储栋梁,礼延我师,自沪而湘。济济多士,如饥获粮,其诵维何?孟轲公羊,其教维何?革政救亡。士闻大义,心痛国创。拔剑击柱,踊跃如狂。夫子诏我,摄汝光芒。救国在学,乃惟康庄。”接着又称赞时务学堂,培养俊秀的贡献:“松坡崛起,折彼鲸狼。温温范君(范源廉)邦教是倡。民智之兴,劂绩辉煌。凡此诸彦,师教之倡。”
1944年1月23日记有《赋诗寄呈时务学堂导师韩树园,(韩文举)兼任公师》
故都侍坐几经年,忽道黄巾拜郑玄。
炊甑生尘明德在,凭庑作计好歌传。
少年不贱余青简(谓同门李抚生蔡松坡),命世无文对白颠,凄凄绝牙琴弦又断,一篇诗就愧空前。
(任师见余盐铁论注序)谬许空前之作。
3.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中的所见
李提摩太(T.Richard 1891-1919)于在华回忆录中两次提到湖南时务学堂,一次是在记述湖南维新运动过程时,提到1897年梁启超在长沙担任一所改革派开办的学校的校长,这里所说的学院当为时务学堂。另一次李提摩太在1914年所记的“湖南首府长沙”曾提到1896年,广学会最著名的作者被长沙一所由改革开办的学院邀去给学生做讲座。这里提到的学院当时为时务学堂。按广学会为西方传教士在华所办的出版机构,李提摩太是主要的工作人员。李提摩太所记的讲学学者是何人,讲学的内容待考。从李提摩太所记,可见时务学堂曾引起西方传教士的注意。
三、史实上的错误
1、关于评述时务学堂学员蔡锷生平的多种论著,皆称蔡氏系学堂中年令最年轻者,《研究》一书也从此说(见第103页)。此说大概首见于唐才质写的《追忆蔡松坡先生》一文,此后从讹传讹,实际上与蔡同班的杨树达生于1885年,而蔡生于1882年,据此,当然杨比蔡年轻,不能称蔡系最年轻的学员。
2、很多论著皆称樊锥是蔡锷的母舅,《研究》一书也从此说见103页,这种说法大概也首见唐才质的《追忆蔡松坡先生一文》。我们只要考察一下蔡氏母亲的生平即可证实,此说不确。据考证,蔡母本是弃婴,后被一位王家老人收养,因此也就姓王了。她和蔡的父亲蔡正陵结婚,家境生活困穷。蔡父将松坡就学于著名学者樊锥,时年十三(很可能有人把他十三岁这个年龄误认为是考入时务学堂的年龄,因此把松坡称为时务学堂最年轻的学员。综上所述樊锥不可能是松坡的母舅。(关于蔡母王氏的生平见《蔡锷的母亲》一文,载蔡瑞编《蔡锷集》,转录于田福隆主编《忆蔡锷》一书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120-123页。
3.《研究》一书第84页辑录了三首时务学堂开办时的贺联,第一首是:
延湖海英雄,力维时局。
勖沅湘子弟,再赞中兴。
《研究》一书说此联系谭嗣同所撰,这一首贺联,据诗联研究家吴恭亨(1857-1937)亲见系熊希龄所撰,并注明熊氏所撰的另两首是“七言”,“八言”,这一首是“九言”,另据吴氏所记,这一首的第一句为“延湖海英豪”,不是“延湖海英雄”。(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