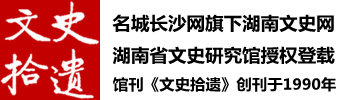20世纪30年代雅礼中学校园
“Bulldog, Bulldog. Rah Rah Rah. Eli Yale”,我不是上星期在纽黑文(New Haven)耶鲁与哈佛的比赛中听到耶鲁人的战歌,而是六十七年前即1936年在中国长沙听到的。
一、传教士和耶鲁学士
我与耶鲁学士(Yale Bachelor)有过交往。需要解释的是,他们是刚从耶鲁毕业的学生,毕业后第一年或有时是第二年志愿去雅礼教书。他们没有工资,而是由他们的同学们资助。那个年代共有超过七十人的耶鲁学士去中国工作过。我深信不疑,当他们回忆人生经历时,这些年轻人在中国的工作时光就像他们生命中的珍宝。当我1936年在雅礼时,耶鲁学士奥斯卡•兰德(Oscar Rand)教我们英语。就在1945年战争结束后,我在上海又遇见了奥斯卡。他当时是一个穿着挺刮制服、在美国太平洋舰队中一支舰队的旗舰上工作的英俊海军军官,而我是一个充满去美国读研究生雄心的大学毕业生。我和父亲、兄长们与他吃了一顿饭。我们问他什么是他在战争期间最难忘的时刻——这个问题意在分享他在战争中令人兴奋的事。他说那是在麦克阿瑟打回菲律宾,他的舰队在莱特岛登陆,以及当两支日本舰队夹击莱特岛的时候,那时绰号叫“公牛”的哈尔西正在追赶日本的诱敌舰队,这使得美军登陆部队没有防备并易受攻击。如果日军得逞了,美军登陆部队将面临灭顶之灾,幸运的是这没有发生。
就在我到雅礼不久,看见一个耶鲁学士在和一个中国学生下中国象棋,我凑了上去。因为知道一点如何下棋,我想我应该给这个外国人露两手。我告诉他应该那样下棋,这位耶鲁学士慢慢地抬起头,转过身来,用一个我一直记得的最刻薄的样子看着我。那个时刻,我知道了应该如何看别人下棋。
还有一次,一位耶鲁学士正在给一些中国学生示范玩橄榄球,我在边上看着。一位学生试图拍橄榄球,但它弹歪了,这位耶鲁学士喊道:“不,不,不,不要拍球”。
另一位耶鲁学士舒乐•坎门(Schuyler Cammann)对中国考古学感兴趣。在湖南,有许多土堆,即中国的坟墓。因为有时一些有价值的财宝埋在里面,盗墓者(长沙话叫土夫子)寻找它们然后偷偷地在晚上干活。正如坎门指给我看的,我在远处看到一些夜光。他说大多数时候土夫子仅仅发现一些小的工艺品,比如一个倒扣、里面装着一只小猪的陶碗。这在中文里意为“家”,也就是我名字里的那个“家”,即屋顶下有一只猪。有时他们发现如雕刻物品之类更有价值的东西(后来,长沙市地方当局谴责坎门偷中国的财宝。1960年代,坎门是费城宾州大学东方研究系的教授,我又与他取得联系,之后我们成为多年的朋友)。
“这些由耶鲁学士产生的结果不是偶然的,一些最优秀的耶鲁年轻人的生命力已经进入了耶鲁”。雅礼协会早期的先驱赖德烈(Kenneth Latourette)如是说(摘自鲁本•候登(Reuben Holden)的传记《雅礼协会在中国大陆:1901-1951》(Yale-in-China: The Mainland 1901-1951)。
我们仅与教会直接接触了几次。有一次,我的兄长和我跟俞道存先生(Dwight Rugh)——后来担任雅礼协会驻长沙的代表——的夫人俞婉瑛(Winifred Rugh)女士学习钢琴。他们有一个小女孩,我想现在该是七十多岁了。对于没有父母压力就没有什么兴趣练琴的小孩来说,我没有学到太多的钢琴知识。
有一天应开识主任叫我和两个兄长从教室出来见见一位教会的女士,她想给我们兄弟——第二代雅礼人、父辈是著名足球明星的三个儿子——拍一张照片。她拍了照片,之后我在一本出版物上看到这张照片。
二、校园里的特别事件
在初中部,我们有一门每星期晚上上一次的特殊兴趣的选修课程,比如合唱团或新闻讨论课。我选择了后者。领头的是高年级学生,他们听短波,然后给我们低年级学生讲解新闻。一天晚上,有一位高年级的学生使了个眼色笑着说:“今晚我们将讲一些浪漫的事情。英国国王刚刚辞去王位,他将和一位离异的美国妇女结婚”。
也有一些紧张的日子。据报道,我们的领袖蒋委员长由于一些那时我还不太理解的原因被张学良将军软禁了,这就是后来所知道的蒋介石在西安被张学良扣留的“西安事变”。共产党方面想让蒋介石与共产党一道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后来有一天晚上上自习时,学校要求所有学生在室外操场集中等待收听电台通知。不久,高音喇叭播报了一个特别的新闻:“搭载蒋介石和其夫人的飞机刚刚安全降落在南京机场,他们安然无恙”。学生们大声地喊叫着,接着劳校长宣布游行庆祝。学生队伍分几队蜿蜒而出,唱着、喊着,一些人用两根棍子敲着鼓,我敲着一面大鼓——咚咚咚、咚咚咚——因为这是行进的节奏,所以对我来说并不难。我们最熟悉、最有激情唱的歌是“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这可能是众人最爱唱的中国抗战歌曲了,这首歌曲现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我们还放了好多爆竹,其他学校也在游行。我看表注意到,我们在长沙的主要街道上游行了一个半小时。等我们返回校园,全城放爆竹所形成的白烟离地大约有六英尺高。多年后当我在西安时,中方东道主陪同我看一处标注着胆怯的蒋介石试图逃跑却被抓住的地方。
湘雅和雅礼之间曾有一场足球赛,这将决定谁代表湖南参加全国足球比赛。比分是零比零,但我们认为裁判吹掉了雅礼一个应有的得分,劳校长下令放爆竹以表示抗议和庆祝我们非正式的胜利。
有一次整个学校去长沙西边的岳麓山郊游一天,所有学生和教职员工都去了。要到那里去,我们先得步行,然后乘船或游泳渡过湘江。我在江里游了一段,水很清,几乎都可以喝,其中一个原因是这是上游的水,那时几乎没有什么工业,所以没有被污染。我看见食堂的师傅们用结实的竹竿挑着盖着盖子的大篮子,里面装着我们喜爱的蒸馒头。我们在那里玩了一种叫“龙球”的游戏,两队的许多男生举手撑着一个直径至少四英尺的大球,他们的任务就是将球在空中推向对方那边,高中生和初中生进行比赛。“跳、跳”,老师们在边上高喊着。作为一个小孩,我跳起来只能勉强碰到球。猜猜哪个队赢了?当然是高中生。这正是雅礼教育目标中希望培养健康和个性的气氛。
有一天晚上突然有一大群白蚁在我们教室里绕着灯泡飞。宿管员在灯泡下面放了一大盆开水用来淹死白蚁。第二天,我看到一个白蚁侦探在干活。他在教室外面挖出一些土,里面有许多小地道。他用一根草仔细地插到一些地道里,然后每次都闻了一下草的味道。有一次闻了以后,他指着一个方向告诉站在旁边的助手:“挖”,果然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白蚁窝,他们迅速铲掉并烧毁了它。从此以后,我们再也没发现白蚁了。
三、在长沙的课外生活
还记得我父母相识之地、长沙富裕的陈氏家族吧?我父亲的同学陈乃勋也有一个与我们年纪相仿的儿子,他也在雅礼上学,因此我们三兄弟跟父亲一样经常在周末到他家玩。因为他家的房子是在长沙的南端,所以我们得从城北穿过城中。这样的话,我们先得进老城门,然后经过铺着鹅卵石的主大街,它光线不好、并且是如此的狭窄,以至于在稍宽一些的地段两个轿子刚好能挤着互相通过,这当然是在旧中国了。商店开在马路两边,正如在那个年龄的男孩经常觉得饿,我们常停下来买碗面吃。当我点了他们有名的牛肉汤面时,我学着用湖南话说:“轻挑,重盖”,意思为:“少放些面,多放些牛肉”。我们加了辣椒,它是如此之辣以至于等我们喝完最后一口面汤时,我嘴里在喷火呢。他们说辣椒有助于去除湖南的潮湿。在美国所谓的湖南菜、甚至于现在的长沙菜辣的程度都不能与之相比。
陈家的房子被称为“洋房”,意思是砖结构而不是泥砌的,它有自来水和一口尚在使用的井。我第一次去那里时,我记得我给高我两辈的女族长——陈乃勋的母亲——磕头,对男孩来说这种风俗表示尊敬。在我去长沙前,我母亲告诉我:“当你坐下来在他们家吃饭时,不要去够离你远的菜,舅婆(舅舅的母亲)会将菜夹到你的盘子里”。的确,当我们吃饭时,舅婆用一只颤抖的手拿着筷子将菜夹到我的盘子里。翌年,1937年日本侵略中国,后来日军逼近长沙,陈家逃离了长沙。几年后,陈家人来到上海,那时我们住在那里,他们暂时住在我们家。有一天,一个从长沙来的客人拜访陈家,舅婆打听她们在长沙房子的情况,那人回答说她们的房子在中国“焦土抗战”毁城时烧成了废墟。舅婆又长又深地叹了口气,因为她将值钱的东西藏在房子的墙壁里了。这是旧中国人、甚至今天在美国的一些中国人的思路。
在雅礼读书期间,我在一场足球赛中受了伤——我带着垒球大小的橡皮球(原文如此,可能有误)向前冲,直接撞上了守门员。我在父亲长沙分公司的经理刘先生家养了近一个月的伤。
我母亲从汉口赶到长沙,带我去看当地一名专治跌打损伤的中医。他开了一些中药并将热的加了药的混合物敷在我的膝盖上。大约一小时后,他解开了绷带。哎呦,在一些由于湿热绷带导致有些发白的皮肤上,有许多像天花一样散布的黑点。医生指着黑点说:“这些是毒,现在它们发出来了,你的状况会变好的”。撇开他的诊断不谈,这些年一直困扰我关于中医的问题是那些斑点是什么?它们是如何形成的?(现代医学用拉伤膝盖肌腱来描述受伤,这需要休息来治愈)。
我住在刘先生家里时,有一天有件事很刺激——显然,刘先生在招待一些客户。客厅里放了一张大桌子。刘太太告诉我:“现在你要很安静地呆在卧室,不要透过卧室的帘子向外面张望”。由于好奇,我窥探了几次,这显然是请了几个当地妓院女子的一场晚餐聚会。就像我从小人书里记得的场景,老鸨穿着蓬松的衣服。皮条客安排如何摆放菜肴,然后妓女们很明显是坐着轿子来了。就像一些中国电影中的一样,她们穿着闪亮、新式的大红绿色两段式服装,脸上涂着亮红的胭脂。老鸨指挥着,叫这些人快点等等。后来我又看到十个人按照男女次序依次坐下,桌上摆了许多菜。男人们,其中有些明显是喝多了脸有点红,笑着、吃着,似乎很开心。有一个女人喂给一个男人吃,然后我看到一些男人和女人都不见了,我不知道他们去哪里了。桌上只剩下两对人。最后晚餐结束了,我和刘太太被允许出来。刘先生向他的太太介绍了坐在他边上的女人,似乎这两个女人的脸上都有些尴尬的表情。我多年后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这是在历史书上描述的场景,但现代人可能很少能亲眼看到。
四、从1937年到现在
1936年是雅礼协会的巅峰时期,从那以后,世界在不停地变化。1937年日本侵略中国,之后战线逼近长沙。雅礼协会的机构、人员和学生迁到湖南另外一个地方,并且在困难的环境中继续他们资源匮乏的学校教育,直至八年后战争结束。许多雅礼的建筑都毁了,一些教员战后返回长沙并开始重建校园。
1951年,最后一位雅礼协会的代表俞道存先生被驱逐出境。雅礼改名为第五中学。1966年之后,“文化大革命”来了。雅礼协会与中国大陆的联系被切断了30年。
1974年年届50岁的时候,我碰巧作为中国政府的贵宾访问长沙,那时还是在“文革”期间。中方接待人员不知道我早年与雅礼的联系,有人领我参观以前的雅礼校园,弯弯曲曲的走廊还在那里。我指着走廊旁的一棵树说:“这是我父亲种的”。教室里的学生望着窗外,看我穿着西装,还有随行人员陪着,这是那个年代不寻常的场景。游泳池没有水,废弃在那里。
我问及上学时受人尊重的教导主任应开识先生,并问能否见到他。长沙当地政府接待人员知道我是指哪位,他们拒绝了我的请求,不过仅仅告诉我他仍然在长沙,并在一所小学教书。毫无疑问,他被关起来了,也许还受到虐待。听到以前有才干的教育家受到迫害,我内心处在极大的痛苦之中。在一九八十年代中国政治气候开始有些好转时,雅礼协会邀请应开识去纽黑文并给予他荣誉。应开识那时已是八十多岁了,由以前雅礼的一位学生陪同去的。我那热衷于雅礼的大哥华家杰专程从洛杉矶到纽黑文参加这个庆典。

1941年应开识(左,雅礼中学教务长,1932年耶鲁大学文学硕士)和劳启祥(右,雅礼中学校长,1926年芝加哥大学理学硕士)先生摄于湖南沅陵。由雅礼协会会长Nancy Yao Maasbach(姚南薰)提供并授权引用。
对于纽黑文来说,共产党政府驱逐俞道存意味着雅礼协会在中国大陆活动的中断。但是雅礼协会没有受阻,通过资助在香港的一个叫做新亚书院、后来变成香港中文大学的新学校继续她在教育方面的工作。雅礼协会(Yale-in-China)后来也改名为Yale-China Association,这反映了时代的变迁。“文革”时代过去了,在1985年,第五中学恢复了她原来的名字:雅礼中学。自从那时到现在,雅礼协会和中国保持着活跃的教育交流项目。现在,雅礼中学是一个有数万名毕业生的名校。最终,正如她的创立者所预料的,雅礼中学自己的毕业生以及高标准的学术和精神的传统支撑着雅礼中学。
2001年,以当时的执行主席南希•查普曼(Nancy Chapman)和杰西卡•普拉姆(Jessica Plumb)出版《雅礼协会百年史》(The Yale-China Association – A Centennial History)为顶点,雅礼协会庆祝她在纽黑文成立100周年。这本144页、280多张照片和插图的精美书籍对历史感兴趣的人来说是一部精选作品。这本书写得很好,是一本适合放在咖啡桌展示或当圣诞礼物的书,这篇文章的部分信息引自这本书及另一本前面已述的候登写的书。
正如《再见,切普斯》先生的结尾一样,雅礼协会的早期创立者——胡美、何钦斯、俞道存——可以安详地休息了,而她还在继续培养许多像她教育过的青年——劳启祥、陈乃勋、应开识、华楚书、华家杰、华家烈、华家熙……
(原文刊登在美国《美华论坛》2005年10月第21卷第2期4—12页)
附录:
华家熙博士(1924-2005)
田长焯(C. C. Tien)著 乔志译
华家熙博士于2005年7月2日在康涅狄格州斯坦福特(Stamford)去世。他与癌症抗争了最后18个月之后故去了。我代表《美华论坛》(Chinese American Forum)对失去华博士表示深深的悲痛。
毫无疑问,他是一位成就卓著的美籍华人,不仅代表他自己、他的家庭,而且还代表美籍华人团体(见2002年10月《美华论坛》第2至5页)。
特别的,华博士长期担任《美华论坛》董事会成员(1990-1999),并且发表了许多文章。华博士也是一位国际公认的职业化学家。他在1970年代创立了美籍华人化学协会。最近几年,他是一位充满激情为公正而战的正义之士。
通过他和“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联合会”(Global Alliance of Preserving the History of WWII in Asia)朋友们的努力,美国通过了编号为PL106-567的《日本帝国政府情报公开法》(the Japanese Imperial Government Disclosure Act of 2000)(2000年12月27日)的公共法。部分自从1945年起长期隐藏在美国保密文件里的关于日本在二战期间和战前在中国、朝鲜和东南亚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的黑暗秘密首次公布于众。
华博士留给了我们为人权和正义而战的遗产。我们会思念他,还要继续战斗并以他为榜样。我们向华博士的家庭致以深切的问候。
(田长焯博士在波音公司工作34年,1995年退休。曾任美华航天工程师协会、全美总会理事长、《美华论坛》社长,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前校长田长霖的胞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