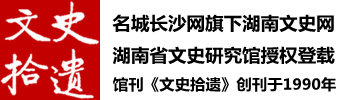2001年5月20日上午9时,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我的恩师马积高先生与世长辞,迄今已整整十载。时光如流水,可以冲刷往事,冲洗泪痕。但这三千六百五十多个日日夜夜里,马先生的音容笑貌,却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镂心刻骨,历久弥深,伴随我的也渐老去的人生。“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苏东坡抒写的,正是人心最深挚最沉重的哀痛。
1959至1963年,我的大学时代在原湖南师院中文系度过。作为一名普通学生,我与马先生并未有过私人接触。当时我正热中于习学古典诗词,给我们讲授唐宋文学的刘家传(廉秋)先生家便是我和学友常去的地方,却不知道马先生也是一位杰出的诗人。对先生的这一认知,是直到老人家病逝后拜读先生手定廖可斌君誊稿的《风雨楼晚年诗抄》才获得的,不胜追悔。而在学生时代留下深刻印象的,则是先生的教学风采:那常带着微笑的注视着学生的眼神,那从容淡定、潇洒自如的气度和旁征博引、鞭辟入里的讲析,都使我着迷和倾倒。以至于时隔十余年自己登上大学讲台以后,都会情不自禁地作为准的学习模仿。
不知道先生那时是否认识我这个年轻瘦削的暗中崇拜者,但不久发生的一件事情却把我和先生联系在一起。这件事情的原委,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我才得以知道。1963年夏天,59级毕业分配时,一位专业成绩全优的学生进入了时任中文系副主任兼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马积高先生的视线。他和系主任李祜坚决主张把这个学生留校任教。但由于该生父亲的历史问题,‘政审’未能通过,此议遂沮。其结果,是应届毕业生未留下一个教学人员,这在中文系历史上是少有的事。‘文革’初,马先生和羊春秋先生(时任古代文学教研室副主任)被作为全省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代表人物‘揪出’,一时‘马羊’成为牛鬼蛇神的代称。随后,李祜主任备受凌辱迫害,夫妇含愤自杀。在批判他们“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罪状”里,就有‘培养修正主义苗子’一条,而为某生留校力争便是一大“罪证”,此事当时弄得沸沸扬扬,尽人皆知。而这位当时成为焦点人物的‘某生’便是我。那时,我在长沙市某中学任教,毫不知情。只是运动初组织上来人要我揭发‘马羊’,但我确实认识不到他们的问题,也就没有写任何材料。我那里想到,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极‘左’肆虐的年代里,我所尊敬的几位老师,会不避风险,主持公道,重才惜才,而蒙受若大苦难。我永远感激他们,并且因为自已未能取得更多成绩报荅他们而深为愧疚。羊先生后来去了湘大,而我和马先生则因为这一段苦难的缘份而接续了二十年的师生情谊。
1981年,我从中学调到高校任教,特别是从1984年到湖南教育学院及以后在湖南师大文学院,同先生有了较多的直接接触的机会。虽然我已无法到先生门下读研深造,虽然“文革”十年和在中学期间科研荒废,自己重新起步太迟,但先生却以极大的热忱给予关心、指导和提携,对我的每一点成绩和进步都给以鼓励,特别希望我有所创新。我担心自己在知识积累上比老一辈学者差距太大,科研难出成果,他说:“你悟性好,肯用脑子,接受新鲜事物比我们快,只要扎实用功,一定会搞出自己的东西。”按照先生的吩咐,我一面拼命读书,恶补欠缺,另一方面注重吸收国内外学术前沿信息,提高和更新自己的理论思维能力。80年代中期,在思想解放的潮流推动下,古典文学研究也酝酿着观念和方法的突破。我作了一点尝试,于1985年和86年写作了《论贾宝玉的女性美崇拜意识及其人性内涵》、《论曹操形象的整体结构及其意义》等论文,运用系统论思维方法对研究对象进行整体性结构性把握分析,并由此提出了一些个人观点。马先生读到以后,即给予充分的肯定。他在1987年为《湖南社会科学手册》(1988年1月湖南人民出版社)撰写的综合述评《古典文学研究概述》评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古典文学“再研究和再评价”的新气象时写道:
“许多论文在研究方法上同过去相比有较大区别,主要是用深入细致的具体分析的方法代替例证加观点的定性的方法,对历史上许多本来复杂的文学现象不作简单的肯定与否定,而是力图从与之相关的各个方面(内部的、外部的、主体的、客体的)作具体分析,以揭示其固有的矛盾和主导倾向。但在实际运用上又各有不同,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用所谓传统的方法,实际上就是用我们过去习用的一些术语、概念(这些术语、概念大都来自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东欧及我国一些革命文艺批评家的著作,也包括我国古代文论中常用的概念)来进行分析。……第二种是所谓新方法,即适当地吸取现代西方自然科学和哲学著作中的某种分析方法或术语,作为分析的工具,以达到揭示历史真相的目的。如刘上生的关于贾宝玉的论文和关于曹操的论文(均见1986年《湖南教育学院学报》。作者按:两文分别见于1985年6期和1986年3期教院《学报》)即吸取了系统论的方法,对这两个文学上的典型形象作了多层次多角度的分析,并揭示其主导的本质的倾向……”
马先生时任湖南省古典文学会会长,从古典文学研究方法革新的角度所作的这种高屋建瓴的评述对于刚步入学术大门的我是多么大的鼓舞。正如马先生后文所说,当时古典文学界的大多数人(包括先生自己)都习惯于“前一种方法”,尝试改变传统话语体系的还只有极少数人,而且这种努力也只是初步的、不成熟的、探索性的。当时不乏指摘、质疑的声音。但先生不但敏锐地发现新生事物,并且热情地加以扶持。他在评述中不仅指出,两种方法不是互相对立的,还特别强调,“采用新概念,术语的人,也仍然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作指导。”爱护之心,溢于言表。听说,马先生和宋祚胤先生在参加省职称评定会后,还在师大中文系的全体教工大会上对我的努力大力揄扬,以后又推荐我担任省古典文学学会理事。老一辈学者提携后进的拳拳之心,至今思之,令人泣下。
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在教学之余,一面参加先生和黄钧老师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编写,一面着手酝酿个人学术著作《中国古代小说艺术史》的写作,登门求教更为频繁,得到先生耳提面命的直接指导更多。谈到写‘史’,他经常引用刘知几《史通》,特别是章学诚《文史通义》的观点,强调史才、史学、史识三者必兼,而尤重史德(章学诚)。所谓史德,就是著史者的人格修养,表现在著述中,就是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勇气操守,这是具有史识(创造性见解)的前提。而才、学则是基础。著史,不能随波逐流,不能哗众取宠,也不能一味标新立异,只能从对事实材料的研究中得出合乎实际的科学结论。在撰写《中国古代文学史》的中唐诗歌部分时,我根据自己掌握的资料和学术信息,提出应摒弃并不符合文学史实际的“新乐府运动”的提法而用“写实讽谕诗派”的概念,来概括白居易诗派的特点。因为这一诗派的诗人在重视运用乐府诗的形式时,包括用“寓意古题,剌美见事”的古题乐府和“因事立题,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进行创作,并非只写新题乐府。由于他们比较重视诗歌的社会接受和直接效应,因而都重视表达和语言的浅切通俗,故文学史上曾把他们称为“通俗诗派”或以其代表人物称为‘元白诗派’,与同一时期的韩孟诗派相对称,但从主要方面看,这一诗派的内容特征显然更重于形式特征。他们在创作实践上或各有取舍,而把写实手段和讽谕功能统一起来,则是他们的共同追求。马先生认为我的意见很有道理,写实讽谕诗派的提法也有新意,比较合乎实际,但他又指出,应该从文学史的源流上把这个流派讲清楚,这样你的论述才能完全站住脚。后来,我在“中唐初期诗歌”增加了对杜甫、元结和《箧中集》的论述,在晚唐增写了‘唐末写实讽谕诗歌’一节。但由于种种原因终未能如先生所愿,把源起于《诗经》的比兴讽谕、汉乐府的写实讽世传统的这一重要流派的发展演变脉络完全理清,留下缺憾。由此事可见先生的史识。在先生的《赋史》、《宋明理学和文学》、《清代学术思想的变迁与文学》《荀学源流》等一系列开创性学术著作中,这种清源流、理脉络、重发展的卓越史识都表现得十分鲜明突出,使人深受启发。我在撰写《中国古代小说艺术史》时,便从此获益良多。在论述古代小说的早期形成时,我通过自己的钻研和思考,根据先秦文化发展的特点(由巫文化到史官文化到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及其递变与联系,总结出传说散文化,历史文学化和议论故事化三条发展线索,以此论述早期小说孕育于史书和诸子著述的过程;同时根据小说艺术主要孕育和形成于史书的事实,进而阐述先秦时代从本体上史说(小说)同源,形态上史说同体,观念上史说同质,到以后史说异派分流,它们从形态到观念的分离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从秦汉至唐),而仍不免因此发生各种各样的纠葛。马先生对于这些关于中国小说发展独特道路的探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中国古代小说艺术史序》中,他写道:“这些概括和分析是既有切实的材料依据又有理论深度的,它不仅使近些年来我国研究界关于小说起源的争论迎刃而解,更重要的是确定了这个源头,从史说分合的角度来俯视以后二千年小说的发展史,许多长期纠缠不清的问题(例如小说与杂记常常混在一起,小说起源早而成熟迟、小说创作中真与幻的争论等)和引人注目的特点(例如历史小说特别多,小说家多以写史的态度汲取史的笔法写小说等)都如高屋建瓴,得到了清晰、系统而合理的解释。”可是,我在《古代小说讽剌艺术的发展》一章中,论及唐传奇讽剌艺术的传统并未能在宋元话本中得到继承,直到明末方有讽刺小说问世,中间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断层,在探讨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时,我提出了与宋代民间伎艺的某种分工有关的推想,认为由于“讽剌滑稽,主要由继承古优和参军戏讽剌传统的表演伎艺杂剧所担负,故以讲史小说为主体的通俗话本,则以传奇性娱乐大众”。马先生认为这一观点虽有创意,但只从不同文学体裁的分工着眼,立论较为单薄,应从更广阔的视野多方面探析,方才周全。以上数例,均可见在我的学术道路的每一步,是怎样得到先生的关怀指导。
1992年冬至次年初,我的《中国古代小说艺术史》将近终稿,当时先生正抱病休养,竟不顾自身健康,为我审阅40余万字的书稿,并欣然作序,表示最大的支持。那时我并不了解先生的具体病况,只见先生尚在家中,便把一叠叠的书稿送给先生,但心中总有不安。有一次,我想向先生有所表示,不料先生竟勃然大怒,命我即刻将书稿带走。我含泪低首,无言以对。因为先生从未对我发过脾气。先生见我如此紧张尴尬,才改容放低声音对我说:“上生,你真蠢!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把老师看成什么人了?”一字一顿,沉重敲击我的心。这件事给了我极大的震撼。我才真正明白,什么是“史德”,什么是一位学者和导师的人格操守。在高大的先生面前,我只是一个卑弱的凡夫俗子,我跟他老人家的差距有多么大,多么远。回想起那段时间在同先生闲聊时,他经常表达对日益严重的一切向钱看、道德下滑、腐败丛生的社会风气的愤慨与忧心,我懂得了先生的人生终极追求。若干年后,我在《风雨楼晚年诗抄》中读到先生这一时期的诗作《一九九二年岁尽书怀,时在病中》:
未能超悟与胡涂,犹自劳生看岁除。淹病难禳惊已老,哺糜不用叹无鱼。孔丘遵道宁浮海,老子清心强著书。京国近传消息好,只愁尸祝入庖厨。(注:时学人纷纷下海,故末句及之)。
先生的疾病与沉重心情延续到次年仍未消除。《一九九三年中秋与国庆相值,感事作》写道:
又值团圆欢庆时,江山寥廓动秋思。避疾难同人共醉,深居唯有鸟相知。无心风月随缘受,着手云烟故自奇。却是苍生忘未得,羞从大款噪明时。
两年之后,先生写了组诗《七十抒怀》,回首生平,感慨歔欷,其四诗云:
商品狂潮卷地来,鱼龙魔怪竞登台。当官合具离朱目,致富惭非范蠡才。但得园林多秀木,不辞蔬食老蒿莱,寄居破屋君休笑,时有清风扫浊埃。
可知,在年老衰病和社会转型之时,先生正经受着身体和精神的双重煎熬。其沉重,当非常人可以想像。但先生向社会、向大众、向学生弟子捧出的是一颗燃烧的、赤诚的、滴血的心。“但得园林多秀木,不辞蔬食老蒿莱”,就是这位七旬老人终身不渝的人生选择。《艺术史》四十余万字的书稿(审阅)和近四千字的长序,就是这颗心熊熊燃烧的结晶。这种超负荷的辛勤付出,肯定损害了先生的健康,以至导致他的过早病逝,想起这些,我无限感激和自疚。
马先生对我在学术上的进步极为高兴,他在《中国古代小说艺术史序》中纵论古今,称赞我写了一部“堪称是新见迭出的别开生面的著作”,还“到处逢人说项斯”。为催我前行,先生鼓励道:“上生同志为人治学都很笃实而思想开扩,博学多通而又正当盛年。这部书只是他的一个方面的研究成果的荟萃,我期待着他有更多的成果问世……”在先生的关怀下,我继续努力,又撰写了《走近曹雪芹——<红楼梦>心理新诠》和《曹寅与曹雪芹》两部研《红》著作。但有段时间,我的一些研《红》论文受到质疑,因为我对本籍汉族没身为奴成为满洲包衣旗人后代的曹雪芹是否具有民族意识及在《红楼梦》中的表现进行了一些自己的探索,是否受了索隐派的影响?马先生知道后,抱病特地看了我的论文和著作,对我说:“我看你的研究方向和方法没有问题。民族意识可以谈。”接着,他跟我举了许多明末遗民及清初汉人的思想言行的例子。说:“人的思想意识是很复杂的,不能过分强调某一个方面,要避免绝对化。”语重心长,富有深意。在研《红》过程中,我为了弥补自己过去在文献方面的不足,有意识地对曹雪芹祖父曹寅进行了重点个案考证研究,我的几篇文章都得到了先生的赞许。然而,正当我结集完成《曹寅和曹雪芹》书稿,准备奉献到先生病榻前的时候,先生却突然病势转重,溘然辞世,给我留下永远的伤痛和遗憾!
“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马先生永远地走了,但他的名字,他的著作,他的风范,都是永恒矗立的不朽丰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我虽只是先生的一名普通学生,但先生博爱覆载,遇我之厚,有同私淑。先生之恩,山高水长。在先生等老一辈学者宗师面前,我等学人,自觉平庸浅薄,只能追随不舍,铭心为报。我虽已年近老迈,但还愿努力。像先生一样做人,像先生一样处世,像先生一样治学。爝火虽小,尚可暖人。愿天堂的灵光,永照我在人生路上前行。
谨以此文和小诗为先生逝世十周年祭
怀恩师马积高先生
茫茫十载隔阴阳,如昨音容未或忘。
敢忝门墙拟桃李,深欣沧海指舟航。
蕙兰畹里花如血,风雨楼前月似霜。
珍重琳琅遗墨在,传承薪火赖辉光。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马积高先生的治学风范】刘上生2011年4期总86
2015-01-03 20:19:01 来源: 评论:0 点击:
2001年5月20日上午9时,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我的恩师马积高先生与世长辞,迄今已整整十载。时光如流水,可以冲刷往事,冲洗泪痕。但这三千六百五十多个日日夜夜里,马先生的音容笑貌,却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
分享到:
相关热词搜索:马积高 治学 风范
上一篇:【李桑牧对鲁迅研究的独特贡献与影响】丁仕原2011年4期总86
下一篇:【作曲家白诚仁的艰苦历程】李欣2012年1期总87
分享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