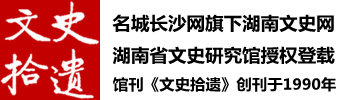杨树达 胡适 易家钺(易君左)
杨树达与胡适,都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重量级人物。二人因地缘、学缘、性格、学术路径等方面的差异,一生交集并不太多,在二人留下的交往记录中,也以意见相左和观念冲突为多。他们的第一次交往就以并不愉快的冲突开始。
1920年以前,杨树达与胡适二人南北揆隔,一直无缘结识往来。杨树达自1911年底留学日本归国后,一直在湖南长沙楚怡中学、湖南第四师范、第一师范、女子师范等校任教。胡适自1917年留美归来后,任教于北京大学。1919年11月,在湖南民众驱逐军阀张敬尧的斗争中,杨树达作为湖南教育界代表,与公民代表毛泽东等人一道北上,向北京政府请愿,直到次年6月张敬尧由湘出走后,杨树达等请愿代表才返回湖南。在滞留北京期间,杨树达可能曾过访胡适。据胡适1920年2月5日《日记》中记载:当日下午二时,“杨遇夫来?”查阅《积微翁回忆录》,当日杨树达没有走访胡适的文字记录;从胡适《日记》此条记载文字后的问号推测,有可能是胡适将别人来访误以为“杨遇夫”,也可能是杨树达确曾于当天下午拜访过胡适,但不知因何原因,胡适显然没有见到杨树达。
1920年6月杨树达从北京回湘后不久,原时务学堂同学范源濂就任北京政府教育总长,他决定前往北京谋职。据杨树达自述其中缘由:“历年在湘任教国文,以改作文卷为苦役。居京数月,见诸任教大学者每周授课不过八、九时,自修时间绰有余裕,每心羡之。近来政局一变,范静生(源濂)任教育部长,思入京谋一教职。”8月下旬,杨树达再度北游,29日抵达北京。9月11日,在梁启超、范源濂的推荐下,到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任职。胡适当时在北京大学任教,同时也兼任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委员。从此,杨、胡二人因同居京城,同在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任职,有了较多交往机会。
胡适留美归来后,乘新文化运动的东风而“暴得大名”,年仅26岁即任北京大学教授,是红极一时的学界“名流”,尤其是他提倡新文学、创作白话新诗,开中国文学界新风,被时人誉为“新文学的泰斗”、“白话诗的通天教主”。却不料在1921年5月发生一件有关“白话诗评”风波,使一向性情温和的胡适,从“略动感情”而大动干戈,其中就牵涉到杨树达。
事情的起因是:胡适的中国公学同学谢楚桢(湖南人)旅居京城,正醉心于胡适等人提倡的新文化运动,他响应胡适的号召,正努力创作白话诗,并且研究白话诗。他收集了一些时人所作的白话诗,并加入自己的点评文字,汇集成一本《白话诗研究集》,拿给白话诗的提倡者胡适看,本以为会得到胡适的欣赏,并请胡适推荐出版。哪知胡适浏览文稿之后,极不以为然,认为“里面的诗都是极不堪的诗,……我说这里面差不多没有一首可算是诗,我又说单有白话算不得诗。”因此,拒绝为之介绍出版,表现出胡适爱惜名声,不苟且循情的为人风格。
当时,谢楚桢住在前门外的湖南同乡会馆里,穷得一塌糊涂,每天自己烧饭,房间里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简直落拓不堪,急于成名以改善生存状态,也是情有可原。在胡适那里碰了一鼻子灰后仍不甘心,他找到正在北京的湖南老乡易家钺、罗敦伟帮忙。当时,湖南人成舍我在北京,正邀集同乡罗敦伟、易家钺等人创办新知书社,致力于出版新文化书籍,请易家钺担任书社总编辑。他们出于乡谊之情,十分同情谢楚桢生活艰难,有感于其对新文学的热心,便同意由新知书社出版《白话诗研究集》一书,易家钺亲自担任该书责任编辑。据《胡适日记》所述:“他后来结交了易家钺、罗敦伟等一班新名士,他们把他捧作一个大诗人,他这部诗评居然出版了!”经过他这位“白话诗的通天教主”鉴评为“不堪”的书,竟然得到一些京城“新名士”的吹捧,并公开出版了,无疑是对白话诗“通天教主”地位的公开挑战,这自然让胡适感觉不快。尤其是该书出版后,谢楚桢又来找胡适,“要我替他在报上介绍,我完全拒绝了他。”再次被胡适拒绝后,谢楚桢并不罢休,当时罗敦伟正主持《京报》副刊“青年之友”栏目,谢楚桢又找到罗敦伟帮忙,在《京报》上登出一则《介绍新出版的〈白话诗研究集〉》的大广告,其中写道:
是书系谢楚桢先生苦心孤诣之作,全书约十万言,内容:上半卷列诗录五十余条,研究新诗作法,无美不备;并列诗谈选一门,都系时下一般名人所作,下半卷列诗百二十首,思精笔美;并列诗选一门,都系男女青年的杰作。讨论批评,创造采集,无所不有,诚为新文艺中别开生面之书。至如生活类中描写社会各种妇女生活状况,使人可怨可歌可笑,尤为此书之一大特色。同人等因其于新诗界大有贡献,特为郑重介绍,想凡有志研究新诗的人,当无不先睹为快哩。
这则广告的署名人包括:杨树达、沈兼士、李煜瀛、孟寿椿、易家钺、孙几伊、陈大悲、罗敦伟、瞿世英、郭梦良、陈顾远、徐六几十二人,都是当时京城小有名气的学人。广告内容应当是该书作者谢楚桢本人所拟,目的无非是扩大影响,为书籍销售打开销路。而署名介绍该书的这些“名士”们,或许出于友情、乡谊,加上文人的惺惺相惜,也就同意在这份“虚假广告”上署名,却不知无意中开罪了“大名士”胡适。胡适《日记》中记载了他看到这份广告后的反应:“我看了很不满意于这几位滥借名字的‘名人’。” 事情到此为止,或许还不至于让胡适大动肝火。
谢楚桢《白话诗研究集》出版、并在《京报》上刊登广告后,的确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当时,正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读书的女学生苏梅(安徽人,胡适的同乡,即后来的“文坛才女”苏雪林)读到这本研究白话诗的文集后,认为该书所选白话诗格调低下,不忍卒读,于是在《益时报·女子周刊》上发表《对于谢君楚桢〈白话诗研究集〉的批评》一文,极严厉的批评这本诗集,文中有“谢先生尽可打牌赌钱去骗钱,不应该出这样的烂书来骗人”的话,又责备推荐该书的人“不应该如此轻率,为这书作推荐人,简直是伙同作者骗人钱财。”苏梅的批评文章见报后,有人化名A.D写了一篇《同情与批评》的文章,刊登在罗敦伟主编的《京报》副刊《青年之友》上,高调反击苏梅对谢楚桢《白话诗研究集》的批评。看到这篇署名A.D的反驳文章后,苏梅推测该文是《白话诗研究集》一书的编辑易家钺所作,于是又在《女子周刊》上撰文说:“A.D这篇文章一定是易家钺作的,至少也有很多易家钺的成分在,正像英文中的DOG=狗,A.D一定等于易家钺。”苏梅认定化名A.D的作者即是易家钺,并将其类比为“狗”,这无疑是在骂“易家钺是一条狗”,对于易家钺来说,这样的辱骂是不可忍受的。
易家钺何许人也?他字“君左”,湖南汉寿人,是晚清著名诗人易顺鼎之子,幼受庭训,饱读诗书,才思敏捷,少年时即有“三湘才子”之誉,1916年考入北京大学国文系就读,当时正担任新知书社总编辑。这样一位青年“才子”,何曾受过别人辱骂,当他看到苏梅指名骂他的文章后,怒火中烧,一气之下,便写了一篇《呜呼苏梅》的文章,署名“右”发表于5月13日的《京报》副刊上。文中起笔说:“北京舞台上新近到了一个名角,专演《新安驿》、《闹洞房》一类花鼓淫戏。其人为谁?呜呼!苏梅!”随后满篇都是这种笔调把苏小姐骂得体无完肤。他在文中反问苏梅道:“苏女士,你认A.D的文章中间至少有易家钺的成分,我且问你:假定我说你的文章中间有别人的成分,行吗?”为报苏梅骂他为“狗”之仇,在此句文字后面,他又专门添加括号写了一句被胡适称为“极丑的话”:“假定说你身体中有别人的成分,行吗?”当时苏梅还是一位20出头未婚的女大学生,此言无异是暗指苏梅与人“性交”,这样“下流”的话出现在《京报》副刊上,立即引起北京知识界的公愤,该文作者易家钺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且牵连到发表该文的《京报》副刊编辑罗敦伟。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5月18日《晨报》登载新知书社启事,宣布取消易家钺、罗敦伟二人的编辑职务。5月19日,成舍我又在《晨报》显著的位置刊登《特别启事》说:“本社董事易家钺为文攻击苏梅,引起社会公愤,信用荡然,人格扫地,着即免去董事之职;罗某主编青年之友,刊载此种文字,同样人格扫地,也一同免职。”为公平起见,《晨报》同时刊出《易家钺紧要启事》,坚决否认《呜呼苏梅》一文是自己所写。
胡适一直在关注着这场笔战,当他看到一邦“小名士”竟然欺侮一位小女生!这使得很有绅士风度的胡适怒不可遏。据1921年5月19日《胡适日记》载:“今天我做了一件略动感情的事。”起因即是苏梅发表批评谢楚桢的文章,因此“触怒了那几位护法小名士,他们在《京报》上大骂苏梅。这场笔战闹的很不名誉,我也不详叙了。”最令胡适感到愤怒的是,在新知书社宣布免去罗敦伟、易家钺的编辑职务,易家钺坚决否认自己是《呜呼苏梅》一文作者之后,《晨报》又登出一则《紧要启事》说:“近来外间有人误认《呜呼苏梅》一文系易君家钺所作,想因易君曾作《同情与批评》一文辗转误会所致。同人对于易君相知有素,恐社会不明真相,特为郑重声明。”郑重证明该文非易家钺所做。启事署名者为彭一湖、李石曾、杨遇夫、戴修瓒、熊崇煦、蒋百里、黎劭西、孙几伊八人,都是在北京各高校任教的名流学者。胡适看到这则启事后更加愤怒,认为这些人身为社会“名流”,竟然不顾事实,不讲道理,仗势欺人,“社会即肯信任我们的话,我们应该因此更尊重社会的信任,决不应该滥用我们的名字替滑头医生上匾,替烂污书籍作序题签,替无赖少年辩护。”盛怒之下,胡适和高一涵立即联名写了一则质问八人的启事,送《晨报》要求刊出。全文如下:
一湖、石曾、遇夫、君亮、知白、百里、劭西、几伊诸位先生:今天在《晨报》上看见诸位先生的紧要启事,替易家钺君证明《呜呼苏梅》一文非易君所作。我们对于诸位先生郑重署名负责的启事,自然应该信任。但诸位先生的启事并不曾郑重举出证据,也不曾郑重说明你们何以能知道这篇文章不是易君所作的理由。我们觉得诸位先生既肯郑重作此种仗义之举,应该进一步把你们所根据的证据一一列举出来,并应该郑重声明那篇《呜呼苏梅》的文章究竟是何人所作。诸位先生若没有切实证据,就应该否认这种启事;熊先生是女高师的校长,他若没有切实的证据,尤不该登这种启事。我们为尊重诸位先生以后的署名启事起见,为公道起见,要求诸位先生亲笔署名的郑重答复。
胡适、高一涵联名的启事送到报馆后,北大学生朱谦之、《京报》主笔邵飘萍、《晨报》主笔蒲伯英等人,都劝胡适不必登出这则咄咄逼人的“启事”。据胡适日记所载:“今晚朱谦之君来,问我能否不登那个启事,我把我的理由告诉他,他就不劝我了。他又说,‘我是快要出家的人了,我后天临走时登一广告,说《呜呼苏梅》是我做的。’我劝他不要如此,因为这虽是仗义,其实是虚伪。他合十赞成,就去了。”不久,“《京报》主笔邵飘萍君打电话来,说他可以完全负责说那篇文章不是易家钺做的,问我可否取消那个启事。我问他,那篇文章究竟是谁做的?他说不知道。我说,那末你不能完全负责。《晨报》主笔蒲伯英君与那八人中的彭一湖君都打电话来,说易家钺明天可以举出一个定使大家满意的证据来,问我可否把那个启事迟登一天。我说,我的质问是对那八位先生而发的,并不为易君本人。那八位先生还须等到明天方才有证据,这就是我不能不质问的理由。我这个广告是不能延缓的,他们明天有证据尽管举出来。”坚持要《晨报》立即刊出他对八人的“质问”。
胡适、高一涵的《启事》刊出后,逼迫八人举出证据来,于是,原来力挺易家钺的“名士”们只得督促易君拿出证据,以证明自己的“信用”。第二天,易家钺并没有“举出证据”来,此后,《京报》也未刊出相关《启事》证明该文不是易家钺所作。5月20日,《少年中国》杂志的“会务消息”上登载一条消息:“近日《京报》上发现易君辱骂女高师苏梅一文,吐词淫秽,阅者无不骇怪。各方面均认为易君手笔,而彼亦无以自白。此文直不啻宣告青年人格的破产,于社会前途影响实大。……适次日易君亦自来函再请出会,并表示非常抱歉之意,遂由执行部一并提交评议部,全体赞同易君自请出会。”说明易家钺正是该文的作者,“少年中国学会”已因此事将其开除出会。
至此,原来力挺易家钺的八位名流学者,不得不各自撇清与此事的关系。5月21日,在北京师范大学兼课的北大教授钱玄同告诉胡适说:“黎劭西(锦熙)并不知有为易家钺登广告的事,乃是杨遇夫之过。”当日,胡适收到黎锦熙的来信,说明此事原委,黎锦熙在信中说:“昨早未见报,午后到北师校,才知道有这回事。傍晚晤杨君,他说先夕本欲通知我,时间紧促,来不及了。细看所登的启事,不过是友谊的对于个人一种人格的证明,君子成人之美;至于这场是非,自有社会上的公正评判,这个启事并无一语涉及;因此我那署名的事,也就对杨君作了事后的承认。”声明自己事先并不知情,是杨树达替他在《启事》上签字署名的。另据胡适《日记》所载:“八人中的戴修瓒也面告一涵,说他不认得易君。熊知白告梦麟说他无法答我的质问。其余几人今日并无回复,报上也不见昨晚他们说的那个‘定使大家满意的证据’!”
眼看易家钺无法拿出确切的证据,5月24日,彭一湖、李石曾、蒋百里、孙几伊四人联名在《晨报》发表《致易君左启事》道:“君左兄:前日你自己郑重声明《呜呼苏梅》一文不是你做的。我们以为此种证据至易检出,且《京报》既发表此文,致兄受诬,当然有为兄辨白之责。然连日《京报》既无负责任的宣言,而胡、高二君又要求我们举出反证,我们以为此事为兄自己名誉,为我们信用,当然有 要求《京报》举出反证之必要。除登报声明外,特此奉闻,即希见复。”次日,熊崇煦、黎锦熙也发表《启事》,声明一致列名昨日彭、李、蒋、孙在《晨报》上所登启事。
至此,在《晨报》上刊登《紧要启事》的署名人中,除杨树达一人外,其余七人全都通过书信、公告、面告等形式,向胡适证明本人在此事中的“清白”,只有杨树达没有公开向胡适“认错”。
参考文献:
[1] 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2] 曹伯言:《胡适日记全编》第三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3] 《京报》,1921年5月10、13日。
[4] 《益世报·女子周刊》,1921年5月12日。
[5]《晨报》,1921年5月18、19、20、24、25日。
[5] 《少年中国》3卷1期,1921年5月20日。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